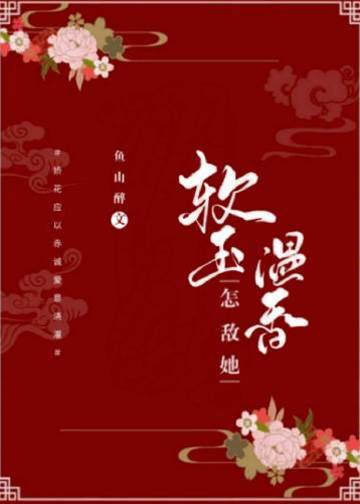《瑤臺春》 第 52 章
男孩子的年對父親的崇拜當然是可以理解的,鄭玉磬也不否認,聖上的權勢和格是會招小孩子景仰的,隻是那個妹妹,大概是永遠生不出來了。
鄭玉磬已經習慣了每日午後睡足起,之後見一見宮裏的管事,理一理宮中的賬務,做了許多年,早已經駕輕就,隻是或許因為聖上許了那個位置,弄得每臨大事也做不到有靜氣,一下午看不下去任何東西。
寧越和枕珠在一邊也能知到貴妃的心緒,但他們也不比貴妃好上許多,更不敢出口安,他們與秦王的幹係也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錦樂宮的孩子能做太子,隻差一步,便徹底穩妥了。
這一個下午過得似乎格外漫長,鄭玉磬寧越他們都出去,瞧著那些詩詞樂譜、佛道真經也靜不得心。
最後,從自己的枕頭下麵的暗盒裏取出了那兩串放在一起的佛珠,一個雖然保養,但還是略有些暗沉,另一串已經沒有什麽特殊香味了,但看著油亮,沒被人把玩挲過。
但是盛裝的盒子上卻已經落了一層薄薄的灰,最近是沒有過了的。
溫熱的眼淚滴到已經有幾個年頭的佛珠上,一點點落,帳中的人歎息了一聲,最後還是合上了匣子,將匣子鎖住,放進了床榻最深的角落。
這是心裏最大的,大概會帶到棺槨裏去,至死也不能說。
為了元柏的日後,
他的生父親永遠隻能是一個,隻要能一直哄住聖上,元柏才不會淪落到廢太子厲王如今的下場。
……
到了晚膳的時候,聖上並沒有帶元柏回來。
鄭玉磬略覺得有些奇怪,但這也不是沒有過的事,所以隻是吩咐人上膳,左右皇帝也不會到自己與皇子,隨他們去了。
Advertisement
但是寧越淨手為布菜的時候卻低聲道:“娘娘,聖人宣召惠妃過書房去了,到現在也沒有出來。”
鄭玉磬雖然心頭略,但也隻是莞爾一笑,“且不說聖人要召嬪妃去書房尋歡作樂不會找惠妃,就是想找,那裏麵還有宰相和元柏呢,聖人哪來的這麽多嗜好?”
皇帝就算再離譜,也不會在兒子麵前做出格的事,也不知道寧越有什麽可擔心的。
“宰相們已經出宮回家去了,”寧越為貴妃夾菜,心裏卻總有些不好的預,“聖上隻留了惠妃和楚王,還有咱們殿下。”
鄭玉磬聽他這樣說,也有些吃不下去,雖然聖上待蕭明輝這個兒子一向不好,但是也沒到要當著他母親還有另外一個兄弟的麵訓斥的地步。
匆匆人撤了碗筷,心裏慌的有些厲害,在殿踱步踱了還不到一刻鍾,外麵的小黃門便進來稟報,說是侍監親自來了。
鄭玉磬稍微鬆了一口氣,讓人請顯德進來,溫聲道:“總管夜裏怎麽一個人來了,聖人與元柏呢,怎麽不過來一道用膳?”
顯
德從前對著這位聖上寵的貴妃,一直是恭敬有加,但今日麵上雖然有不忍,但出於明哲保,還是有幾分公辦公事的意味:“貴妃娘娘,聖人請您往書房去一趟。”
鄭玉磬雖然被聖上寵多年,但也沒有衝昏頭腦,依舊有察言觀的本事,見到顯德這樣的臉,便知道或許是今日下午書房裏出了什麽紕,
衫袖下的手微微攥,但顯德肯定是不會同明說其中詳,因此雖然手心被指甲攥出來幾道月牙痕跡,但還是強裝作一副鎮定的模樣,隨口笑道,“既然是聖人相召,那我梳妝妥帖了便過去。”
Advertisement
顯德卻搖了搖頭,他看了看鄭貴妃,“聖人的意思是,娘娘還是快些過去才好。”
紫宸殿燈火通明,往常的天子寢殿大半時候燈火已經歇了,聖上總喜歡在貴妃歇息,因此紫宸殿反而常常被君王閑置。
鄭玉磬哪怕心中閃過一千種可能,但還是保持著往日的嫻雅儀態,然而等侍通傳之後,剛剛邁進書房,便察覺到了些不妙。
元柏懂事以後,很會哭鬧不休,聖上雖然可惜這孩子的天抑,但還是更讚這一點的。
可是現在,卻有兩個侍擎住了秦王的手臂,蕭明弘的被滿滿當當地堵住,哭泣也十分吃力,仿佛是嚨堵塞,窒息的前兆。
錦樂宮跟來的宮人都在外麵候著,鄭玉磬就算平日裏再怎麽能裝,但
是見到自己親生的孩子哭到麵皮漲紅,甚至有些發紫窒息的時候,連對聖上的禮也忘記了行,看了一眼旁邊掛彩的蕭明輝與惠妃,跌跌撞撞地跑到了蕭明弘前。
“元柏、元柏,你怎麽了?”
鄭玉磬眼中的淚不控製地湧了出來,侍們不敢去攔貴妃,也不敢的,任憑鄭玉磬急切卻小心輕地把秦王口中的東西拿出來,連聲音都有些抖。
“好端端的,你這是……”頭哽咽了一下,但是顧及到自己與孩子的環境,驚恐的元柏倚靠在自己的肩頭到來自母親的安,“是怎麽惹你阿爺生氣了,快和你阿爺認錯,不許這樣不統!”
蕭明弘如今也還不到五歲,他驟然遭到這麽大的變故,世界都崩塌了,他聽到阿娘這樣說,哽咽地指著蕭明輝,一一道:“阿娘,他說,他說我不是阿爺的兒子!”
Advertisement
孩稚的話語仿佛是在鄭玉磬的耳邊平地炸雷,搖搖墜,但是想到蕭明稷雖然為人不,但隻要是他盡心想做的事,便沒有一件不的,稍微穩定了一些。
秦君宜大抵是在,一個如喪家之犬的楚王,本沒有可能接到他。
而岑建業的家人,私下裏也一直安排得很好,他與自己是一條船上的人,自己保他榮華富貴,斷不會有反水的念頭。
蕭明弘的那一聲打破了書房其他人的安靜,聖上
略有些疲憊的坐在座上。
地上,是一已經被寶劍劈兩半的骨頭。
“貴妃,楚王指秦王並非朕親生之子,而你混淆皇室脈,你有什麽好辯解的麽?”
聖上的神雖然冷厲,雖然他一句話可以決定地上所跪子和所生孽種的生死,但是聽見自己曾經疼了那麽久的子與孩子悲戚如斯,天子心的酸並不比鄭玉磬一分半點。
但是正因為這樣的酸,才那份心的鈍痛愈發強烈,頭腥甜。
那是他疼了許多年的子,兩人之間經曆了許多,他也不想因為一個兒子突如其來的指責,而難,又與自己離心生分。
但是蕭明輝卻似乎極有把握,跪在書房外死諫,結果呈上來的東西天子也大吃了一驚。
鄭玉磬聽見聖上這樣冷淡,雖然還不知道蕭明輝做了些什麽,但心卻失,站起道:“聖人如今這般,大概是已經信了大半,我還有什麽可辯解的?”
聖上是不信的,哪怕如此寵,也從來沒有信任過。
但是略帶有哭的聲音落在聖上耳中,卻是格外的刺痛心扉。
那盛滿了冷茶的白胎薄瓷在的裳邊四分五裂,元柏正在哭泣的聲音都頓了頓,鄭玉磬下意識護住了元柏,向聖上的時候滿眼不可置信。
“合做過了,滴骨也驗過,”聖上抬了抬手,人將證據都拿給了鄭玉磬看,一字
一頓道:“貴妃,你好得很啊!”
猜你喜歡
-
完結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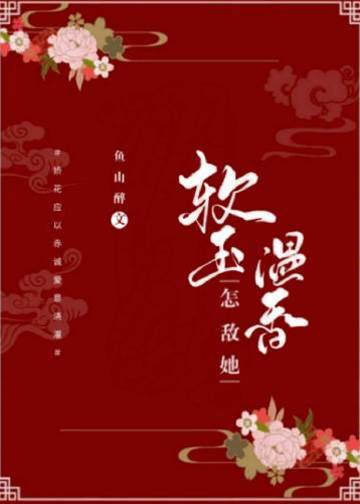
怎敵她軟玉溫香
提起喬沅,上京諸人無不羨慕她的好命。出生鐘鳴鼎食之家,才貌都是拔尖兒,嫁的男人是大霽最有權勢的侯爺,眼見一輩子都要在錦繡窩里打滾。喬沅也是這麼認為的,直到她做了個夢。夢里她被下降頭似的愛上了一個野男人,拋夫棄子,為他洗手作羹湯,結果還被拋棄…
21.9萬字8 10743 -
完結356 章

養丞
童少懸第一次見到家道中落的唐三娘唐見微,是在長公主的賞春雅聚之上。除了見識到她絕世容貌之外,更見識到她巧舌如簧表里不一。童少懸感嘆:“幸好當年唐家退了我的婚,不然的話,現在童家豈不家翻宅亂永無寧日?”沒過多久,天子將唐見微指婚給童少懸。童少懸:“……”唐見微:“知道你對我又煩又怕,咱們不過逢場作戲,各掃門前雪。”童少懸:“正有此意。”三日后,唐見微在童府后門擺攤賣油條。滿腦門問號的童少懸:“我童家
150萬字8 1887 -
完結559 章

一念桃花
八年前,常晚雲在戰亂中被一名白衣少年救下,她望著眼前的少年,俊美,有錢,當場決定我可以; 八年後,常晚雲終於知道了少年的身份。 當朝皇帝的九皇子,裴淵。 重新見面,晚雲作為醫聖唯一的女弟子,來到裴淵身旁為他療傷,阿兄長阿兄短。 裴淵日理萬機,只想將她送走,甚至當起了紅娘。 豈料趕人一時爽,追人火葬場。 晚雲冷笑。 憑本事踹的白月光,為什麼還要吃回去?
95.3萬字8 1050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