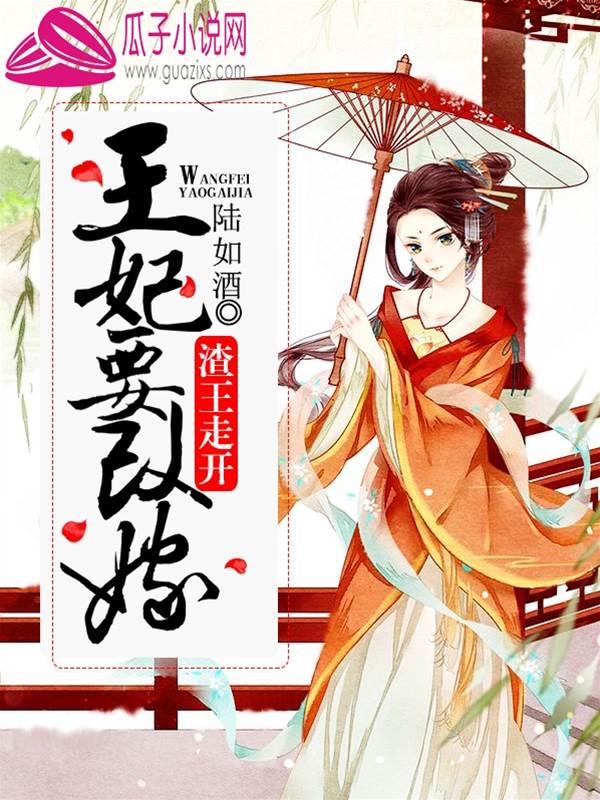《白發皇妃》 第94章 隱姓埋名(2)
心中如此想著,但不知為何,上卻說了一句:“我去小旬子。”說完,嘆氣,人還沒,手已經被他一把拽住,他的力氣依舊很大,手指蒼白,映著同樣蒼白的,怔住,的手是從何時開始,竟也同他的一樣,蒼白似鬼。
怔愣之際,他微微抬頭,眼里忽然有了一亮,“容兒,原來你還會擔心我。”
漫夭一聽,立刻甩開他的手,想說:“誰會擔心你。”但話還未出口,一抬眼,便對上他眼角殷紅的印跡,軀一震,嚇得一屁跌坐在鋪有席子的榻上。那……竟然不是從他口中流出,而是……而是從他眼睛里流出來的!
好詭異!怔怔的著那張消瘦的臉頰,蒼白的面部,襯著眼角垂下的兩道痕,他冰灰的眸子也籠上一層淡淡的霧,讓人看了心驚膽。
見過的腥場面已經太多了,但這種眼睛里流下淚的景卻是第一次見,頓時面一白,心中盈滿了恐懼,分不清究竟是在害怕什麼?
啟云帝見用如此神看著他的臉,不用手了把眼角,對著手上的殘紅,眸變了幾變,卻對笑了笑,仿若無事般的說道:“嚇到你了。”
漫夭雙抿,沒有吱聲。
啟云帝平穩了息,重又坐直,目投在地板上的殷紅跡,沒有焦距。過了半響,他突然問道:“容兒,你確定……他真是你這一生想要的幸福?”
漫夭用眼神告訴他,確定。
啟云帝靠回后的車廂板,緩緩地緩緩地閉上眼睛,他的手垂在邊,一點一點的。
漫夭看著他疲憊到極致的容,不再說話。他也會累嗎?覺得好像不管什麼時候睜開眼,他都是醒著的,幾乎懷疑這麼多天,他到底有沒有睡過覺?還是他警覺太強,哪怕是睜開眼睛也能吵醒他?
Advertisement
見他閉著眼睛許久不,以為他要睡著了,以為這次的談話就這樣無疾而終。正當也準備合眼休息之時,啟云帝再次沒有預兆的開口:“好,我全你。但我有一個請求,你助我達一個心愿,我此生唯一的一個只屬于我自己的心愿,然后,我便放你離開。”
漫夭問道:“什麼心愿?”
啟云帝張開眼簾,眼中一片朦朧而晦的,看不出神,“陪我去一個地方,姓埋名,過一段普通人的生活。你放心,我不會你做你不愿做的事。”
眉頭微蹙,稍稍猶豫,可以不答應嗎?似乎沒有選擇吧!
“什麼地方?需要多久?”
“你去了自會知道。至于時間,也許四五個月,也許半年。”
“不行。半年太久了,我沒那麼多時間。”
的也不知還能支撐多久,半年一過,是否能見無憂最后一面都不一定。而的孩子,要親手給他,囑咐他一定要很疼很疼他們的孩子。
啟云帝似是看穿的心思,“你害怕見不到宗政無憂?不用擔心,你的時間,我會還你。”
“還?怎麼還?”
沒聽說過時間也可以借可以還,除非,他能解上的毒。這“天命”之毒,或許是他下的也說不定。心里燃起一希,定定著他清雋溫和的面龐。
啟云帝卻不再開口,重又閉上眼睛。
“你……”漫夭想問,但一個字還沒說完,啟云帝溫的打斷的話:“容兒,我累了,想睡一會兒,別吵。”
他的聲音似是從肺腑里艱難刺出,虛弱無力,卻堵得不得不住了口。
馬車了啟云國邊界,漫夭開車簾,看見邊城里家家戶戶門前都掛著一條白帆,以示國哀。
Advertisement
如今的啟云國,四都在討論一件事:皇帝大薨,一直潛心禮佛從未踏出慈悉宮半步的太后娘娘突然站出來,持國璽,以皇帝沒留下子嗣為名獨攬朝政。而更令人奇怪的是,朝中幾名舉足輕重的大臣竟站出來表示支持。太后掌政,發出的第一道旨意,以藩王之位為懸賞,活捉皇室不孝子孫——容樂,為皇帝報仇。
因此,漫夭再不敢輕舉妄。而的肚子,也一天天的更沉了。
馬車又走了十日,這天傍晚,停在了一個小村子里。
那是一個麗的村莊,鄰啟云國皇城匯都的邊緣,村子不大,約有十幾戶人家。村里有一條大河,河上修建了錯綜復雜的長木橋,橋邊鎖鏈上掛著各種的蓮花燈,一到晚上,整個河橋蓮燈亮起,五六,斑斕多彩。
這里的村民樸實憨厚,靠打漁為生。白天坐在橋上垂釣,晚上乘船游湖,生活過得有滋有味,令人羨慕不已。
漫夭被扶著下了馬車,站在河岸上,著周圍的景致,忽覺有些悉,仿佛曾經來過這里。
啟云帝已換回男裝,雖不再是錦華服,但那一儒雅高貴的氣質是那布棉所遮掩不住的。他自己也易了容,奇怪的是,就連他易容后的模樣似乎也見過,好像這一次與他出來之后,他的行為舉止,都不自覺產生一種約的悉。
上穿了一件白底藍花的布,頭發用深藍的布包裹著,配著這張普通的面容,雖有不凡氣質,但一般人見了不會多想。
“公子回來啦?”
遠遠的,一個四十多歲的大嬸見到他們,高興的迎上來,笑容真切道:“房子一直收拾著,等著你們回來呢。這下好了,夫人,這次回來不走了吧?”
Advertisement
夫人?漫夭皺眉,疑的看向邊的男子。
啟云帝溫和有禮的笑道:“多謝余嫂。我們這次回來,大概會住上一陣子。旬子。”他對小旬子使了個眼,小旬子掏出一錠金遞給余嫂,客氣道:“辛苦余嫂了,這是我們……公子的謝禮。”
“哎呀,這可使不得,快收回去。”余嫂連忙推拒,“這幾年也就是去掃掃塵,土,不費啥力氣,哪用得著這麼重的禮啊!公子每年派人送來的銀子我們都使不完呢,這回說啥也不能收。你們剛回來,天也黑了,今晚就別起火了,來我家里將就著吃一口吧,也沒啥好菜,別嫌棄就。”
這余嫂倒是個實誠人。啟云帝禮貌笑道:“不麻煩余嫂了,我讓旬子去村口酒肆買些飯菜回去就好。容兒子重,得早些回去歇著。”說著他有意看一眼漫夭隆起的小腹,面上神似是將為人父的喜悅和幸福。
漫夭皺眉,不得不贊嘆這人的偽裝功夫不是一般的強。而此刻的啟云帝斂去一威儀,面對尋常百姓,完全沒有一個皇帝的姿態,他就像是一個儒雅的士,謙和易。
余嫂順著目去看,喜道:“喲!原來夫人有了孕啊,那我得恭喜公子和夫人了!想想啊,你們親也有好幾年了,這是第幾個孩子?”
親好幾年?容樂和啟云帝?六月天,漫夭覺心底遽然升起一子涼氣,將整個凍結。糊涂了,這容樂和的哥哥到底是什麼樣的關系啊?怎麼讓人越來越迷?
啟云帝攬著的肩,對余嫂笑道:“就這一個。”說著,拿了小旬子手中的金錠放到余嫂手中,又道:“這個你還請收著,我想請你幫個忙。”
Advertisement
余嫂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說道:“需要我做啥,公子只管說。”
啟云帝道:“是這樣,容兒自從有了子以后,脾氣不大好,我這次帶出來散心,家中老人不知。倘若有人問起,麻煩您就跟他們說我們是您的遠房親戚,過來投奔您的。”
余嫂了然一笑,以為定是婆媳之間鬧了矛盾,這小夫妻瞞著老人出來散心。果然是大戶人家是非多啊!爽快的一拍脯,笑道:“這個容易,包在我上。別說是旁人打聽了,就算是衙門里的人來查,我也能應付。”
啟云帝道了謝,牽著漫夭的手,儼然一個的丈夫模樣,神溫的說道:“容兒,走,我們回家了。”
漫夭抗拒的想掙他,那余嫂一副過來人的口吻勸道:“公子真是天底下有的人啊!希夫人惜福才好。夫妻兩要同心協力,才能過好日子。快回去吧,懷著孩子別累著,有啥需要幫忙的,讓旬子過來打個招呼就得。”
漫夭皺眉,“我……”
“容兒,有什麼事回家再說,聽話。”啟云帝不給開口的機會,拉著就走。
余嫂在他們后看著漫夭的背影,直搖頭嘆息,“唉,這夫人也真是,有這麼個的丈夫還不知足,非得鬧別扭。也不知道六年前為什麼突然離開,害公子一個人傷心……”
漫夭走得慢,將余嫂的話都聽在耳中,驚在心里。眉頭皺,心中的疑團越來越多,也越發的不安,容樂和啟云帝的關系,似乎比想象的還要復雜。他們不是兄妹嗎?
紛的愁緒如一團麻,越理越,想得頭都痛了。
啟云帝帶著走進村子東頭竹林前的一棟簡單而又別致的小院,院中花草茂盛,院墻四周種滿了銀杏樹,枝葉繁茂散開,將整個小院攏在中央。而院中半人之高的白重瓣蜀葵大片大片盛開,聚在一起,繁華似錦,走在其間的石板路上,一沁人心脾的花香隨風迎面襲來,吹卻一腔煩緒。
“一別六年,這銀杏樹一點沒變,只是這些花兒,已經長得這樣高了。”男子蒙了一層霧般的目四打量,帶著懷念,語氣中著淡淡的幾不可聞的哀傷,最后目落在上,只剩下溫又寵溺的笑意,“容兒,你喜歡嗎?”
漫夭子忽然一僵,腦海中有一副模糊的畫面一閃而逝,似乎聽到有人在說:“齊哥哥,我喜歡這些銀杏樹,我們的房子就蓋在這里吧。到了秋天,風一吹,滿院子都是金黃的銀杏葉,那一定很。”
“好。再圍個院子,院里多種些花草。容兒喜歡什麼花?牡丹好不好?”
“不,我喜歡蜀葵,白的蜀葵,一到夏天,開滿整個院子……齊哥哥……”
頭又痛起來,像要炸開般的覺,用手抱著頭,蹲下去,突然不想聽到那些話。為什麼記憶越多,心中的不安越是強烈?
“容兒,怎麼了?頭又痛了嗎?旬子,快去煎藥。”啟云帝急忙將抱起,走進屋里,放到床上。
用手揪著頭發,怎麼都止不住那猛烈襲來的痛,整個腦袋沉重到無力支撐,亦無法思考。無措的抓住他的手臂,指甲用力掐進去。
手臂上的疼痛沒有令啟云帝皺一下眉頭,他看著的目滿是疼惜,由著在他上留下一個又一個的指印,一聲不吭。
不知過了多久,累了,累得連掐他的力氣都沒了,癱倒在床上,口氣亦覺得艱難。
啟云帝轉出去了一趟,很快便回來,手中端著一個藥碗。他吹了吹,扶起來,將藥遞到邊,苦的藥味合著一子刺鼻腥氣直撲而來,皺著眉偏過頭去,直覺的想拒絕。
“喝了它,頭就不疼了。容兒乖。”他像是哄孩子般的哄著。
漫夭盯著他端著藥碗的手,有些發愣,這是第三個喂喝藥的男子,第一個是傅籌,第二個是無憂,第三個是他,來到這個世界六年,與這三個男人糾纏不斷,他們都曾傷過,卻又都是真心著,而,從來不貪心,只想要一份就足夠。
端過藥碗,屏息飲下,當真是苦之極。遞回藥碗,瞥見他抬手時袖下,蒼白的手腕間一道被利刃割破的未來得及理的傷口還在流。從眼前劃下,一道凄艷的直線,而分明聞到了那沾帶腥氣的苦藥味。
心中一驚,震的抬頭他,“這藥里……是不是有你的?”
啟云帝怔了怔,眸一閃,沒有回答。
漫夭子僵住,竟然喝了他的?!頓覺胃里一陣翻涌,那腥氣在鼻尖久久不散,俯了子連連干嘔,痛苦的憋紅了臉。好端端的為什麼要把他的放進藥里?難道他的能解上“天命”之毒?
啟云帝順了順后背,等平復了,才遞給一杯清水,待喝完,溫笑道:“服了藥就睡吧。”說罷扶躺下,替蓋了薄被。雖說已是六月天,但這里的天氣并不算太熱。
他做完這一切,端著碗出去了。
漫夭歪過頭,看著他清瘦的背影,心里說不出是什麼滋味。
該如何看待這個人?已經不知道了。
睜著眼睛看天花板,心中喃喃道:“皇兄,你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為什麼一邊置我于死地,一邊又用自己的命來救我?”
那麼多的謀詭計,他想要什麼,不懂。如果說他有爭霸天下的野心,那麼,一個眼中只有江山權勢的野心家,怎麼會跟一個子到這麼一個鄉村來蓋房子、種花、植樹?如果他沒有野心,那他又為何利用,侵占臨天國,將推死路?假如,他知道已經不再是那個真正的容樂,他又會如何?還會以相救嗎?或者干脆掐死。
帶著無數的疑問,在藥的作用下,沉沉睡去。
這個村子,他們一住便是四個月,這四個月里,啟云帝對好極了,除了不放離開以外,其它的,想做什麼他都會依著,對呵護備至。而他的咳嗽日益嚴重,不只眼角流,鼻也常見了,而嗜睡的病反倒有所減輕。
猜你喜歡
-
完結197 章

花重錦官城
澜王世子蔺效与道观俗家弟子瞿沁瑶在妖魔作祟的山中相识,之后一起解决长安街头巷尾的各类诡异事件,并在这个过程中相知相爱的故事。本文共六卷,每卷出现一个妖怪或鬼物
58.3萬字8 10242 -
完結480 章
首輔家的美食小辣妻
現代女強人,21世紀頂級廚神,一朝穿越成了軟弱無能受盡欺負的農婦,肚子裡還揣了一個崽崽? 外有白蓮花對她丈夫虎視眈眈,內有妯娌一心想謀她財產? 來一個打一個,來一雙打一雙,蘇糯勢要農婦翻身把家當。 順便搖身一變成了當國首富,大將軍的親妹妹,無人敢動。 但是某個被和離的首鋪大人卻總糾纏著她...... 寶寶:娘親娘親,那個總追著我們的流浪漢是誰呀? 蘇糯:哦,那是你爹。 眾侍衛們:...... 首鋪大人,你這是何必啊!
90.3萬字7.73 76746 -
連載52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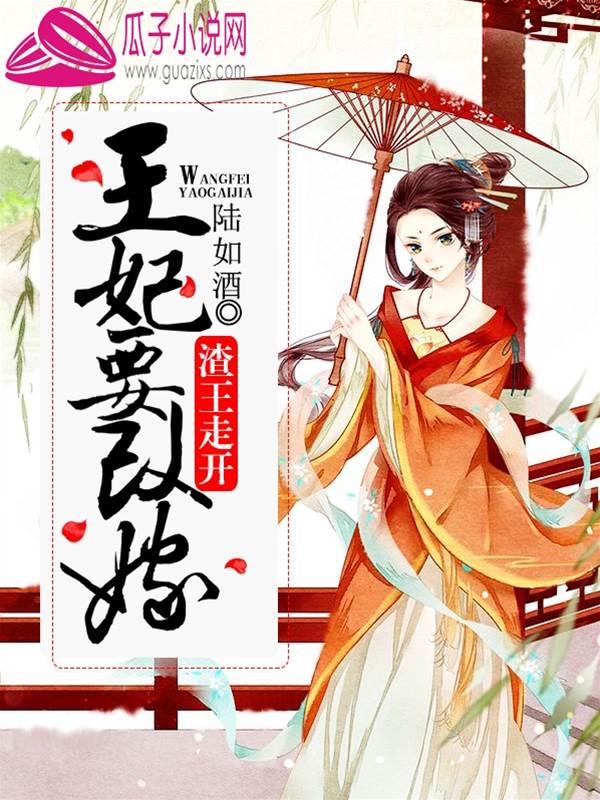
渣王走開:王妃要改嫁蘇妙妗季承翊
蘇妙,世界著名女總裁,好不容易擠出時間度個假,卻遭遇遊輪失事,一朝清醒成為了睿王府不受寵的傻王妃,頭破血流昏倒在地都沒有人管。世人皆知,相府嫡長女蘇妙妗,懦弱狹隘,除了一張臉,簡直是個毫無實處的廢物!蘇妙妗笑了:老娘天下最美!我有顏值我人性!“王妃,王爺今晚又宿在側妃那裏了!”“哦。”某人頭也不抬,清點著自己的小金庫。“王妃,您的庶妹聲稱懷了王爺的骨肉!”“知道了。”某人吹了吹新做的指甲,麵不改色。“王妃,王爺今晚宣您,已經往這邊過來啦!”“什麼!”某人大驚失色:“快,為我梳妝打扮,畫的越醜越好……”某王爺:……
99.7萬字8 1278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