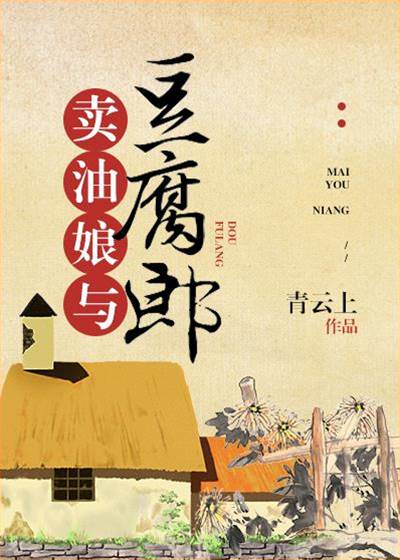《女配不入愛河,瘋批非要她負責》 第36章 撞目標了
被這麽兌,裴鶴昭竟也不生氣:“抱歉,我的眼神確實自就不大好。”
趙清寧哽住。
真誠是必殺技是吧?
看出的無語,裴鶴昭忍不住一笑,同時用折扇擋開蕭澤淵的劍:“澤淵,拿劍對著姑娘家可不好,於禮法不合。”
蕭澤淵垂下眼睫,利落將劍收起。
陳晉寶這才鬆了口氣。
要不是有裴鶴昭,怕是蕭澤淵這廝真要手。
趙清寧切了一聲,要不是裴鶴昭出來搗,還真想看看蕭澤淵如何收場。
似乎是不願意與他們多說,蕭澤淵轉往山下走。
裴鶴昭很是友好:“趙小姐,不如一起下山?”
趙清寧點頭:“可以啊,我可不像別人那樣,自作多以為你跟著我。”
說這話的時候超大聲,生怕前麵的人聽不見。
蕭澤淵腳步一頓,片刻後下心中怒火,繼續下山。
裴鶴昭笑笑:“你怎麽知道,我不是在跟著你呢?”
實際上,他還真是跟著下山的。
他覺得趙清寧跟從前相比,有意思多了。
趙清寧神態自若:“裴世子,好奇心會害死貓,做人還是不要太好奇比較好。”
可不會自的以為裴鶴昭是看上了。
從這個人屢次試探來看,他大概是覺得自己變化太大,像是變了個人,才有所懷疑。
不過趙清寧一點不擔心,畢竟是換了個靈魂,還是原主的。
裴鶴昭要是能查出來才怪。
丟下那句話,踏步往山下走,陸景寒下意識跟上。
裴鶴昭挑眉,隨即慢悠悠跟在他們後麵。
一路走來,他發現趙清寧對陸景寒十分照顧。
路邊,趙清寧把自己的帕子遞給陸景寒:“小九,累不累?要不要汗?”
陸景寒剛想接過,又回了手:“我不累。”
他如何能用的帕子。
Advertisement
這麽好的錦帕,不要被他給糟蹋了。
趙清寧沒有注意到他的小心思,繼續下山。
裴鶴昭將一切看在眼裏,隻覺得對陸景寒好過頭了。
如果說是長公主要扶持九皇子,趙清寧對他好倒也無可厚非,但也不至於這麽照顧,帕子這種私,也給他用。
他帶著疑,一路跟著趙清寧。
趙清寧了頭上的汗,看向陳晉寶:“下次出來玩如果還是爬山,就當我死了吧。”
陳晉寶:“呸呸呸,別說不吉利的話。”
趙清寧翻了個白眼,是真累啊。
好在總算是快到山腳了。
“救命啊!來人啊!”
忽地不遠傳來一道呼救的聲音,聽著還是個孩子,趙清寧瞬間打起神,往那個方向跑去。
繞過彎道,看到一個孩子,正被人挾持。
剛想讓陳晉寶救人,結果那子就轉過來了。
薛雲初楚楚可憐地看著眼前的蕭澤淵:“蕭公子,救我。”
後,拿著大刀的土匪怒吼:“退後,不然我殺了這丫頭!”
這悉的臺詞……
趙清寧狐疑地看去,一張著絡腮胡的悉的麵孔映眼簾。
正是之前上山時,陳晉寶雇來的土匪頭子。
趙清寧:“……”
陳晉寶也發現了:“那不是我找的人嗎?”
合著人家真還有別的生意啊。
土匪頭子在看到蕭澤淵的時候愣了一下,總覺得這小子有點眼,等看到他後的趙清寧與陳晉寶時,傻眼了。
上一單雇主英雄救的目標,跟這一單的撞上了。
薛雲初淚眼朦朧,等著蕭澤淵出手救。
好不容易打聽到蕭澤淵要來青雲山,本想來個偶遇,結果在山腳,遇到了這個吆喝做打劫生意的人。
一問才知道,原來他是假裝土匪打劫,以此來製造英雄救佳話的。
Advertisement
“小姐,俺們兄弟都是專業的,包你滿意,我保證你那小郎君救你之後,你們二人必將投意合。”
話本裏,都是這麽寫的。
於是心了,花十兩銀子雇了他們,然後專門在下山路上候著,果不其然就等來了蕭澤淵。
薛雲初心中歡喜,等著他而出救自己。
陳晉寶下意識就想跟那土匪頭子打個招呼,趙清寧眼疾手快攔住了他:“幹什麽,好好看戲。”
他立馬安分了。
土匪頭子見他們沒有拆穿他的意思,忍著尷尬念出臺詞:“小子,你想救,就得先……”
蕭澤淵打斷他的話,淡淡開口:“我不想救,你隨意。”
土匪:“……”
這小公子太冷了吧?
薛雲初也懵了,反應過來後淒淒慘慘道:“蕭公子,我們兩家也有,你難道忍心看我死於匪徒之手嗎?”
蕭澤淵看了一眼,而後,徑直離去。
薛雲初:“……”
陳晉寶回過神來:“老大,我才發現原來找人假扮劫匪這麽傻。”
看薛雲初那矯造作的模樣,與平時霸道行事相差太多,他都快吐了,幸好他老大當時沒這樣。
趙清寧悠然:“我也沒想到有人跟你蠢到一起去了。”
這青雲山在皇城裏,又多是達顯貴來玩,用腳趾頭想想都知道怎麽可能會有土匪啊。
往日這土匪能做生意,那是因為人家兩相悅,就差捅破窗戶紙,男的樂意上鉤表現自己的能力而已。
蕭澤淵隻會喜歡薑知意,哪裏會救他們。
陳晉寶歎口氣:“該說不說,這麽傻的事兒,我還花了十兩銀子呢。”
趙清寧挑眉,想起近日來,薛雲初在啟辰殿中也曾多次怪氣,忽地有了新的主意:“你想不想,把這十兩銀子賺回來?”
Advertisement
“想,當然想。”
他零用錢本來就不夠用了。
“那就看我的。”
薛雲初惱怒不已,剛想責怪這人演的不行,就聽有人高聲道:“慢著!”
抬眸,就看到了趙清寧,悠然走過來:“你剛說,怎麽才能救?”
見了,薛雲初厭惡地皺眉。
在啟辰殿,第一討厭薑知意,第二討厭趙清寧,從前兩個人關係就不好。
因為雖然出高貴,但總是矮趙清寧一頭,更別提進了啟辰殿,那些人都想跟趙清寧做朋友,卻沒多人跟搭話。
不就是長公主的兒嘛,有什麽大不了。
剛想說自己用不著趙清寧管,這也不是真土匪,卻又看到了後的裴鶴昭。
裴世子清風霽月,也是京中貴的夢中人。
薛雲初雖然喜歡的是蕭澤淵,但若是裴鶴昭出手救,倒也不錯。
於是又變回那副可憐模樣:“救命。”
雖喊著救命,目卻是一直看著裴鶴昭。
而前的趙清寧,卻沒得到一個眼神。
不過趙清寧並不在意,看向那土匪,眼神示意一番,而後道:“怎麽才能救?”
土匪注意到手上錢的小作,咳了兩聲:“給我十兩銀子,我就放了。”
趙清寧拔高聲音:“什麽?十兩?你知不知道你綁的是誰?這可是薛家嫡,才十兩?你辱誰呢?”
土匪:“……”
好,他懂了。
“給我一百兩,不然我殺了!”
趙清寧滿意地點點頭:“這才對嘛。”
說著拉著秋荷走到一邊,兩個人竊竊私語了半天。
薛雲初看向裴鶴昭:“裴世子,救我。”
裴鶴昭歎口氣:“薛小姐,在下也想救你,但今日出門沒帶那麽多錢啊。不過有趙小姐,你不會有事的。”
薛雲初咬牙,恨不得馬上推開土匪恢複自由,可又怕裴鶴昭看出破綻,隻能繼續裝可憐。
Advertisement
良久,趙清寧回來了,扔了一個錦袋過去:“拿錢,放人。”
那沉甸甸的錦袋讓土匪頭子目一亮,迅速收好,而後把薛雲初一推,就離開了。
陳晉寶快急死了:“小九,你說老大是不是腦子有問題?薛雲初跟關係又不好,幹嘛要拿一百兩救?”
陸景寒沒說話。
他剛才看了一眼,那錦袋裏塞得好像不是銀子。
眼看著自己的計劃沒有功,薛雲初勉強笑笑,看向裴鶴昭:“多謝裴世子。”
“喂,薛雲初,救你的人是我,你謝他幹什麽?”趙清寧挑眉看。
薛雲初冷哼一聲:“本小姐樂意。”
說著轉就要走,結果被趙清寧拉住:“慢著,你還沒給錢呢,想去哪兒?”
薛雲初皺眉看:“什麽錢?”
“贖金啊。”趙清寧攤手,“剛才我可是給了土匪一百兩才救的你,這錢你不得給我?”
薛雲初差點沒氣吐。
就知道趙清寧沒那麽好心。
“我又沒讓你救。”
“你這是不給了?好啊你,薛雲初,我大發慈悲救你,你居然還賴賬。”
趙清寧氣憤不已,“你這不是欺負老實人嗎?等我回了書院,定要讓夫子好好教育你。讓大家看看,你是個無賴。”
薛雲初氣的牙都咬碎了。
就不該找人假扮土匪,綁架自己!
眼看著趙清寧糾纏不休,裴鶴昭又在後看著,不願意為了一百兩銀子丟人,更不想回去告狀,讓自己被同窗指指點點。
於是從腰間錢袋出銀票,扔在趙清寧麵前:“給你行了吧!”
堂堂公主之,怎麽這麽寒酸!
趙清寧笑彎了眼,誰會不喜歡錢。
看著薛雲初怒氣衝衝下山,高聲喊到:“薛雲初,下次被綁架了,我還救你。”
薛雲初加快腳步,恨不得飛下山。
看著的背影,趙清寧樂滋滋。
就知道薛雲初的腦子不好使。
顧著裝弱,連那錦囊裏裝的是石子都看不出來。
不過那土匪也配合演的很出,往裏麵放了些碎銀,就當他辛苦費了。
趙清寧轉頭,看向陳晉寶:“喏,這不就給你掙回來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11 章

嫡長孫
趙長寧是世家大族的嫡長孫,被選拔入嚴苛的大理寺為官。 環境艱苦,對手眾多,她小心謹慎,步步艱難。 直到有一天,她的冷酷上司,惡毒對手,甚至是虎視眈眈的庶弟都知道了自己的秘密…… 咦,怎麼感覺他們都一反常態,比自己還要小心翼翼,日常接觸變得怪怪的。 ———————— 大理寺論壇熱帖: 我對手/下屬/突然變成女孩紙了,我現在跟她說話接觸變得很緊張很羞澀該怎麼辦,在線等挺急的 —————— 正式版:能科舉,能入仕,能當官。她是家中的頂梁柱,老太太眼里最重視的第一人,所有的嫡小姐和姨娘都要對她客客氣氣的。她也不用宅斗, 因為她是嫡長孫。 ——————————————————————————— 本文甜寵,蘇文! 1:人物復雜,站男主請慎重。 2:蘇文作者筆下都是蘇文,滿朝文武愛長孫,雷此可撤退。 3:背景大明,請勿嚴格考據。
50.2萬字8.18 16279 -
完結344 章

邪王霸寵:逆天六小姐
世人皆知,君府六小姐靈力全無,廢材草包,花癡成性;世人皆知,當今景王天賦異禀,風姿卓越,邪魅冷情;她,君府草包六小姐,世人辱她、罵她、唾棄她。他,北辰皇室景王爺,世人敬他、怕他、仰望他。他們雲泥之別。然而,冥冥之中,早有注定:她,是他的‘天情’。
90.7萬字8 59938 -
完結14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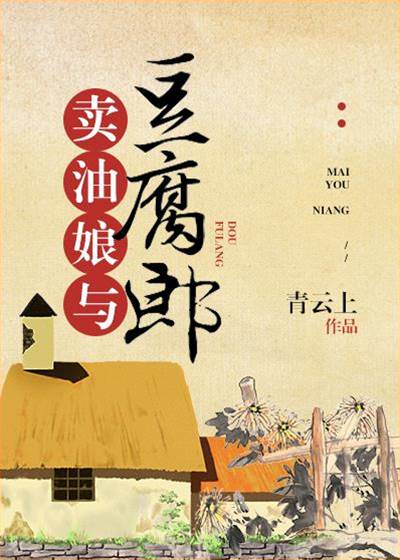
賣油娘與豆腐郎
每天早上6點準時更新,風雨無阻~ 失父之後,梅香不再整日龜縮在家做飯繡花,開始下田地、管油坊,打退了許多想來占便宜的豺狼。 威名大盛的梅香,從此活得痛快敞亮,也因此被長舌婦們說三道四,最終和未婚夫大路朝天、各走一邊。 豆腐郎黃茂林搓搓手,梅香,嫁給我好不好,我就缺個你這樣潑辣能幹的婆娘,跟我一起防備我那一肚子心眼的後娘。 梅香:我才不要天天跟你吃豆腐渣! 茂林:不不不
77.7萬字8 13071 -
完結358 章

嬌妾出墻
閬州知府顧決身份高貴,父權母盛,端方持穩,是上京城人人稱道的君子。便是這樣的人,卻在兩府聯姻之日,做出勾纏嬌女的事。男人手撫懷中女子臉頰,音色沉啞問:“叫我什麼,嗯?”“兄長……”姻親之時,外面百般清淑的未婚妻又怎比得上懷中溫柔小意的憐嬌?——-桑矜長得溫媚昳麗,不冒尖出頭,乖乖巧巧當顧府備受折磨的孤女。寄人籬下,她懂得遮掩鋒芒,能躺便躺,似乎在她眼中沒有什麼在意。唯那個男人。他是清輝月,他是盛世顏,同時他也是她的目標,是她要牢牢抓住又用完丟棄的人。情淡人涼,女子揮揮衣袖起身離去,獨留為情傷神的男人停留原地。顧決:“桑矜,你到底有沒有心?”桑矜:“別搞笑了,渣滓也配談心……”
63.8萬字8.18 404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