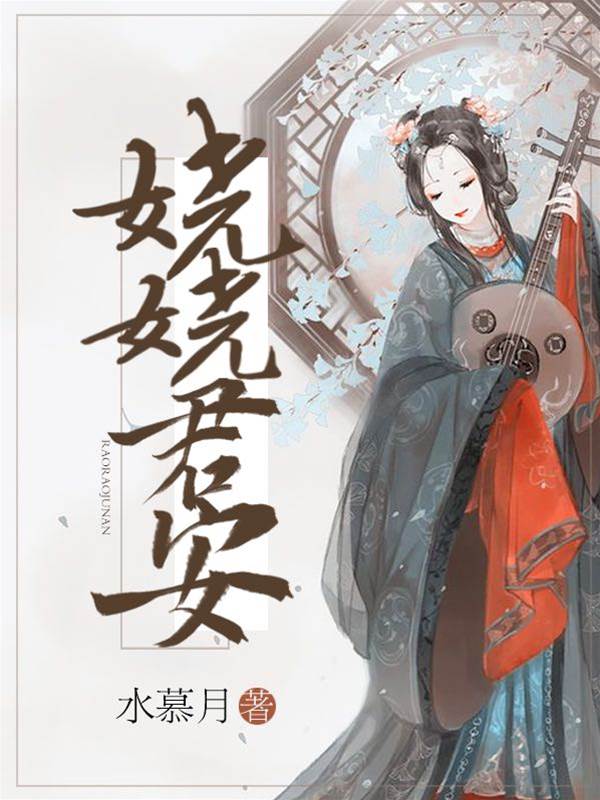《青梅難哄》 第九十三章 鍾粹宮
自燕懷澤獲封齊王,賜婚姑蘇雲氏之雲妙瑛後,純妃便一改常態,鮮在外人麵前麵。
為四妃之首,又育有皇長子和公主的純妃,乃是宮中人人豔羨的對象。雖已不似當年深聖寵,但其地位依舊無法搖。
如此反常的行為,讓宮中許多人不著頭腦。原以為會借機尋個由頭大鬧一場,可暗自觀察留心了好一陣,仍然未見任何靜。
似乎察覺到眾妃隔岸觀火的態度,純妃以子抱恙為由,告假辭了請安。
曾經人來人往的鍾粹宮,如今門可羅雀。
清晨的寒氣未消,坤寧宮裏便坐滿了前來請安的後宮諸豔。
皇後的子大不如前,愈顯頹勢,為不使親近之人擔憂,瞞天過海,唯有伺候的婧姑姑與江太醫知曉。
這天子不適,到得晚了些,然而才走至珠簾後,就聽淑妃與壽貴人在高談闊論純妃有關的事:“依我看,純妃是積鬱疾,心火難消才閉門謝客的,否則這會兒鍾粹宮的門檻早給人踏破了。”
壽貴人隨其後接道:“妹妹我前幾日正巧在花園見過純妃娘娘,聽說是出來散心的,瞧著麵紅潤,倒未能看出任何不妥啊。”
“哼,這就是你孤陋寡聞了,純妃向來是個死要麵子的——”
話音未落,皇後便掀開簾子走了出去,目如炬,直直落在淑妃上,看得渾汗倒豎。
在場眾妃亦被皇後的突然現嚇了一跳,反應過來後紛紛朝行禮。
麵平靜從容,輕輕抬手示意們平,緩緩道:“近來宮中瑣事繁多,不乏出現些流言蜚語,本宮也能理解。隻不過——需懂得適可而止。”
Advertisement
後宮之主的威嚴不可小覷,眼尾一掃,餘下的人便噤若寒蟬。
請安結束,妃嬪們一一告退。自皇後出言提點以來,整個早晨都沒怎麽說話的淑妃與壽貴人走在一塊,待離其他人較遠後才低聲談。
“姐姐,皇後今日是怎麽了?這宮中要說誰和純妃的關係最差,定非皇後娘娘莫屬,沒想到娘娘竟也會有幫純妃說話的時候,真是太打西邊出來了。”
淑妃往後一瞥,小腰一扭一扭,抬手了鬢角:“本宮也猜不皇後在想什麽,但我們又能如何?這後位坐得比花園的石墩子還穩當,就連當年純妃承寵最盛時都未能撼分毫。難道年夫妻,如此深意切?”
“可妹妹我瞧著,聖上除了必要的那幾日,未曾時時關切皇後娘娘呀?且近段時間國事繁忙,聖上都許久沒翻牌子了。”
聞言,淑妃姿態居高臨下地掃一眼,幽幽道:“你才宮半年,多得是你不知道的事兒。倘若你有福氣活到後頭,自然會明白本宮的意思。”
壽貴人到底年輕,聽出淑妃的意思後,姿態更為恭敬,二人一前一後,漸漸遠去。
坤寧宮,皇後仍八風不地坐在上首,沉默不語,似乎正著緒。良久,才對著空無一人的宮殿吞吐一口濁氣:“隨本宮去鍾粹宮。”
……
純妃近來的況並未同外人猜測那般水深火熱,反倒極其安逸,仿佛又回到進宮前,仍是閨閣的那段時日。
彼時年方十三,穿過府一眼不到頭的長廊,就能瞧見岸芷汀蘭的韓逋——那是自時起便慕得年,非但才高八鬥,年有為,憑借自學識在朝中聲名鵲起,對更是極盡照顧。
Advertisement
每每見從遠提奔來,韓逋都會無奈又滿含寵溺地提醒道:“鰩娘,你慢些,仔細摔倒了。”
而總笑著撲韓逋懷中,被他穩穩接下後,便甜甜地喚:“韓哥哥!”
父親乃韓逋的恩師之一,二人亦同青梅竹馬,相知相許。
本以為及笄後,韓逋上門提親,他們便能一生相守,恩共度。
誰知天不遂人意,暴雨將至時,如同驚雷般劈在腦門上將撕碎的,是一道宮的旨意。
說造化弄人太可笑了,實在過於可笑。
明明就差一點了不是嗎?
經年已逝,年夢碎,他不再是岸芷汀蘭的韓哥哥,而是韓丞相;也不再是天真無邪的鰩娘,搖一變,為了寵冠後宮的純妃。
後來亦見過許多青梅竹馬,譬如皇後的寶貝兒子和鎮安侯家的丫頭片子,每當瞧見他們向彼此的眼神時,都會瞬間將純妃的回憶拉至最好的那段年華。
如今回想年荒唐又可笑的意氣,心中有悲涼、有怨恨,更多的是憾。
憑什麽他們要生生錯過?
世上那麽多人,憑什麽,偏偏是和韓逋?
這個問題,純妃始終沒能得到答案,如今卻不需要了。
在天子的眼皮底下,大膽盛放生命中本就不屬於他的芳華,圓與韓逋多年的意難平。
背著仁安帝私通,甚至刻意間離他與皇後關係之事本不值一提,多年來與仁安帝又有幾分真,幾分算計?要讓天家人吃盡苦果,嚐到被報複的滋味。
外頭宮人高喊“皇後駕到”時,純妃正學著韓逋的樣子臨摹最的詩句。
“年一相逢,投意已合,柳邊栓駿馬,酒為君飲。”
Advertisement
腳步聲在後戛然而止。
純妃回首,角掛著真切的笑意:“娘娘你聽,此詩可好?”
皇後並不吃這套,冷眼旁觀片刻後,沉聲命令所有人退下。
“純妃,本宮有事要告訴你。”
拾起團扇,挑眉,瞧著心十分愉悅的樣子,甚至笑著請皇後坐下。
曾經兩人每每麵便劍拔弩張、冷嘲熱諷的樣子仿佛已不複存在。
“皇後娘娘但說無妨。”
“闔宮都在傳,你心灰意冷,打算躲在此地了卻殘生,本宮卻不這麽認為。”周威儀得人不過氣來,就連此刻的純妃亦不例外,“純妃,你與韓丞相這段茍且生,得過且過的日子,究竟想持續到何時?你覺得自己勝券在握,便可放心讓韓逋助齊王去奪嫡了?”
此話一出,宛若一場兀自卷起的狂風,驚純妃所有刻意掩藏在心底的。
“什麽意思?”好似被人及逆鱗般,眸一凜,“你要準備做什麽?”
“你們以為,聖上不曉得你與韓丞相的小作?”皇後冷笑,“他懶得拆穿罷了,但本宮想,他總有一日會的。那些你們自認為一葉障目的事,其實在他麵前本不足為奇。”
三言兩語,將好不容易才重新拚湊的夢重新打碎。
越深想越後怕,雖早料到會有這麽一日,但沒料到來得如此之快。
他們分明已經千分小心、萬般仔細,藏得這樣好了,為何還是暴了?
來不及細想,皇後又道:“看在相識多年的份上,本宮提醒你一句,早日收手,別再心存僥幸。”
純妃神森然,指尖陣陣發,緘默不語。
“當然,若你死不改,本宮也樂得見你玩火自焚,隻是給你個忠告——休要我兒和裴筠庭,否則,本宮要韓逋,連同你與他的孩子一起陪葬!”
Advertisement
“你究竟知道些什麽!”純妃怒目圓睜,吼道。
“聖上知道什麽,本宮便也知道什麽。”隔岸觀火,撂下最後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後便拂袖而去,“希你不會因此後悔。好自為之吧。”
待再也瞧不見的影,純妃才輕聲答道:
“有得悔麽?”
……
返回坤寧宮的路上,皇後視線不由自主地朝遠眺,終究未能如願看到除紅牆綠瓦以外的事,就連鳥兒的翅膀也沒有。
畢竟皇宮這樣森的地方,心向自由的飛鳥怎會甘願停留呢?
自嘲一笑,收回目:“聖上今日可有傳召淮臨?”
“似乎未曾。”
皇後不置可否,靠在奢華的轎攆上,抬眸將湛藍的蒼穹映眼底,“去承乾殿吧。”
“是。”
猜你喜歡
-
完結389 章

農門姐弟不簡單
穿越而來,倒霉透頂,原身爹爹戰亂而死,送書信回家後,身懷六甲的娘親一聽原地發作,立即生產,結果難產大出血而亡。 謝繁星看著一個個餓的瘦骨嶙峋還有嗷嗷待哺的小弟,她擼起袖子就是乾,看著滿山遍野沒人吃的菜,有這些東西吃,還會餓肚子、會瘦成這樣? 本以為她這是要帶著弟妹努力過活,改變生活過上好日子的,結果,弟妹沒一個簡單的。 本文又名《弟妹不簡單》《弟妹養成記》《弟妹都是大佬》《全家都是吃貨》
70.4萬字8.18 36131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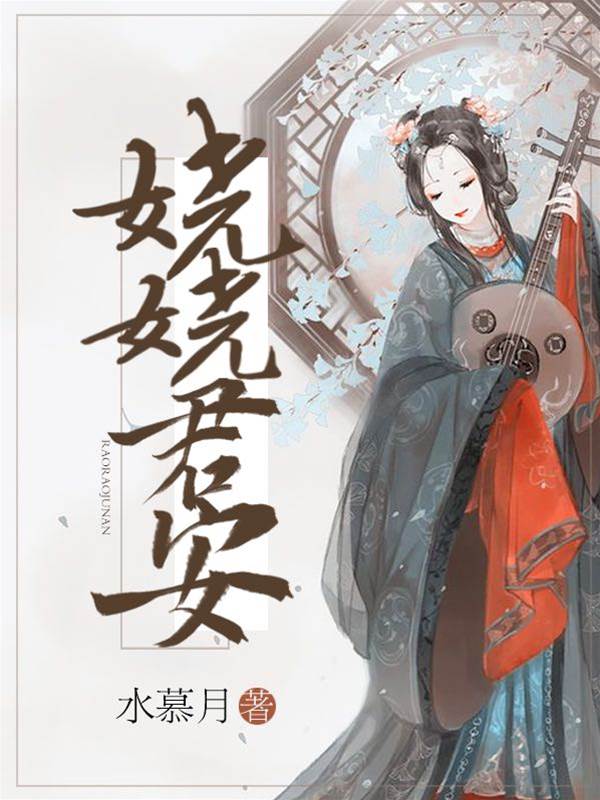
嬈嬈君安
原想著今生再無瓜葛,可那驚馬的剎那芳華間,一切又回到了起點,今生他耍了點小心機,在守護她的道路上,先插了隊,江山要,她也絕不放棄。說好的太子斷袖呢!怎麼動不動就要把自己撲倒?說好的太子殘暴呢!這整天獻溫情的又是誰?誰說東宮的鏡臺不好,那些美男子可賞心悅目了,什麼?東宮還可以在外麵開府,殿下求你了,臣妾可舍不得鏡臺了。
16.6萬字8 14030 -
完結171 章

錯撿瘋犬后
病嬌太子(齊褚)VS聰慧嬌女(許念),堰都新帝齊褚,生得一張美面,卻心狠手辣,陰鷙暴虐,殺兄弒父登上高位。一生無所懼,亦無德所制,瘋得毫無人性。虞王齊玹,他的孿生兄長,皎皎如月,最是溫潤良善之人。只因相貌相似,就被他毀之容貌,折磨致死。為求活命,虞王妃許念被迫委身于他。不過幾年,便香消玉殞。一朝重生,許念仍是國公府嬌女,她不知道齊褚在何處,卻先遇到前世短命夫君虞王齊玹。他流落在外,滿身血污,被人套上鎖鏈,按于泥污之中,奮力掙扎。想到他前世儒雅溫良風貌,若是成君,必能好過泯滅人性,大開殺戒的齊褚。許念把他撿回府中,噓寒問暖,百般照料,他也聽話乖巧,恰到好處地長成了許念希望的樣子。可那雙朗目卻始終透不進光,幽深攝人,教著教著,事情也越發詭異起來,嗜血冰冷的眼神,怎麼那麼像未來暴君齊褚呢?群狼環伺,野狗欺辱時,齊褚遇到了許念,她伸出手,擦干凈他指尖的血污,讓他嘗到了世間的第一份好。他用著齊玹的名頭,精準偽裝成許念最喜歡的樣子。血腥臟晦藏在假皮之下,他愿意一直裝下去。可有一天,真正的齊玹來了,許念嚴詞厲色地趕他走。天光暗了,陰郁的狼張開獠牙。齊褚沉著眸伸出手:“念念,過來!”
26萬字8 7046 -
完結232 章

陛下輕點罰,宮女她說懷了你的崽
為了活命,我爬上龍床。皇上不喜,但念在肌膚之親,勉強保了我一條性命。他每回瞧我,都是冷冷淡淡,嘲弄地斥一聲“蠢死了。”我垂頭不語,謹記自己的身份,從不僭越。堂堂九五至尊,又怎會在意低賤的宮婢呢?
43.7萬字8.18 534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