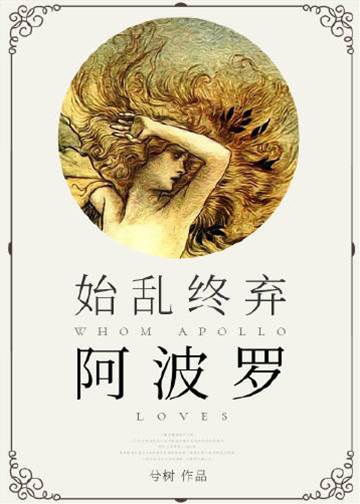《暴君是個女兒奴》 第474章 撫平姒妧心頭傷
/>
冥北幽取下姒玄的麵,狹長的眼瞼裏,氤氳著閉的雙眼,長睫微卷。
如今執蠱毒發,又被人設下著攝魂咒,他到底該如何是好?
別看此刻安靜,一生氣時,言詞簡直令人瞬間崩潰,印象盡毀,活像個十八層地獄裏殺上人間來的勾魂惡霸似的。
從前隻覺得一張小兒「拉拉」沒完沒了地在說話,吵得他頭疼。
可此刻,在他腦海裏,心裏,眼底,這容清絕世間,水湄之姿娉婷,剪水罩雙眸,清醇之氣氤氳,回鼻繞朱,冷傲之質嬈,瑩珠璣,傾詞歎之兮,絕於天地,足以引得浮生,赴萬重險。
“姒玄,吾心有一囯,疆土無垠,卻僅有一人。”
“這一人,可不死不滅,然,心如止水。”
“所以,你鑿開了封閉的城,怎能說來就來,說走就走?”
“你一定會平安無事,一定會!”
他輕輕地握住了的微涼的手,在手背上,落下淺淺的一個吻。
的手,好生弱,好生小巧,像是一隻初生的狐兒。
說起來,帝禹的王後,便是九尾天狐:。
上也有妖神脈,想要救,或許還有一個辦法!
“令狐!”
“在!”
“速速布下羅天陣,沒有本侯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出!”
“諾!”
冥北幽劍指一揮,指尖一抹流劃過,沒姒玄眉間的花鈿。
隨即,他長臂一揮,一座玉臺出現在麵前,再將姒玄輕地抱起端坐玉臺上,自己坐在了的對麵。
而後,冥北幽長手飛旋,一串繁複的手印,化作一個個流道印,排列一個八卦圖,將姒玄和冥北幽罩在其中,劃分。
*
而另一邊,姒玄還在與姒妧聊人生,夏朝的覆滅是曆史必經的過程,可就算如此,也想為自家老爹博得一線生機,免他殘之痛,免他背負曆史數千年的罵名,或許這種事隻是空談,可不去一試,覺得有愧於暴君對的疼與守護。
Advertisement
腦子裏不斷閃現出一個字,「桀」,此字於自家老爹來說,真正的含義到底是什麽?
“孤也想出去,隻是他將孤的神魂靈抅來,又設了那陣法與結界。”一危機竄上心頭:不行,得趕想個法子,從這裏逃出去,看了看姒妧,一副慵懶的神態,帶著無奈和順勢而為的莫奈何,道:“二皇姐,你知道什麽做「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嗎?指的就是像孤這樣兒,有想法,沒有,什麽都做不了!”
“你來找我,是想讓我幫你?”姒妧眼珠子一甩,斜睨著姒玄,“你別忘了,你上回還當眾了我的服,讓我丟盡麵,我還沒找你算賬呢,你不會以為我會那麽大度,不計前嫌地去幫你吧?”
“對謔,咂!”姒玄眨了眨眼,手指放在畔,“那要不,你現在孤的服,咱們不就兩清了?”
“姒玄!”姒妧氣急,指著大門,怒聲道:“你給我滾出去!”
先不說本無法到一個神魂靈,就算是真的能到,有人家來看嗎?
最是討厭這副裝癡扮傻的模樣,明明是個腹黑狡詐的臭丫頭,姒妧越想越氣。
姒玄才不管姒妧怎麽罵,就一直賴在這裏,“二皇姐,你說,姒嫣和姒瑤現在在做什麽?”
“……”姒妧懶得理,幹脆躺倒在床榻上,用被子將自己和頭和腦的捂起來。
姒玄飄在隆起的小山包上,問道:“二皇姐,你說,父後後宮裏麵那麽多人,為何就咱們幾個子嗣?”
“……”姒妧。
幹脆也鑽進被褥裏,“二皇姐——”
“姒玄!”姒妧猛然掀開被褥,從床榻上站起來,「咚」一聲,腦袋撞到床頂上,痛得齜牙咧,“嘶~”
Advertisement
姒玄鴛鴦眼眨了眨,趕手,作勢要幫腦袋上的包,“嗨呀,二皇姐,怎麽這麽不小心呢?你看看你,這麽大了還躁躁的,痛痛飛、痛痛飛……”
“啊!”姒妧就這麽一直被折磨到月上中天,終於是撐不住了,苦著一張臉道:“姒玄,你可是嫡公主,要點臉行不?”
姒玄聞言,倏然一笑,“你是孤的姐姐,在姐姐麵前撒撒有什麽關係?”
“你明明知道,我——”姒妧聽罷,下意識出言想要辯上一句,既然姒玄憑著一氣息就能認出,找到,那與姒蓮之前說的話,肯定也被姒玄聽到了才是。
姒玄忽地揚起一手指,抵住了姒妧的瓣兒,衝著出了一個淺淺甜甜的笑容,“九州三千列國,都是炎黃脈,你我卻生在同一個時代,長在同一個家,能為姐妹,這是很神奇的緣分,所以,其它之事,何必計較那麽多?”
“你真的一點也不介意?”姒妧聽這麽說,再回想起往日還又癡又傻時的畫麵,心中五味雜陳。
姒玄大概能理解姒妧心中著的那刺,在心底悵悵地歎了一口氣:難怪這個姒妧自小對十分冷淡,可除了冷淡,還有一子嫌棄之外,卻從不曾出手傷過半分。
相比是姒嫣的假仁假義,背地裏夥同姒瑤算計,言語辱,一人唱紅臉,一人唱白臉,踩著獲得名和利,姒妧頂多就是在一旁,一副事不關己,冷眼相看的態度。
再回想起那日在皇家演武臺,故意出言挑釁,興許本不是真的要挑釁,再聯想到那日,出手羈押了曹晃兒,還有危嫋嫋,姒妧對說了一句:希你一直保持這樣的狀態……
Advertisement
,是希好起來吧?
這個看似戴著一層一層麵,偽裝的姑娘,在為了自己生母所做之事到愧疚,可又無法啟齒,所以,從前對冷漠,冷眼,冷酷,實則是恨鐵不鋼,恨爛泥扶不上牆?
卻輕笑,道:“父後說,九州子民皆是他的兒,你想要孤去介意什麽?”
“父…大…他、他真的這樣說?”姒妧心頭一酸,眼眶一熱,理智告訴,別去信,因那位在心裏,一直都是個殺伐天下的恐怖存在,怎可能說得出這樣溫的話來?
“真的。”姒玄肯定地點點頭,“所以,你千萬不要聽別人的擺布,那載羿本不是好人,你留在有窮國,會死得很慘。”
姒妧訝然,聽見姒玄這般關心,心頭一暖,眼眶裏莫名地酸,一層霧氣遮住了視線,忙轉過頭去,故作傲,冷冷地道:“反正我也無可去,上的也流失殆盡,注定活不過二十,死在哪裏都一樣。”
“二皇姐。”姒玄聽那般厭世的語氣,充滿了濃濃的悲戚,“每一個人,從出生那日起,便是獨立的個,生命,原本是平等的,隻是出生的份不同,作為一個人,我們應該有自己的思維方式,有責任為父母養老送終,有義務承擔家族使命,可人活一世,本就做不到盡善盡,連黃金玉都做不到人人喜歡,何況是人?”
姒妧木訥地著姒玄,眼底帶著疑,帶著追尋,還有幾許震驚,好像在問:這些話,是誰教你的?
“所以,選擇接命運的人,有智者,但都是弱者。”姒玄也側過頭,著姒妧,興許對來說,早死早解,不用再心理上的折磨和煎熬,未嚐不是一件好事。
Advertisement
可在姒玄的心裏,每一個生命,都是奇跡,怎能眼睜睜看自暴自棄?
“活著,才能更好地去修補曾經的過錯與憾,何況——那不是你的錯。”
“那,不是…我…的錯。”姒妧木訥的臉上,終於有了一容,口漸漸脹痛,頭哽咽,“那,不是我的……錯!”
隨即而來的是山雨來的焦灼,這些年來,一直背負著巨大的,這一刻,仿佛蓄積著某種沉重的傷痛,堅強的麵下,是一個飽摧殘的心,“嗚——”一抹淚水再也藏不住,奪眶而出。
姒玄默默地陪在邊,看著將這些年所有的委屈與悲哀都喧泄殆盡,為平心頭每一次過的傷。
翌日。
姒妧因為前夜被姒玄折騰了一晚上,哭得力氣全無,反而因為卸下心中的包袱而難得地睡了個飽。
等醒來時,破天荒地換下了素來喜的白,著一套玄,仍將頭發束在腦後,褪去端莊秀麗,換得一副英姿颯爽的大氣。
走在王宮,那張臉上帶著淡淡的笑,卻不再給人一種很悲涼的錯覺,眉眼多了幾分淡泊的氣息。
“姒玄,我把借給你,你可得爭氣點,趕從這裏逃出去!”姒妧的聲音,從自己的意識裏傳達到軀,這是主提出來的,讓姒玄附在的上,然後二人找機會,想辦法一起逃出去。
姐妹二人連夜想出了個好主意,那就是同用一副軀,一起離開這個鬼地方。
“二皇姐,你說的那個腰牌,要去哪裏領?”姒玄轉了一大圈,也沒找到姒妧說的那個地方。
“你怎麽這麽笨啊!”姒妧有些著急,“我都說了三遍了,從這裏往左,往左,你每次都往右,找得到才有個鬼!”
“難道沒有嗎?”
“我懶得跟你說,這回你一定要聽我的,我你怎麽走,你就怎麽走!”
“好好好,聽你的。”姒玄其實是故意走錯的,想看看這裏麵到底有什麽玄機,那陣法居然會如此強悍。
走了大半晌,姒玄也覺得差不多了,總算「順利」找到了褒服司,因為昨日姒妧換下了一套裳,那腰牌忘記取下來,褒服司的人正好準備給送來,這一來一回剛巧在途經太子府的岔道上見了。
取了令牌直徑前往出宮的門,卻見前方四頭白羊,脖頸上拴著碩大的金銅鈴鐺,上塗著朱砂紅,羊角上綁著大紅花,拉著一輛看起來喜慶的木箱車,從姒玄麵前走過。
忽而,卷起一縷風,吹得簾子翻飛。
姒玄下意識停下腳步,目探向車之人,隻見那羊車的子,一臉木然,蒼白的麵上卻被化了個酡紅酒醉的裝扮,一雙死寂的眼,大睜著,狀若惡鬼,呼吸都卑微得像個傀儡。
這氣息是:姒蓮。
在腦子裏,忽然閃過這個人的樣貌。
一直於遊魂狀態,木訥無的姒蓮,忽然像是被什麽驀地拉回了神智,陡然瞪大眼睛,眼球裏爬滿了紅,一把掀開車簾,著「姒妧」,此刻,上穿著腥紅的嫁,看似打扮的金貴奢華,實則全是俗氣的金銀,本與「夏後皇朝四公主」的份完全不匹配。
“二皇姐,二皇姐!”在羊車逐漸拉開們的距離時,姒蓮的頭探出了看看能抻出的窗口,朝「姒妧」所站的方向抓去,歇斯底裏地喊著,“他著要我嫁給一個又矮又的白發老翁,求求你,救我…救救我…”
隨著那聲音漸行漸遠,姒妧一聲不吭。
“你不打算救嗎?”姒玄問。
許時。
“人各有命,這是自找的。”
應道。
姒蓮著站在原地不為所的「姒妧」,一雙眼睛更添了幾分腥紅,一副破敗的子,力氣忽地被幹,上的嫁,紅若泣,映著初冬的,像是一把被點燃了的焚業火,而,像極了被困在業火中的飛蛾,眨眼之間便會被燒得灰飛煙滅。
早上,醒來時,邊躺著那老翁,自己一不掛,渾都是曖昧的痕跡,那一刻,心中最後一抹希,徹底被抹殺了。
做夢也沒有想到,年時一眼定終生的年,九州三千列國屈指可數的列強王儲之一,年輕一輩中的風雲人,在眾人眼裏,那般清冷孤傲,人品貴重的有窮國太子,竟然會對自己的未婚妻下如此狠手。
猜你喜歡
-
完結683 章

天才維修師
星歷1245年,機甲競技S級選手[sink]展露鋒芒,創下多項記錄,風光無限的他卻在獲得大滿貫后宣布退役,引得無數粉絲為之遺憾可惜。與此同年,KID基地戰隊機甲維修師因為違背聯盟規則被取消隊醫資格,基地老板不得已在聯盟發布招聘公告,瞬間就在…
199.6萬字8 10424 -
完結10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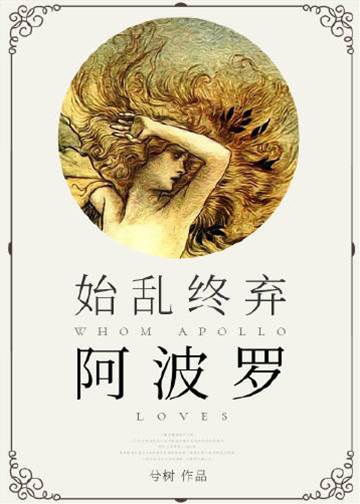
始亂終棄阿波羅后[希臘神話]
卡珊卓遭遇意外身故,一個自稱愛神的家伙說只要她愿意幫他懲戒傲慢的阿波羅,就可以獲得第二次生命。具體要怎麼懲戒?當然是騙走奧林波斯第一美男子的心再無情將其踐踏,讓他體會求而不得的痛苦,對愛的力量低頭。卡珊卓:怎麼看都是我賺了,好耶!…
30.2萬字8 975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