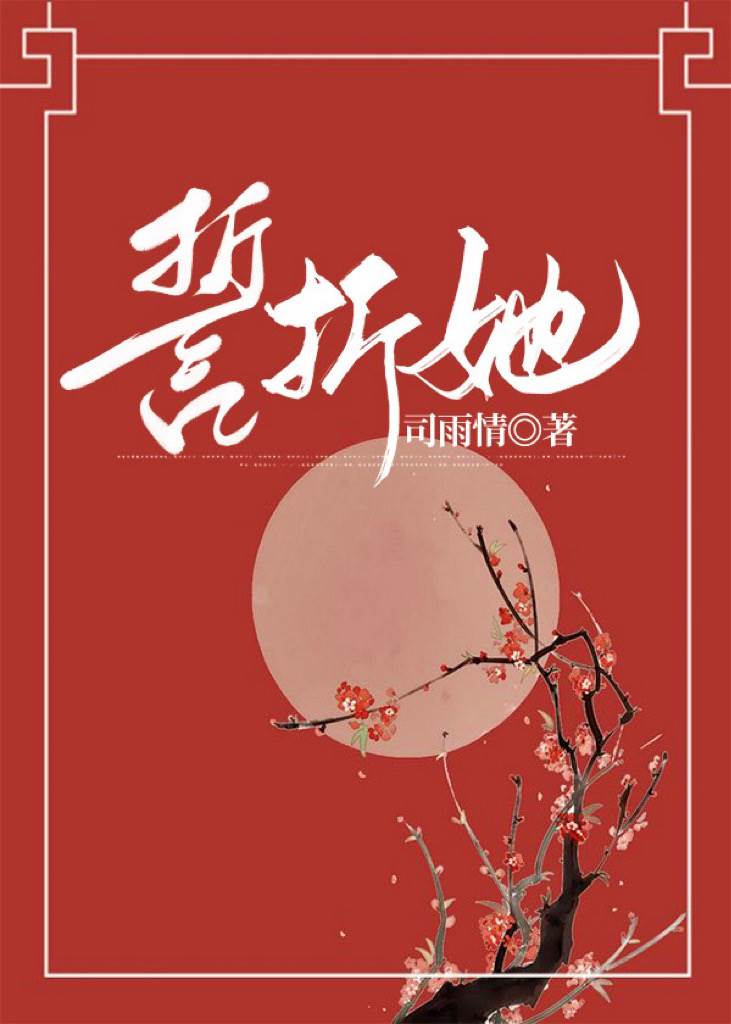《暴君納妃當日我孕吐了》 第85章 住步
窗子被關起,文瑾便沒那樣冷了。
“左邊這些都是我寫的。右邊這些并不是。你不會看的,對嗎。你為我打上細作烙印了。你必然以為我在垂死掙扎地狡辯。但我猜想你邊仍有細作,要多加警惕。”
“我邊的細作何止一二,每天揪出不知幾個。有勞你費心。你的演技真的很好。”
傅景桁蹙了蹙眉心,看著蒼白的面頰若有所思,思及苦百姓,便將自己心對文瑾的不忍收起了。
“撞在劍口上,用你所謂的義無反顧的,使朕生出惻之心。離間了朕與軍機以及國師,使其二人質疑朕不顧大局寵幸政敵,令智昏。你做到了。”
文瑾輕聲道“我…沒有要離間你與軍機。誠然,我家中有弟弟妹妹和,腹中有娃娃,有母仇未報,我貪生怕死。是有先發制人使你不忍之意。但我只是不想枉死…人都想活著,我肩膀上擔子重,我死不起,不行麼!”
傅景桁冷冷笑了笑,“朕已撤下林軍和押解車,并安排了死囚代你刑,你不會死了。驕傲嗎?朕清譽掃地,被罵昏君,險些敗名裂,卻沒有殺掉你。朕素來自詡不近人。卻為你一再破例。你是朕的政治污點,朕可悲嗎?”
“傅…”哦,原來是政治污點。
“朕一個字都不想聽你再說了。”傅景桁不悅地將文瑾的話語打斷,“你必然希文廣如切下我父親頭顱那樣,也切下我的。告訴你,朕不會輸的!文廣和蔣懷洲的命朕要定了。并非只有你們懂得離間。朕比你會。報復是這世上最簡單的事,因為報復的時候你不必顧及人世故,甚至可以不計后果。”
Advertisement
“我沒有想要他切下你的頭顱!冤枉!”文瑾隨即便沒有說話了,倒了杯溫茶遞給傅景桁,許久破罐子破摔“喝杯茶吧。我什麼都認了。我是細作,想切你頭,這些年我和那邊寫著信,出賣著你。不要怒了。一會兒頭又作痛了。好麼。”
“你!”
傅景桁將眼睛別開,沒有去接的溫茶,在這樣的況下,居然還在關心他。他已然…分不清是真還是假意了。和的讓他千瘡百孔。
張院判輕聲道“君上,瑾主兒臂膀雖然傷不致命,若不用藥的話,恢復會比較慢,但是用藥便會影響胎兒狀況。”
“我的
傷我清楚,沒事。”文瑾忙說,“不用藥了。沒有關系,孩子要。”
“是,蔣長林要!胳膊都要斷了都無所謂!就為了給他延續香火!”傅景桁隨手把文瑾倒的溫茶揮落在地了,茶杯碎了一地。
文瑾倏地出了兩眼淚,“傅長林。”
傅景桁冷笑,“蔣長林!文長林!興許不得你的房東哥也來足,凌長林!”
“是!”文瑾心口如刀絞,“我人盡可夫。長林他是百家姓!趙錢孫李,張王李趙,蔣文凌,獨獨不姓傅!”
莫乾見狀,便擺擺手將張院判帶了下去,出門便說“君上把醋又喝上了。瑾主兒護著孩子他就心里堵。”
張院判不解,“啊,如何和自己的孩子還吃醋。”
“很復雜。”莫乾擺擺手,“得從四個月前皇祖母的祭日說起。你給我五十兩,我空給你詳細講講。”
張院判捂著荷包“你先八卦的,怎麼還問我要五十兩!我不好奇君上的總行了吧!嗨喲,果然皇家野史賊貴。”
Advertisement
室只余傅、文二人。
文瑾看著滿地碎掉的茶杯,幽幽吐了口氣,便蹲下,去撿茶杯碎屑,布滿傷痕的手又被茶杯割破了。
傅景桁看見手指被割破,鮮刺目極了,便猛地攥住纖細的手腕,把猛地拉至自己近,視著令他神馳的容。
“你究竟還要在朕面前裝可憐到幾時?乖乖,你的親筆信已經被朕查到了!南郭鎮子死人了!希冀朕像個柳下惠一樣繼續花前月下哄你麼?”
文瑾被他拉住了有劍傷的那個臂膀,牽了傷口,巨痛鉆心,咬著沒有出聲,只是用霧蒙蒙的大眼凝著盛怒的傅景桁,不知道他的怒意何時可以消解,屬實害怕了,沒有安全,沒有自己想的那麼堅強,也需要一個溫暖的港灣,容撒撒,發發無傷大雅的小脾氣。
兩滴淚水無聲地落,
流過面頰,滴落在他的手背,接著有更多的淚水落了下來。
傅景桁的心如被狠狠住了,作痛,他抿著薄道“不是能言會道最狡辯,如何不說話了?”
“我只是在撿茶碗碎屑。你每次摔東西我都會收拾的。我沒有裝可憐。我的可憐還需要裝嗎。”
文瑾說著便哽咽了。
“我習慣了包容你的壞脾氣。但我…可我一直也只是個沒娘的孩子啊,我多希你能包容一下我,而不是每每在我面前摔東西呢……這幾個月你沒有回家知道我獨守空房怎麼過的嗎…你知道我怕黑的,你知道我害怕到在床角徹夜不敢合眼是什麼覺嗎…”
傅景桁緩緩將文瑾的手漸漸地放了。
他們都安靜了。
Advertisement
中間擺著那些撕裂二人的信件。
老百姓苦,使傅景桁無法過鴻去擁抱安文瑾。會良心不安。
文瑾還要去國子監送玉甄寶銀報道念書,便著心口的委屈,去洗漱了,不能因為的事把弟弟妹妹的前途耽誤了,的責任需要扛起來。
“玉甄寶銀念書的事,和老薛談好了?”傅在靜了很久之后問了出來,“伯母的案子…”
“老薛給了推薦信,我們要去國子監報道了。母親的案子停滯不前,康蕊黎不敢口。謝謝君上問我。”
“嗯。”傅景桁便走到窗畔,推開窗戶看著遠道清湖的風景,沒有再說話了,一直來是包容他居多,他習慣了從上得到藉,從不知道堅強的也會脆弱。
“你說給端木小姐讓位,我什麼時候搬走?”文瑾靠在桌沿,終于問了出來。
“現在。請你凈出戶!”傅景桁絕地轟人,“一片布縷也不準帶走!朕的每一文錢都不養細作。”
現在。
凈出戶。
真的很絕。
沒有任何人味。
文瑾覺得自己猶如死了,跟了他十幾年,終于被轟出家門了,半月前便不該回來吧,他那時好溫說他想,便糊涂了,若知道回來會被他為
了新歡轟出去,怎麼會回來讓自己如此難堪呢,縱然再思念他也不會回來的呢。
文瑾緩步走到傅景桁邊,用手捧著一個青銅制的小獎章,遞到傅景桁的前,仰起下頜凝著他俊秀的容。
“小時候,你說你要是能當一個為民做主的好皇上,要我給你獎章。我刻了一個獎章,你不鋪張浪費,我沒有選金銀,而是選了便宜的青銅。本來打算你二十五生日送你的。你生日那天和軍師妹妹過的。我沒機會給你。現在給你吧。”
Advertisement
傅景桁低眼看著靜靜躺在文瑾手心的銅制獎章,正面刻著“稱職”二字,反面刻著“明君”二字,時的記憶在腦海劃過,他眼眶竟酸了。
瑾妹,瑾妹,我如果以后為一名民親民好皇上,你怎麼獎勵我呢?
阿桁哥,我給你親手刻一枚大獎章呢!
“諷刺朕?當下淮南民生疾苦,橫尸遍野,你給朕看這個,說朕稱職?”傅景桁倏地將手中獎章揮開了,獎章掉在地上,發出悶悶一聲響,“明君?”
文瑾看著刻的獎章滾落在桌案底下,不見了蹤影,心中的窟窿它痛極了。
便在此時,門外響起了端木馥的嗓音,“君上,臣寫好了為民祈福的萬字書。您有時間過目嗎?”
傅景桁聞聲一頓,不悅被外人打擾,“有事。外面候著!”
“阿桁哥,我走了,祝你和端木婚姻滿。保重!”文瑾被多余包圍著,再一次調轉了腳尖,自他的生活中黯然離場,灰溜溜的,沮喪極了。
轉一瞬,淚如雨下。
將手探在門把手上,要拉開那厚重的木門。
“文!”
傅景桁突然急聲喚。
忽然聽到后面腳步聲響起,腳步聲越來越近,越來越急,接著傅景桁猛然從后面把子抱住。
他抱抱得很很,仿佛要把嵌進他的里,他的心跳聲重重打在的后背,仿佛他很懼怕會失去似的。
疑了。
在耳側,他素來薄涼的嗓音也發了,“朕…舍不得”
猜你喜歡
-
完結300 章
王妃脾氣爆:皇叔,請節製
一朝穿越成傻妞,廚房茅房傻傻分不清。幸有爹孃疼愛,四位兄長百般嗬護成長。笑她目不識丁癡傻愚頑?一朝驚天地,袖手弄風雲。從此商界多了個不世出的奇才!說她軟弱可欺任意拿捏?上有護短狂老爹撐腰,下有妹控兄長為她收拾善後。權傾朝野號稱天下第一美色的輔助親王,更是化身寵妻狂魔,讓她橫著走!某天在金子堆裡數錢數的正歡慕容明珠,被一雙大手覆上「王妃,今晚我們……」「一邊去,別妨礙我數錢」「……」
52萬字8.18 10969 -
完結11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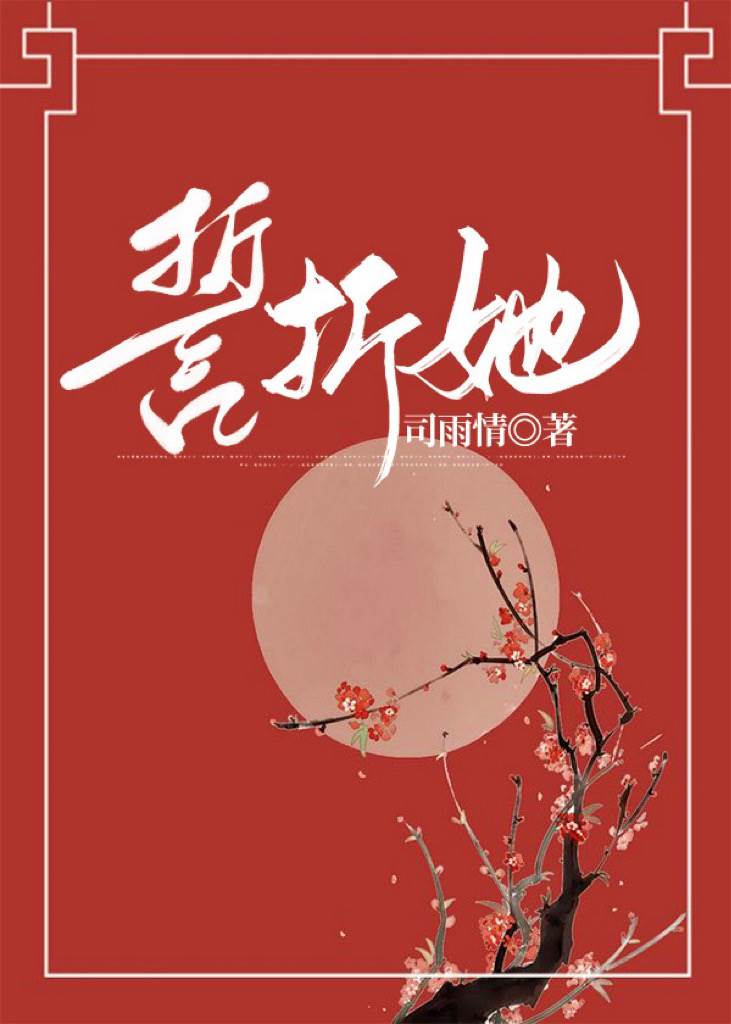
妄折她
昭華郡主商寧秀是名滿汴京城的第一美人,那年深秋郡主南下探望年邁祖母,恰逢叛軍起戰亂,隨行數百人盡數被屠。 那叛軍頭子何曾見過此等金枝玉葉的美人,獸性大發將她拖進小樹林欲施暴行,一支羽箭射穿了叛軍腦袋,喜極而泣的商寧秀以為看見了自己的救命英雄,是一位滿身血污的異族武士。 他騎在馬上,高大如一座不可翻越的山,商寧秀在他驚豔而帶著侵略性的目光中不敢動彈。 後來商寧秀才知道,這哪是什麼救命英雄,這是更加可怕的豺狼虎豹。 “我救了你的命,你這輩子都歸我。" ...
40.2萬字8.18 6699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