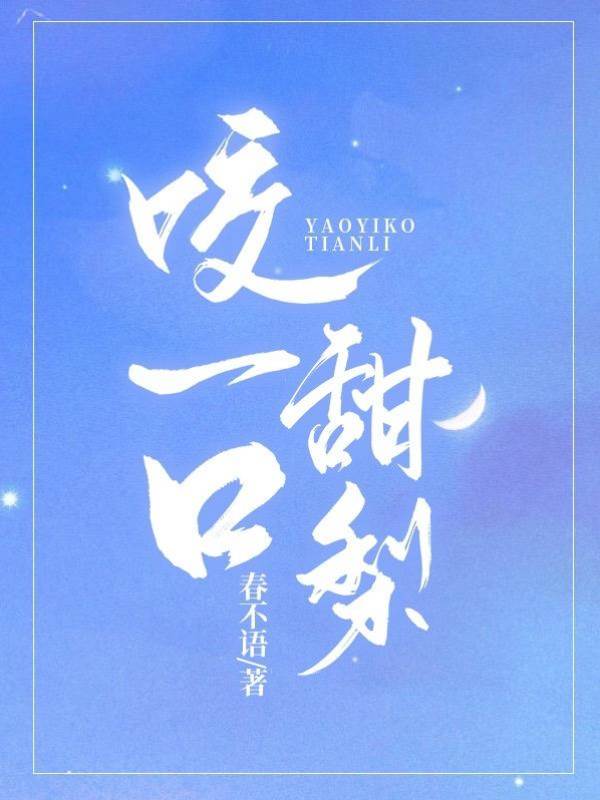《冬夜吻玫瑰》 第166頁
他只知道,自己從來沒有喜歡過別人,但看到南知的第一眼,他就有明顯的悸。
麗鮮活,像帶著的仙,跑到他面前,不怕他也不可憐他,笑著問他什麼名字。
他第一次有一種認知,好漂亮。
見起意。
顧嶼深在完全不認識的況下,對第一個念頭的確是好漂亮。
但他見過那麼多的生,漂亮的本數不清,卻從來沒有一個了他的眼,也從未去用好看與否去評價對方過,對誰都是漠視的態度。
其實南知也不只是漂亮。
更多的是明艷,與生俱來一種能夠讓人充滿朝氣、溫暖的能力。
再往后,這種認知便了一種執念。
只是因為——“是南知。”
初見時說,南知,東南西北的南,知識的知。
他喜歡的理由也僅僅是因為,是南知。
-
半個月后,到了Sherry芭蕾演出的日子,南知和顧嶼深下班后在外面吃過晚飯便直接去了劇場。
Advertisement
排隊、檢票、場。
買的是前排票,看得很清楚。
顧嶼深倒也不看這種演出,從前看的都是南知的演出,今天完全是為了陪來看的。
但無疑這是一場很彩的演出,看完,南知還興沖沖地問:“你覺得怎麼樣?”
“還行。”
“怎麼就還行。”南知還不太滿意,“每個作都做的也太漂亮了吧!”
顧嶼深敷衍地回答:“沒你的好看。”
南知愣了下,轉而笑了:“我又不是在考驗你,這不是網上那種給男朋友的送命題。”
他挑眉:“男朋友?”
“老公。”南知立馬糾正。
過了會兒,好玩似的,笑著又喚了聲:“老公。”
顧嶼深被這種野路子的撥勁兒弄的心猿意馬,剛想過去親,旁邊一道聲音橫進來。
Sherry用英語喚了南知一聲:“我聽Alisa說你來看我這場演出了,謝幕時就覺得眼,原來真的是你。”
南知跟Sherry不,但幾次在一個劇場演出過不同劇目,也算互相認識、彼此欣賞。
Advertisement
見特意過來,南知驚喜道:“我特別喜歡你的表演。”
Sherry說也一直以來很喜歡南知的表演。
相互客套完,Sherry便把目轉到了側高大男人上,笑了下:“這位就是你丈夫嗎?”
“嗯。”說的是丈夫而不是男朋友,南知笑問,“你也知道這件事了嗎?”
Sherry笑著點頭,說是Edward痛哭著告訴這件事的,還說他的神徹底離開他了。
這話肯定有夸張的分在,Edward是從前南知的追求者之一,男芭蕾舞演員,有趣一哥們兒,跟們倆都認識。
又聊了幾句,那邊有Sherry的朋友,這才結束。
往劇場外走,顧嶼深挑了下眉,平靜道:“Edward?”
南知看他一眼,笑起來,點了點頭,毫無求生地回答:“哦,以前把我當神的一個舞蹈演員。”
顧嶼深“嘖”了聲,抬手摁住后頸,用力掐了把。
Advertisement
“疼!”南知怒了。
他跟拎小兔崽似的,依舊不松手,淡聲:“把你當神?”
南知:?
怎麼會有這種男人!!!
但好漢不吃眼前虧,認命道:“不說了不說了。”
顧嶼深輕嗤一聲,終于松手。
南知著脖子歪了歪頭:“變態。”
顧嶼深眼風一掃過來,立馬往旁邊撤幾步,生怕又被他抓去。
顧嶼深笑了聲:“你怕什麼。”
“……”
“過來。”他招招手,“疼了?我給你。”
南知挪回去,讓他,小聲說:“小心我告你家暴。”
顧嶼深笑了笑,把人重新摟到懷里:“看不出來,現在口語還可以?”
從前讀書時候南知因為跳舞耽誤不學習時間,又是個貪玩的子,英語早讀課被懶覺占據,經常被英語老師起來讀課文。
而那時顧嶼深作為的同桌,也被牽連著作為搭檔一塊兒讀。
跟他的口語比起來,南知的就有些難登臺面了,那時候不知道被英語老師比較著數落了多回。
Advertisement
南知知道他在說什麼,笑道:“要是在國外這麼多年還不會說,我真傻子了。”
“難學嗎?”他問。
“難的。”
南知是一個沒怎麼吃過苦的人,唯一不那麼順暢的幾年都是在國外前幾年,本也覺得沒什麼,但顧嶼深一問,便又覺得有些委屈了。
“剛到國外開始上課的時候,經常聽不懂,但又要考學,經常要學到很晚。”
顧嶼深了頭發。
聳了聳肩,笑著:“其實我那時候也想過,我不想那麼努力了,想回國,想去找你,我還計劃得好,我吃一點,節約一點,就死皮賴臉地讓你養著我算了。”
顧嶼深彎,又覺得心疼,側過頭在發頂親了下。
南知輕輕吸了口氣,緩著聲故作輕松道:“可是我以為你真的不要我啦,我也只敢心里想一想,但一想到不可能實現就更難過了,現在再回過頭去看,我們好像真的差錯地錯過太多了。”
猜你喜歡
-
完結223 章

總裁追婚記:嬌妻哪裏逃
三年前,初入職場的實習生徐揚青帶著全世界的光芒跌跌撞撞的闖進傅司白的世界。 “別動!再動把你從這兒扔下去!”從此威脅恐嚇是家常便飯。 消失三年,當徐揚青再次出現時,傅司白不顧一切的將她禁錮在身邊,再也不能失去她。 “敢碰我我傅司白的女人還想活著走出這道門?”從此眼裏隻有她一人。 “我沒關係啊,再說不是還有你在嘛~” “真乖,不愧是我的女人!”
29.6萬字8 5231 -
完結1939 章

替嫁后我被大佬纏上了
所有人都說,戰家大少爺是個死過三個老婆、還慘遭毀容的無能變態……喬希希看了一眼身旁長相極其俊美、馬甲一大籮筐的腹黑男人,“戰梟寒,你到底還有多少事瞞著我?”某男聞言,撲通一聲就跪在了搓衣板上,小聲嚶嚶,“老婆,跪到晚上可不可以進房?”
290萬字8.18 189231 -
完結1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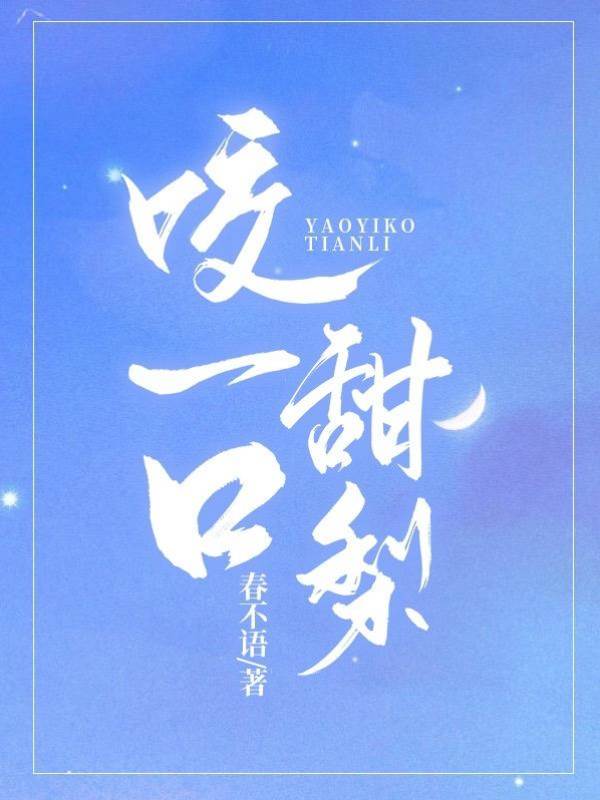
咬一口甜梨
白切黑清冷醫生vs小心機甜妹,很甜無虐。楚淵第一次見寄養在他家的阮梨是在醫院,弱柳扶風的病美人,豔若桃李,驚為天人。她眸裏水光盈盈,蔥蔥玉指拽著他的衣服,“楚醫生,我怕痛,你輕點。”第二次是在楚家桃園裏,桃花樹下,他被一隻貓抓傷了脖子。阮梨一身旗袍,黛眉朱唇,身段玲瓏,她手輕碰他的脖子,“哥哥,你疼不疼?”楚淵眉目深深沉,不見情緒,對她的接近毫無反應,近乎冷漠。-人人皆知,楚淵這位醫學界天才素有天仙之稱,他溫潤如玉,君子如蘭,多少女人愛慕,卻從不敢靠近,在他眼裏亦隻有病人,沒有女人。阮梨煞費苦心抱上大佬大腿,成為他的寶貝‘妹妹’。不料,男人溫潤如玉的皮囊下是一頭腹黑狡猾的狼。楚淵抱住她,薄唇碰到她的耳垂,似是撩撥:“想要談戀愛可以,但隻能跟我談。”-梨,多汁,清甜,嚐一口,食髓知味。既許一人以偏愛,願盡餘生之慷慨。
20.2萬字8 7865 -
連載256 章

全球通緝令,抓捕孕期逃跑小夫人
曾經顏琪以爲自己的幸福是從小一起長大的青梅竹馬。 後來才知道所有承諾都虛無縹緲。 放棄青梅竹馬,準備帶着孩子相依爲命的顏鹿被孩子親生父親找上門。 本想帶球逃跑,誰知飛機不能坐,高鐵站不能進? 本以爲的協議結婚,竟成了嬌寵一生。
45.2萬字8 466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