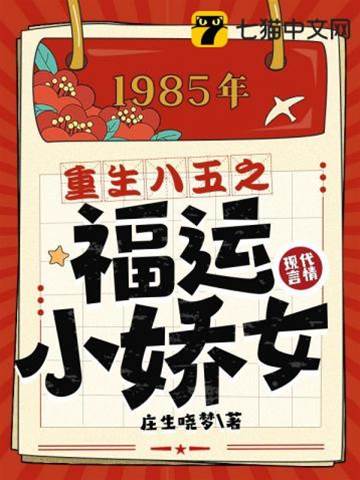《烏合之眾》 第307章 番外篇·白杏36
所有經過的路人,都覺得眼前這一幕,無比詭異。
一邊是相擁的,一邊是站著的沉默的男人,男人的眼神很平靜,也沒有過分的舉,但依舊讓人覺到他似乎被傷到了。
溫源總覺有一視線落在自己上,然后抬起了頭。
白杏閉著眼,卻覺到男人的吻沒有落在自己上,有些疑的睜開了眼睛。
看到了幾步之遙的何致遠。
白杏只頓了一下,然后抬起溫源的下,當著何致遠的面,親了上去。
撲面而來的快,報復的快。
我怎麼可能,永遠在你面前示弱呢?想。
是被這樣的。
白杏眼眶微微潤,再睜眼時,不遠的人,已經不見人影,仿佛那只是的錯覺。
溫源擔憂的說:“你還好吧。”
“非常好啊。”白杏笑起來,說,“我已經不知道有多久,沒有過自由的氣息了。”
溫源似乎有話要說,但最終只是跟道別,“這段時間你也很忙,好好休息吧。”
白杏也沒有談說的興趣。
Advertisement
回了家,等待著何致遠的電話,已經準備好了跟他談判,想再也不用在他面前賣乖了,多好啊,會把他最的那些利益,甩在他臉上。
只可惜何致遠并沒有聯系。
一整晚,他杳無音訊。
白杏第二天不得不主聯系他,時隔兩個月,再次來到了他的別墅,曾經的囚牢。
何致遠坐在沙發上,表有些淡,不知道在想什麼。
走到他的邊,才恍然想起,門口有幾棵小杏樹,沒有了他的打理,這會兒禿禿的。
“我來找你談事。”白杏公事公辦道。
何致遠一不,看著窗外,似乎是看癡了,他沒有看,只道:“我曾經以為,我們的矛盾,只在孩子上。你雖然恨我,但我想也應該有幾分意。等孩子回來,我們就能重歸于好。”
白杏搖搖頭,說:“我不你。”
至于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不的呢,也忘記了。
何致遠角微,最后只道:“是的,你并不我,但你表現得……有那麼一點像。”
Advertisement
“盛夏背后的人就是我。”
何致遠說:“我知道。”他并不驚訝,似乎在他的預料之。
白杏頓了頓,道:“我對做生意沒什麼想法,只要你把孩子給我,何氏的核心產業鏈我不會再投使用。你依舊能站在行業金字塔尖,相信你很快就能恢復過來。”
“但是,我不會銷毀,我得防止你緩過勁來后,重新把孩子搶走。”白杏拿出一份文件,那是關于養權的合同,說,“你要是同意,就簽字吧。”
何致遠終于回頭看了一眼,隨后就在文件上簽了字。
白杏又有那麼一丁點不自在了,怎麼小寶還沒有這點產業重要麼?
但也只是心里有點別扭,很快就利落的收起了文件,公事公辦的說:“謝謝配合,我什麼時候能過來接小寶?”
“一個月以后。”何致遠道。
見他這麼配合,白杏便也能跟他客套幾句,客氣的笑了笑,說:“麻煩何總了。”
何致遠安靜了許久,才道:“你是真的喜歡他?”
對溫源覺不錯,至于是不是喜歡,不知道,可是在他面前,還是干脆利落的承認道:“是的。”
Advertisement
“你一直告訴我,你對他沒想法。”
“怕你針對他啊。”白杏輕描淡寫的說道,“在你面前,我只有裝作不在意,才能保住我在意的東西。”
何致遠再次陷沉默。
“孩子萬一不在了,你會毫不猶豫的去死,對麼?”
白杏的臉瞬間就冷了下來:“不錯,我不會獨活。”
何致遠看了片刻,再次移開了眼,看著窗外,一言不發。
“你當時,就也從來沒有想過你死了,我該怎麼辦。”他的聲音很輕,緒也不明顯,只是有些頹廢。
“我死了,你可以再娶,何總怎麼可能缺人。”白杏見談完事了,轉就走。正如所想的那樣,不用再給他一個好臉。
他們如今也算得上是死對頭了。
白杏說:“如果哪一天,你來報復我,我絕對不會多說一個字,那是你的本事。”
何致遠一不。
白杏不知道他是不是睡著了,沒有再管他,推開門離開了。
何致遠在走后,才慢慢的睜開眼。
……
“大爺也這麼可憐呀?”坐在他邊,疑道,“過生日也一個人干坐著,怎麼不回家?”
Advertisement
“何家并不是我家。”
”你還有其他家啊?”
“沒有。”他不太耐煩,也不愿意跟解釋他母親的事,母親不在了,他便沒有家了。
眉眼彎彎,說:“我也沒有家,要不然我給你一個家吧,我這個人很忠誠的,可以跟你過一輩子呢。們比我漂亮,卻沒有我踏實。不過你給我在門口中一排杏樹吧,別人一眼就看出來我是主人啦。小三上門還得對我客氣點,怎麼說他相好曾經給我種過樹,顯得我也很重要過。”
他無語,卻還算客氣:“不用。”
“我真的很忠誠的。”說,“我覺得冥冥中,你會給我種,你就是喜歡我這樣的。”
猜你喜歡
-
完結73 章

霍先生的妄想癥
薛小顰通過相親嫁給了霍梁。 這個從骨子里就透出高冷與禁欲的男人英俊且多金,是前途無量的外科醫生。 薛小顰以為自己嫁給了男神,卻沒想到婚后才發現,這男神級的人物竟然有著極為嚴重的妄想癥。
24.6萬字8 9101 -
完結3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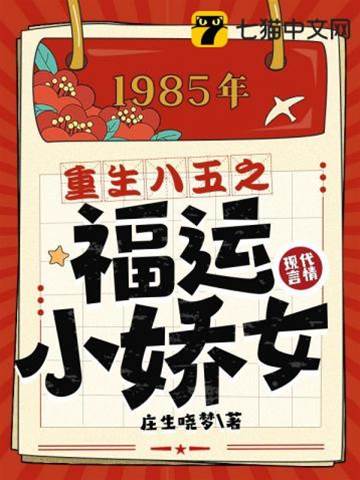
重生八五之福運小嬌女
前世,喬金靈臨死前才知道爸爸死在閨蜜王曉嬌之手! 玉石俱焚,她一朝重生在85年,那年她6歲,還來得及救爸爸...... 這一次,她不再輕信,該打的打,該懟的懟。 福星錦鯉體質,接觸她的人都幸運起來。 而且一個不留神,她就幫著全家走向人生巔峰,當富二代不香嘛? 只是小時候認識的小男孩,長大后老是纏著她。 清泠儒雅的外交官宋益善,指著額頭的疤,輕聲對她說道:“你小時候打的,毀容了,你得負責。 ”
70.5萬字8 19167 -
連載940 章

替嫁新婚夜,植物人老公要離婚
甜寵1v1+虐渣蘇爽+強強聯合訂婚前夜,林婳被男友與繼妹連手設計送上陌生男人的床。一夜廝磨,醒來時男人不翼而飛,死渣男卻帶著繼妹大方官宣,親爹還一口咬定是她出軌,威脅她代替繼妹嫁給植物人做沖喜新娘。林婳???林婳來,互相傷害吧~林妙音愛搶男人?她反手黑進電腦,曝光白蓮花丑聞教做人。勢力爹想躋身豪門?她一個電話,林氏一夜之間負債上百億。打白蓮,虐渣男,從人人喊打的林氏棄女搖身一變成為帝國首富,林婳眼睛都沒眨一下。等一切塵埃落定,林婳準備帶著老媽歸隱田園好好過日子。那撿來的便宜老公卻冷笑撕碎離婚協議書,連夜堵到機場。“好聚好散哈。”林婳悻悻推開男人的手臂。某冷面帝王卻一把將她擁進懷中,“撩動我的心,就要對我負責啊……”
112.4萬字8.18 3439 -
連載902 章

人潮洶涌
周稚京終于如愿以償找到了最合適的金龜,成功擠進了海荊市的上流圈。然,訂婚第二天,她做了個噩夢。夢里陳宗辭坐在黑色皮質沙發上,低眸無聲睥睨著她。驟然驚醒的那一瞬,噩夢成真。陳宗辭出現在她廉價的出租房內,俯視著她,“想嫁?來求我。”……他許她利用,算計,借由他拿到好處;許她在他面前作怪,賣弄,無法無天。唯獨不許她,對除他以外的人,動任何心思。……讓神明作惡只需要兩步掏出真心,狠狠丟棄。
158.9萬字8.18 261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