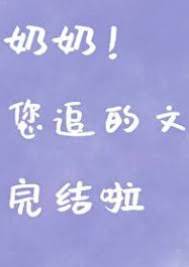《他的小嬌嗔》 [他的小嬌嗔] - 第15節
,能清楚覺到自己結實的口著獨屬於孩的。
那種覺,比早上在樓梯那兒要更為真實和。
當時倒是沒有多想,如今再細品,莫名品出一子的燥熱。
岑頌吐出一口長長的,略帶灼熱的氣息。
不知是不是燙著的臉了,惹得本來睡得很安穩的人翻了個。
原本放在側的胳膊隨著翻的作,無意識地蜷起,剛好繞過他的胳膊。
似乎是覺得那條延著青筋脈絡的胳膊涼涼的讓很舒服,在枕頭上的那半張臉,蠕蹭了幾下後,往那胳膊那兒靠近,這樣一靠,子不由得往一起蜷。
那種姿勢,溫順的好似一隻想要得到主人安的小貓。
大概是等不到主人的回應,開始把臉往他手臂上蹭,蹭了幾下,最後把那雙如棉花糖的在了他手臂。
被酒點燃的臉是燙的,也是燙的,呼出的氣息更是燙到灼人。
手臂裏的都好像被燙沸了似的,想回胳膊,可作卻和念頭唱反調。
很快,被灼燙的呼吸噴灑的那塊手臂皮洇出了細的水汽。
岑頌別開臉,以為幾個均勻的呼氣吸氣就能把心裏的燥給下去。
結果徒勞一場不說,間鋒利滾的頻率愈加繁無章。
別說是他心心念念的人,就算對沒心思的,也不住這樣。
床下一周亮著懸浮應燈,在淺的地毯上氤出一圈昏黃的朦朧。
暖的最能滋生曖昧,在靜謐的房間裏,每一縷看不見不著的空氣都能變讓人犯.罪的因子。
神經和理智掙開心底束縛,想吻的念頭開始在他腦海裏橫衝直撞。
他甚至覺得,老天都想人之,給他這樣一個機會,彌補早上樓梯間他對的遐想。
Advertisement
他俯離近,和氣息一樣滾燙的,還有他的目,他追著安靜的眼睫,明目張膽地看,看了好半晌,才輕聲問:“知道我喜歡你嗎?”
閆嗔閉著眼,雖然沒有醒,但好像潛意識還在,似回應地“嗯...”了一聲。
就是那一聲,不僅擊潰了他所有嚴合的偽裝,也讓他丟掉了‘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素養。
湊近的,就要落下時,他又稍稍偏了幾分,吻在了臉頰上。
克己複禮的都不像他。
臉上細小的絨被拂,混著他的鼻息,讓側臉睡著的人蹙了蹙眉。
淺淺的一聲“唔”讓岑頌心髒一。
以為是要醒,心裏正想著要找個什麽樣的借口時,原本側躺著的臉突然轉了過來。
被他心心念念想吻卻又克製的過他臉,最後停在了他上。
岑頌隻覺間一,愣在原地一不敢,呼吸都要停滯。
目落到近在咫尺的那雙眼睛上。
隻見那排眼睫安安靜靜地垂著,倒是他,眼睫抖個不停。
若是的老實一點,岑頌或許還能極力克製住,偏偏,噘了噘,不知是覺到了上的,還是覺得了。
著他的那雙♪瓣突然張開,含住他的同時,溼潤潤的舌尖從齒間探出。
手臂上的青筋瞬間繃,蟄伏在他心底的突然掙了束縛般,讓他氣一點一點上湧。
所有的克製在那一瞬,全部潰不軍。
第14章咬破舌尖
人在口幹舌燥的時候,到溼潤的東西,總會下意識去汲取它的水分。
所以,當閆嗔覺到有溫的什麽在上時,條件反地了,又含住那塊吮了吮,似乎被不屬於自己的溼潤驚喜到,碾著他的瓣,用牙齒咬。
Advertisement
岑頌眉心一擰,“別咬,疼。”
似乎是聽到了警告聲,下的人頓時鬆開了雙齒,想聽話,卻又不滿足,滾燙的舌尖鑽進去,左勾一下右勾一下,漉漉的♪讓本能地想要更多。
盯著看的那雙漆黑瞳孔,因綢繆的熱烈而一點點染上了穀欠的。
視覺、聽覺、味覺裏全是。
四麵八方向他席卷,將他籠罩。
心心念念的人就在懷裏,他克製不住地把對的喜歡盡數淹沒在滿是意的吻裏。
飲鴆止般,用力地吻。
周圍一切都靜止了,隻有相的兩輾轉作。
岑頌把滾燙的舌推回去,再把自己溫熱的舌口,貪婪地攫取著口中的酒甜,再如所願的,將自己的溼潤一點點渡給。
直到覺到不再回應他的作,吻的力度才逐漸溫,奉若珍寶又小心翼翼地輕吮的。
放開時,岑頌的呼吸又促又燙。
再繼續待在旁邊,岑頌不敢保證自己會不會失控。床墊因他猛然起的作倏地回彈,沒一會兒的功夫,有水聲從衛生間裏傳出來。
床上的人瀲灩,微微紅腫,不知做了什麽好夢,角彎著。
但衛生間裏的人就沒這麽愜意了,暗紫的襯衫和黑西一件丟在了原木的竹筐裏,一件丟在了黑的洗漱臺上。
半點水汽不見的磨砂玻璃門裏,那條頎長的人影半天沒有作。
岑頌兩手撐著大理石牆麵,任由冰涼的水柱從頂噴花灑澆下來,若不是連續兩聲噴嚏,他這個涼水澡還不知要洗多久。
星氤氳在朦朧的夜裏,縹緲如紗。
不知是不是喝醉了的原因,閆嗔這一覺睡的很沉,睜開眼的時候,已經有大片的金從窗外鋪進來。
Advertisement
赤腳站在窗邊,兩條胳膊直抬到頭頂,做了幾個拉後,才去了衛生間洗漱。
清涼的牙膏漫到舌尖的時候,縷的疼意讓眉心淺淺皺了一下。
漱掉裏的泡沫,閆嗔離近鏡子,細細看了看自己的舌尖。
有一道很小很小的傷口,不細看本就看不出來,但是一就疼,閆嗔用舌尖又了一下,頓時,一聲“嘶”音從倒吸的一口氣裏溜出來。
昨晚吃日料的時候也沒覺咬到,怎麽會有小傷口呢?
閆嗔一邊想著一邊下樓,踩下樓梯的最後一階,徑直往餐廳去。
餐桌上剛好有一杯水,閆嗔也沒多想,端起水杯轉又往客廳去。
裏的水還沒來及咽下,目陡然落到沙發扶手懸下來的兩條。
閆嗔心裏一驚,邁出的一雙腳猛然收回,突生的恐懼讓嚨一,還沒來得及尖出聲,就被口中的水嗆出了劇烈幾聲咳。
沙發裏的人被驚醒,撐著胳膊探起。
接連的一陣咳嗽把閆嗔的臉憋得通紅,再一抬頭,對上那雙微瞇的雙眼,閆嗔表一呆,手裏的水杯“咚”的一聲掉在了地毯上,淺的羊絨地毯頓時被浸出一團深。
閆嗔狠狠吞咽了一下,睜圓了的一雙眼寫滿了震驚:“你、你怎麽在這?”
岑頌收起翹在沙發扶手的兩條,耷拉著眼皮,懶懶地打個哈欠說:“我不在這,你怎麽回來?”
這話是什麽意思?
閆嗔在心裏把他的話回味了兩遍,這才後知後覺地想起昨晚給他打電話讓他去接這事。
“昨晚你真去接我了?”
岑頌眉眼帶著閑散的笑意:“你這是喝斷片了?”
閆嗔撲閃著眼睫,又努力回想了一陣,再抬頭,臉上現出要命的無辜:“我、我有點想不起來了。”
Advertisement
昨晚吻過之後,岑頌還在擔心,若是一覺醒來想起昨晚他對做出的荒唐事,會不會扇他幾掌,又或者把他連人帶電話地拉黑,以後都不再見他。
卻沒想到這人喝醉會斷片。
明明該慶幸的,可心頭又止不住的,爬上幾分失落。
岑頌略有煩躁地抓了把頭發。
閆嗔這才注意他平時都梳上去的劉海這會兒都垂了下來,長度剛好到他眉骨,落下細細碎碎碎的影,整個人看上去要和許多,和平時大相徑庭。
見杵在那兒不說話,還一個勁盯著他看,岑頌心裏生出些不安。
他輕咳一聲從沙發裏起,越過閆嗔邊時,看見了上的水,以及下的一點水痕。
他間鋒利驀然一滾。
昨晚熱烈激吻的畫麵頓時四麵八方地湧腦海。
誰能想到,平時看著含蓄一小姑娘,醉起酒來竟然那麽大膽。
但是很快,心裏的那點回味就被不爽占滿了。
昨晚幸虧是他,如果不是他呢,換個男人,是不是也會這樣?
這麽一想,他心裏頓時三分慍惱,七分煩躁。
可麵對此時一臉無辜的表,他又實在發作不出來。
“頭疼不疼?”
帶著關心的詢問,他聲音很溫。
閆嗔聽得微怔,反應過來,忙搖頭說不疼。
結果上一秒還滿腔溫的人突然帶了幾分教訓人的口吻:“下次不許再喝酒!”
閆嗔再一次怔住,想著這人怎麽一會兒一個變的時候,原本站旁的人已經越過走了。視線追到衛生間門口,閆嗔轉了轉眸子,如果剛剛沒聽錯,他好像有點生氣。
是因為昨晚被一個電話喊去接?
可一個掌也拍不響,他要是不想去幹嘛還問要日料店的地址......
不過想是這麽想,轉往樓上去的時候,又忍不住嘀咕著,之前也不知是誰說要照顧好,話倒是說得漂亮,結果翻臉比翻書還快。
等岑頌洗漱完從衛生間出來,客廳裏已經沒人了。
剛想往樓上去,擱在茶幾上的手機滋滋震了起來。
電話是李旭打來的:“岑總,關明輝定了八點四十去鹽城的機票。”
岑頌冷出一聲笑:“他倒是機靈,還知道要去找輝盛的汪總。”
“岑總,”李旭問:“您要不要過去一趟?”
“鹽城就不去了,查一下環地產的劉董這兩天在不在香港。”
“在的,昨晚劉董人發了一張朋友圈,是在香港的永巢別墅,”李旭問:“要給您定今天的機票嗎?”
“嗯,”岑頌在心裏盤算了下時間:“上午十一點到下午兩點,你準備一下。”
電話掛斷,岑頌給靳洲打了一個電話,“還在香港吧?”
靳洲笑了聲:“怎麽,你要過來?”
岑頌也沒跟他兜圈子:“上次你不是說環地產的劉董想在地投資環保項目?”
“然後呢?”靳洲問。
“我這邊剛好有一個,他應該會興趣。”
靳洲對岑頌,從來都不吝嗇他的際圈:“今晚七點有場慈善晚宴,劉董和他夫人會參加,不過名單已經截止,如果你要,我讓人把我的那份改了。”
岑頌混不吝地拖著調:“那我就先謝過靳叔叔了。”
靳洲冷出一聲笑意:
猜你喜歡
-
完結260 章

小可愛你挺野啊
第一次和江澈見麵,男人彎著一雙好看的眼,伸手摸摸她的頭,笑著叫她小喬艾。他天生笑眼,氣質溫雅中帶著些許清冷,給人感覺禮貌親切卻又有幾分疏離。喬艾正是叛逆期的時候,個性還不服管教,但為了恰飯,她在江澈麵前裝得乖巧又懂事。時間一久,跟江澈混熟,喬艾的人設日漸崩塌……她在少女時喜歡上一個男人,長大後,使出渾身解數撩他,撩完消失的無影無蹤。多年後再遇見,男人紅著眼將她圈進臂彎裡,依舊彎著眼睛,似是在笑,嗓音低沉繾綣:“你還挺能野啊?再野,腿都給你打斷。”
44.2萬字8 20042 -
連載2076 章

撿個首富回家寵
送外賣途中,孟靜薇隨手救了一人,沒承想這人竟然是瀾城首富擎牧野。
237.7萬字8 208041 -
完結213 章
生崽痛哭:豪門老男人低聲輕哄
【年齡差11歲+霸總+孤女+甜寵+無底線的疼愛+越寵越作的小可愛】 外界傳言,華都第一豪門世家蘇墨卿喜歡男人,只因他三十歲不曾有過一段感情,連身邊的助理秘書都是男的。 直到某天蘇墨卿堂而皇之的抱著一個女孩來到了公司。從此以后,蘇墨卿墮落凡塵。可以蹲下為她穿鞋,可以抱著她喂她吃飯,就連睡覺也要給她催眠曲。 白遲遲在酒吧誤喝了一杯酒,稀里糊涂找了個順眼的男人一夜春宵。 一個月以后—— 醫生:你懷孕了。 白遲遲:風太大,你說什麼沒有聽見。 醫生:你懷孕了! 蘇墨卿損友發現最近好友怎麼都叫不出家門了,他們氣勢洶洶的找上門質問。 “蘇墨卿,你丫的躲家里干嘛呢?” 老男人蘇墨卿一手拿著切好的蘋果,一手拿著甜滋滋的車厘子追在白遲遲身后大喊,“祖宗!別跑,小心孩子!” 【19歲孩子氣濃郁的白遲遲×30歲爹系老公蘇墨卿】 注意事項:1.女主生完孩子會回去讀書。 2.不合理的安排為劇情服務。 3.絕對不虐,女主哭一聲,讓霸總出來打作者一頓。 4.無底線的寵愛,女主要什麼給什麼。 5.男主一見鐘情,感情加速發展。 無腦甜文,不甜砍我!
39.3萬字8 14199 -
完結18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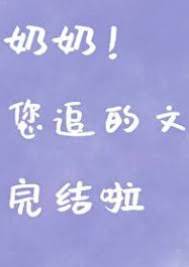
南風知我意
清遠公安裴西洲,警校畢業履歷光鮮,禁慾系禍害臉,追求者衆卻無一近的了身,白瞎了那顏值。 某天裴西洲受傷醫院就醫,醫生是個女孩,緊張兮兮問他:“你沒事吧?” 衆人心道又一個被美色迷了眼的,這點傷貼創可貼就行吧? “有事,”裴西洲睫毛低垂,語氣認真,“很疼。” “那怎樣纔會好一些?” 裴西洲冷冷淡淡看着她,片刻後低聲道:“抱。” - 緊接着,衆人發現輕傷不下火線的裴西洲變乖了—— 頭疼發熱知道去輸液:南風醫生,我感冒了。 受傷流血知道看醫生:南風醫生,我受傷了。 直到同事撞見裴西洲把南風醫生禁錮在懷裏,語氣很兇:“那個人是誰?不準和他說話!” 女孩踮起腳尖親他側臉:“知道啦!你不要吃醋!” 裴西洲耳根瞬間紅透,落荒而逃。 ——破案了。 ——還挺純情。 - 後來,裴西洲受傷生死一線,南風問他疼嗎。 裴西洲笑着伸手擋住她眼睛不讓她看:“不疼。” 南風瞬間紅了眼:“騙人!” 卻聽見他嘆氣,清冷聲線盡是無奈:“見不得你哭。”
36.3萬字8.18 15565 -
完結510 章

改嫁總統后,假千金成團寵了!
【真假千金+團寵+閃婚+萌寶】大婚當天,許栩沒等來新郎,卻等來了未婚夫霍允哲和許雅茹的曖昧視頻。 她滿腹委屈,給遲遲未來婚禮現場的養父母打電話。 養父母卻說:“感情這事兒不能強求,允哲真正喜歡的是雅茹婚禮,趁還沒開始,取消還來得及。” 直到這刻,許栩才知道,得知她和許雅茹是被抱錯的時候,養父母和霍允哲就早已經做好了抉擇! 不甘成為笑話,她不顧流言蜚語,毅然現場征婚。 所有人都以為她臨時找的老公只是個普通工薪族。 就連養父母都嘲諷她嫁的老公是廢物 卻不想海市各方大佬第二天紛紛帶著稀世珍寶登門拜訪! “海市市長,恭賀總統新婚!送吉祥龍鳳玉佩一對!” “海市民政局局長,恭賀總統新婚,送錦緞鴛鴦如意枕一對!” “海市商務部部長,恭賀總統新婚,送古董梅瓶一對!”
59.8萬字8 3582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