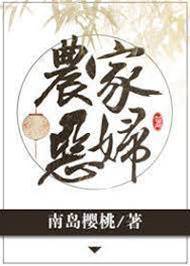《春江花月》 第 63 章 第 63 章
有這樣一支衛隊護送,此行必定安然無憂。
同時傳來的,還有另一個消息。
那就是伯父好似對伯母的這個決定很是不滿,據說兩人大清早地就爭執了起來。
但高桓對此,表示并不關心。
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就在自己以為出行無的時候,事竟然峰回路轉了!
伯母既開口了,以高桓那點淺薄的生活經驗來推斷,基本就表示,這趟義之行,板上釘釘了。
高桓狂喜,飛奔到了阿姊的跟前,見已收拾好了東西,面帶微笑,問他可做好了準備?
便是如此,三月的這一天,高桓懷著對長公主伯母的無限拜之,盡量忽略掉伯父那張難看至極的沉臉孔,騎著高頭駿馬,護送著坐于車中的阿姊,躊躇滿志地出了建康,抵達渡口,上了一條大船。
大船將隨一支運送軍糧的船隊沿江西去,抵荊州后,上北岸,到郡,然后再循他曾想象過無數遍的那條行軍之道,一直北上,去往此行的目的之地,義郡。
高嶠站在渡口,目送著那艘被軍船護簇在中間的大船揚帆,漸漸遠去,消失在了江波盡頭。
他轉臉,看了眼邊的妻子,見視線還落在兒離去的方向,心中之不滿,此刻依舊沒有消盡,皺雙眉,一語不發,撇下了,背著雙手,徑直便去了臺城。
向晚,將近戌時,高嶠才結束了一日朝事,回到高府。
原本以為今日如此爭執過后,妻子已經回了白鷺洲。高嶠滿腹心事地了屋,卻意外地發現竟還在。
Advertisement
發猶髻,未解,端坐于房中,似乎在等著自己。
高嶠一怔,想起今早不顧自己反對,竟執意安排兒去往義的一幕,心里的火氣又上來了,沉下了面,也不,只站著,淡淡地道:“不早了,你還不去歇?”
蕭永嘉凝視著他,雙眸一眨不眨。
高嶠見不說話,又被如此盯著瞧,漸漸又有些繃不住了。皺眉道:“阿令,非我責你,只是這回,你的行事,實在莽撞!倘是別事,哪怕李穆對我再不敬,我亦不會將兒如此帶回。你也不小了,早不是從前可以胡鬧的年紀,為何還是如此不懂事,任不改!都二十年了,你卻毫沒有長進!實是我失!”
他說到后來,痛心疾首。
蕭永嘉依舊那樣著他,似乎毫沒有在意他的這番訓斥。
高嶠只覺無奈至極,扶額,長嘆一聲。
“罷了罷了!兒都被你送走了,我又何必和你再說這些!你歇了吧,我去書房了!”
他轉要走,卻見蕭永嘉忽地朝自己出了笑容。
屋里燭火耀燦,本就映得若凝,這一笑,更是珠輝玉麗,艷無邊。
高嶠不自覺地停了腳步,狐疑地皺了皺眉:“你笑為何意?”
“高嶠,我知你對我一向失。我本就是如此之人,這一輩子,大約也是改不了了。”
“不如我再告訴你,就在不久之前,我還殺了一個人。你是不是要將我送去大理寺,大義滅親,以正法紀?”
蕭永嘉止了笑,凝視著他,幽幽地道。
Advertisement
高嶠盯了片刻,眉頭皺得更了。
“阿令,你在胡說什麼?”
“我沒有胡說。”
蕭永嘉著丈夫那張端方正氣的臉,眸變得有些飄忽了起來。
“朱霽月。朱霽月就是我殺死的。”
一字一字地說道。
高嶠大吃一驚,愣在原地片刻,驀然仿佛回過了神兒,快步來到妻子的邊。
“阿令,你沒在胡說八道吧?怎會是你殺的?”
他仿佛有些不放心,抬手要去額頭。
蕭永嘉避開了他過來的那只手掌。
“你沒有聽錯。是我殺的。那日企圖勾引李穆,約他去青溪園,被我得知,我大怒,闖了過去,和起了爭執,拿劍在手,奪我劍,腳下沒有站穩,摔了過來,我的劍便刺的脖頸,就那樣死在了我的手下。”
高嶠定定地看了片刻,問道:“那場火呢?火又是怎的一回事?”
“李穆趕到,送我回來,幫我放了那一把火,將事蓋了過去。”
高嶠驚呆了,神僵,立著一不。
“當年我害死了邵玉娘,如今我又親手殺了一人。你大可以將我告至前,也可休了我。我不會怪你,更不會再勉強要你和我續做夫妻。”
屋里沉寂了下去。
“罷了……聽你之言,你也非故意殺……事既過去了,罷了便是……”
他的臉還是極其難看。
半晌,方道了一句,聲音聽起來,極是艱。
蕭永嘉微微一笑。
“多謝。”
高嶠了一眼,眼底流出一復雜的神。臂膀微微了一。手似要朝去,到一半,卻又慢慢地收了回來。
Advertisement
“不早了,你歇下吧——”
他喃喃地道,慢慢地轉過了。
“你且留步,我還有一事。”
后忽然又傳來蕭永嘉的聲音。
高嶠轉頭,見從袖中取出了一只香囊,解開,倒出一面玉佩。
那玉佩潔如云,面雕云藻紋案,是為男子的腰飾之佩。
只是下頭懸著的結有些褪,應是有些年頭了。
蕭永嘉將玉佩托于掌心,端詳了片刻,輕輕放于案面,朝他推了過來。
“高嶠,這東西,你應該還有印象吧?君子比德于玉。這東西,從前是我從你那里強行要來的。如今我還給你了。”
高嶠茫然了片刻,終于,認了出來。
這玉佩原是自己所有。
依稀也想了起來,那是很早之前的事了,似乎那一年,蕭永嘉還只有十三歲。
也是那年的曲水流觴會上,仗劍風流的高氏世子,在樂游苑里,偶遇了皇室小公主。
桃花樹下,傲慢地攔住了他。指著他腰間懸著的玉佩,說紋路不錯,要宮中玉匠照著鏤出一塊,用完便還,隨后不由分說,將東西從他上摘走了。
后來,那玉始終沒有歸還。
再后來,他也尚了,了他的丈夫。
這麼多年下來,高嶠早就已經忘了自己還有一塊玉佩,一直留在蕭永嘉的手里。
他抬起眼,看向自己的妻子,臉上一片茫然:“阿令,你這是何意?”
“高嶠,你的玉佩,當年是我強行從你那里要來的。不是我,終究不是。我還給你了。”
“這些時日,我一直在反省自己。當年本就是我強行嫁你,這些多年來,我更是沒有盡到為妻本分。我知你也容忍我多年,很是對不住你。如今我想通了。你若愿和我和離,我們和離便是。你若顧忌名聲,或是怕兒傷心,再要維持你我夫妻名分,我亦無不可。”
Advertisement
“你人過中年,膝下卻只有阿彌一個兒。是我耽誤了你。倘你不愿和離,往后,盡可納妾,為高氏開枝散葉,免得你這一脈,在你這里斷了香火。”
高嶠呆若木,一不,全然沒了反應。
蕭永嘉從案后起,從他旁經過,走到門口,轉頭又道:“今日我之所以不顧你的反對,送了兒去往義,是因我知兒大了,不愿再事事聽憑你我安排。想去,就去一趟。我相信阿彌,是非曲直,自有判斷。”
“至于人之福禍,更是無常。譬如當年,我你若狂,嫁你之時,當為我此生最為歡欣時刻。那時我又怎會想到,終有一日,你我會落今日地步?”
說完,開門,出面前那道門檻,走了出去。
。
猜你喜歡
-
完結540 章
醫品庶女代嫁妃
中西醫學博士穿越成宰相府庶出五小姐,憑藉著前世所學的武功和醫術,懲治嫡出姐姐,鬥倒嫡母,本以爲一切都做得神不知鬼不覺,卻早已被某個腹黑深沉的傢伙所看透。既然如此,那不妨一起聯手,在這個陰謀環繞暗殺遍地的世界裡,我助你成就偉業,你護我世世生生!
97.3萬字8 169441 -
完結177 章

重生之賢妻難為
上一世,她是將軍府的正室夫人,卻獨守空房半生,最後落得個被休棄的恥辱。直到她年過四十遇見了他,一見鍾情後,才發現遇他為時已晚。 今世,上天待她不薄,重生那日,她便發誓,此生此世必要與他攜手一世,為他傾盡一生。
39.6萬字5 7707 -
完結15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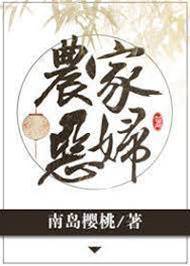
農家惡婦
何娇杏貌若春花,偏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恶女,一把怪力,堪比耕牛。男人家眼馋她的多,有胆去碰的一个没有。 别家姑娘打从十四五岁就有人上门说亲,她单到十八才等来个媒人,说的是河对面程来喜家三儿子——程家兴。 程家兴在周围这片也是名人。 生得一副俊模样,结果好吃懒做,是个闲能上山打鸟下河摸鱼的乡下混混。
48.4萬字8 668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