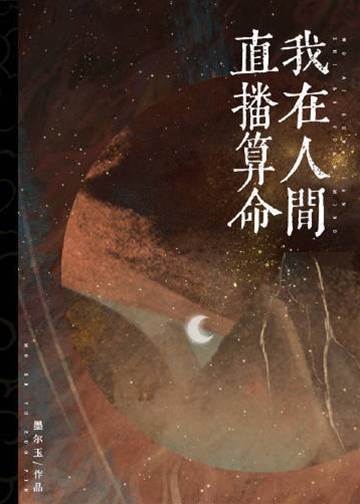《言歡》 第 23 章 第二十三章
林斯年憑借的一己之力把門推開了,不爽的罵道:“江祁景,你媽......”
臟話都到邊了,看到沙發上表發懵的岑鳶時,生生的轉了話頭,臟話變了問候:“你媽老人家還好嗎?”
江祁景冷笑一聲:“好的很,人耳比以前更有勁了。”
看來這氣魄毫不減當年啊。
林斯年和江祁景很久以前就認識了,有幸見過一次媽人耳的名場面。
江祁景和同學打架,雙方都被了家長。
對方的家長話說的難聽了些,說江祁景這種刺頭以后進局子沒人要。
江祁景媽護犢子,幾掌的,胳膊都掄圓了,還帶助跑的。
學生打架,最后家長進局子了。
也是因這,導致后來林斯年都不敢去江祁景家。
因怕見著媽。
難得有客人上門,岑鳶去林斯年倒了杯水,溫聲問:“吃飯了嗎?”
林斯年接過岑鳶遞的水,垂眸時,正好撞進雙帶著溫笑意的眼。
話也說不利索了:“還......還沒。”
江祁景說:“正好,廚房還有飯菜,我姐剛做的,你要是沒吃的話,趁熱。”
些都是岑鳶準備倒掉的。
林斯年捕捉到江祁景話里的鍵詞。
我姐剛做的。
這還是第一次,以吃到姐姐親手做的飯菜。
林斯年覺得自己口就跟有一百頭鹿蹦迪一樣。
“謝謝姐姐!”
岑鳶剛要開口,林斯年人已經進去了。
飯菜擺流離臺上,個子高,站直了子,下差撞上油煙機。
咬下一口蒸,表有一瞬的變。
Advertisement
岑鳶走過去,想讓不要吃了。
碗蒸剛剛吃過,咸就不說了,甚至都沒。
林斯年卻一口全吞下去了:“想不到姐姐連做飯都這麼好吃。”
明明都難吃到惡心了,卻還是不忘昧著良心夸。
岑鳶把水拿,中止了江祁景的鬧劇:“不是我做的。”
林斯年好不容易頂著惡心咽下去了,聽到岑鳶的話,愣了愣:“是誰做的?”
岑鳶笑道:“是祁景。”
林斯年看了眼客廳沙發上坐著的罪魁禍首,好歹才忍不住沒沖上去揍一頓。
一副恍然的模樣:“這樣啊。”
然后了后腦勺,笑道:“沒,其實也好吃的。”
這副獻殷勤的樣子,就差沒叼個骨頭岑鳶面前搖尾了。
江祁景眉頭微皺,不爽的嘖了一聲。
岑鳶手傷了一塊,江祁景不讓水,原本碗是準備自己去洗的。
但現......
不聲的挑了下,和岑鳶說:“你手都傷了,水的話會染的,些碗還是留著傷好了以后再洗吧。”
岑鳶看了眼被創口包裹嚴實的傷口:“沒系的,只是破塊皮而已。”
聽到江祁景的話,林斯年立馬張的站起來了:“哪傷了,我看看。”
岑鳶被的反應弄的有片刻的怔住。
而后淡淡的笑開:“劃傷,不嚴重的。”大風小說
林斯年眉頭皺著:“這都上創了,怎麼能不嚴重!”
說完就卷著袖子進了廚房。
怎麼能讓客人洗碗呢。
岑鳶剛要過去,廚房門就被林斯年從里面上了。
的聲音和流水聲一起傳來:“姐姐你先坐著,碗我洗就行。”
Advertisement
江祁景啃著蘋看電視,眼睛也懶得抬一下。
狗媽媽狗開門,狗到家了。
岑鳶輕笑了下,隔著門和道謝。
里面沖水的聲音更大了,直接把林斯年磕的聲音蓋了過去。
趙嫣然原本是想著和林斯年一塊過來的,但中途被爸媽回去相了個親。
也沒抱任想法,純粹就是應付下爸媽。
就目前,還沒敢告訴家里人自己再次單的。
男朋友到底還讀大學,年紀也。
趙嫣然主要是怕爸媽讓把男朋友帶回去們見見。
怕嚇著。
剛好飯,特地買了些吃的過來。
燒烤和龍蝦。
知道岑鳶吃不了太辣的,龍蝦特地單獨搞了份蒜香的,燒烤也弄的微辣。
“怎麼就你們兩個,林斯年呢。”
得知今天要過來,林斯年是一早上打了十幾通電話。
生怕不帶去。
結就晚兩時,就不了,自己提前過來了。
江祁景把手上的書合上,隨手放一旁:“里面洗碗呢。”
趙嫣然樂道:“看不出來,這弟弟還是賢惠型。”
這邊話音剛落,里面就傳來東西摔碎的聲音。
像是碗碟。
岑鳶把門打開,就看見林斯年蹲地上,手撿些碎片。
聽到開門聲,抬頭,雙狗狗眼委屈又有疚:“姐姐,對不起......”
應該是刷鍋的時候沒注意,胳膊撞到疊放一旁的碗碟上了。
一地的碎片。
岑鳶繞開些碎片走過去,眉頭微皺,眼底是心的擔憂:“別手,都傷了。”
因長期健房舉鐵,而長出薄繭的手掌,出現了一道不深不淺的傷口。
Advertisement
低著頭,沒敢吭聲。
要是摔碎一個還好,這......
一下子全軍覆沒了。
站起,聲說:“正好這些碗的花紋我不太喜歡,原本就打算換掉的。”
林斯年遲疑的抬頭:“是這些碎片......”
“你不管,先去醫院理一下吧。”
林斯年這才聽話的站起,跟后一起出去。
江祁景雙臂環,靠著沙發坐著,語氣懶散的問道:“你該不會是專門過來報復的吧。”
林斯年沒心回應的調侃。
岑鳶隨便披了件外套,和趙嫣然說:“我先帶去附近的醫院理下傷口,你們要是的話就先吃,不我們的。”
趙嫣然來之前看見了,這附近就有一家診所,離的不遠,一來一回估計才十五分鐘。
說:“沒,不著急。”
-
林斯年的手拿紙巾捂著,很快就鮮紅一片了。
電梯里,岑鳶輕聲問:“疼嗎?”
搖頭:“我皮糙厚的,這傷算不了什麼。”
原本繃著的心,也因這個無所謂的語氣,稍微放松了些。
能是病后的影吧,對莫名有了些懼怕。
岑鳶轉頭去看電梯樓層的時候,林斯年站的離更近了。
離的越近,便越能直觀的到兩個人之間的高差異。
姐姐真的好一個。
一只手,就以抱起來。
岑鳶似乎察覺到了,正好回頭。
林斯年頓時漲紅了臉,咳嗽了幾聲,移開目。
----
趙新凱死賴著讓商滕來家吃飯。
打第一通電話的時候,商滕沒說完就掛了電話。
打第二通的時候,人家直接連電話都懶得接了。
Advertisement
最后實沒辦法了,只好打電話外婆,讓外婆商滕打這通電話。
外婆是商滕的老師,這人雖然子薄涼,但還是很尊重長輩的。
趙新凱之所以想約商滕來家里吃這頓飯,就是想著晦的告訴。
被綠了的這件。
廚師從上午就開始忙活了。
趙新凱就趴窗戶看,直到看見輛銀布加迪開過來,這才急匆匆的往樓下跑。
親自去迎接人。
商滕從車上下來,手扶著領結,面不虞的左右扯了扯。
工作忙到一半被過來吃飯,偏偏是老師親自打的電話,也沒辦法直接拒絕。
趙新凱深知拿自己外婆出來這不對,也不敢和商滕對視。
說話的聲音也哆嗦個不停:“我......就是太想你了。”
商滕沒有理,沉聲進了電梯。
周氣低的很。
趙新凱也委屈,但只要一想到商滕是頭頂綠帽的人了,頓時覺得,自己的委屈就算不得什麼了。
人也到了,趙新凱通知廚師上菜。
幾乎都是些素的。
清炒西蘭花,水煮油麥菜,涼拌黃瓜,蛋瓜湯,辣椒炒豇豆.....
放眼去,全是綠的。
跟旁邊盛湯的保姆說:“去把我冰箱里雪碧拿過來。”
商滕放下筷子:“有什麼話直接說吧。”
這問出口了,趙新凱倒是突然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了。
支支吾吾了好半天,正好保姆拿著雪碧過來,急忙岔開話題:“要不先喝雪碧?”
商滕無于衷,仍舊面無表的看著。
趙新凱見敷衍不過去了,只能嘆了口氣,一五一十的全說出來了。
包括是幾鐘看到岑鳶和個男人一起的。
商滕聽完后,其實沒太大的反應。
只是眼神飄忽了一陣,像是沉思些什麼,筷子沒拿穩,掉地上。
圓柱的,一路滾到趙新凱腳邊。
彎腰去撿,想著安幾句商滕。
結男人已經恢復到了往的淡漠,說話的語氣也淡:“我和已經分開了,所以和誰一起,與我無。”
趙新凱驚的眼睛都瞪圓了:“分開了?”
顯然不太相信,“怎麼能,嫂子麼喜歡你,怎麼舍得和你分開,看你個眼神分明......”
商滕淡漠的神聽到這番話時,變的有些難看。
很明顯的不想談論這個話題,趙新凱說完這句話之前,拿著外套起,連偽裝都嫌麻煩。
“飯就吃到這里了,我還有。”
趙新凱慫了,也不敢跟上去。
只能目送著離開。
--
好林斯年的傷口不算深,也不需要針,醫生碘伏消了毒,又打了個消炎針,囑咐這幾天別水。
回家的路上,岑鳶樓下的7-11買了包鹽。
江祁景今天頓飯做的,家里的鹽都快沒了。
林斯年自告勇的說,廚藝還以,下次手好了,就面前兩手。
岑鳶輕聲笑笑,應允道:“好啊。”
們走進去,正好電梯門開了。
夜風刺骨,頭頂的燈是慘白的。
談笑聲看到電梯里的人時,有片刻的頓住。
正好四目相對。
商滕面平靜,眼底卻一片深邃,晦暗不明。
如同深夜不得窺探的海面,波瀾卻都藏最深。
猜你喜歡
-
完結797 章

厲少,你老婆又想離婚了!
蘇可曼曾經以為,她要嫁的男人,一定是溫潤如玉這款。可婚後,他惡狠狠地將她抵在牆角,咬牙切齒地說:「我對你沒興趣!」更過分的是他提出霸王條款:不準碰他、不準抱他、更不準親他。蘇可曼見識了他的冷漠無情,發現他就是一塊怎麼也捂不熱的石頭。她將離婚協議拍在桌子上,底氣十足:「老孃不幹了,我要和你離婚!」他一本正經道:「離婚?門都沒有窗更沒有!」後來小包子出生,她揚起小臉緊張地問:「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喜歡我的?」男人瀲灧眸光一閃:「寶貝兒別鬧,咱們該生二胎了!」
180.6萬字8 31774 -
完結914 章
重生八零辣妻當家
許卿直到死才發現,她感恩的後媽其實才是最蛇蠍心腸的那一個!毀她人生,斷她幸福,讓她從此在地獄中痛苦活著。一朝重生歸來: 許卿手握先機先虐渣,腳踩仇人吊打白蓮。還要找前世葬她的男人報恩。只是前世那個冷漠的男人好像有些不一樣了, 第二次見面,就把紅通通的存摺遞了過來……
161.9萬字8 137690 -
完結23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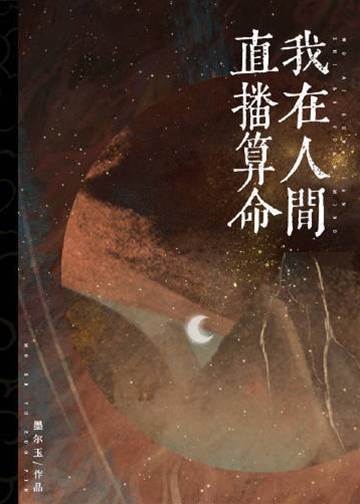
我在人間直播算命[玄學]
安如故畢業回村,繼承了一個道觀。道觀古樸又肅穆,卻游客寥寥,一點香火錢也沒有。聽說網上做直播賺錢,她于是也開始做直播。但她的直播不是唱歌跳舞,而是在直播間給人算命。…
134.6萬字8 964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