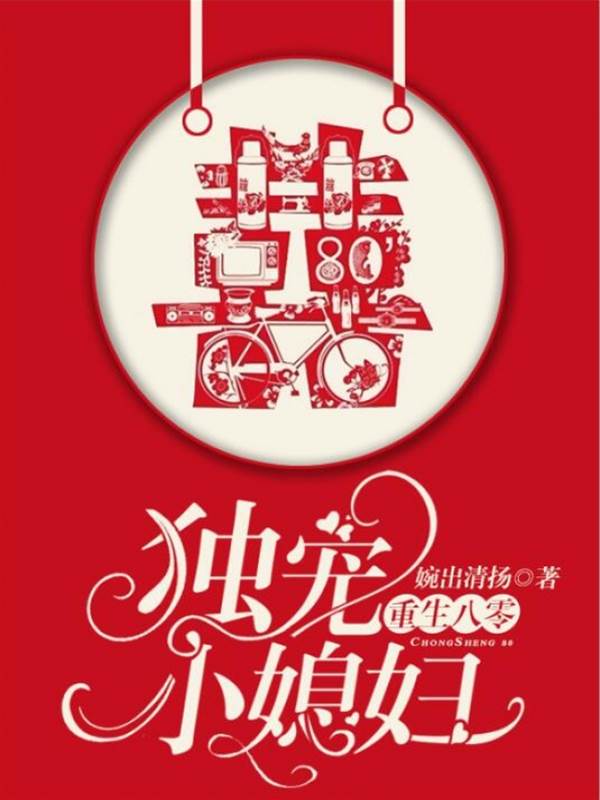《杳杳歸霽》 第29章 奶鹽
蘇稚杳眼睛泛起亮,激地跳過去,一把抱住脖子:“謝謝您!”
saria出蒼老的手掌,輕輕了靠在頸側的腦袋:“剛剛,賀來過電話。”
賀司嶼?
蘇稚杳愣住兩秒,頭從肩上離開,慢慢抬起臉:“他……說什麼了?”
“也沒什麼。”saria含笑:“只是說你不耐,吃不了制品,他為我們訂了晚餐,稍后送到。”
蘇稚杳眼睫忽兩下,心難以言喻。
那份解約協議像是從潘多拉盒子里走的禮,到手前,心安理得經不住.,到手后,又讓十分的空虛。
過去的每個細節都在反噬著,加重的負罪。
老天仿佛是故意要應證給看。
后面的某一天,蘇稚杳收到一個來自國的特運包裹,同時接到zane的電話。
當時是個中午,蘇稚杳坐在房間的窗前。
saria的別墅在維也納的郊區田園,兩扇復古酸枝木格窗向外推開,是片的麥田和草場,當地的孩子們穿著奧地利傳統伐利亞,腰繩,亞麻面料漂亮的大擺,在金燦燦灑落的草坪上跳格子。
悠遠的歡聲笑語漾在空氣中。
蘇稚杳將收到的包裹擱到上,攏著剛吹干的黑的長發,撥到一邊用手指梳理,另一只手握著手機和zane通電話。
zane聽聞在奧地利準備比賽,特意空鼓勵,順便給了一些彈奏上的小建議,蘇稚杳很開心,師生許久未見,一聊就是一個多鐘頭。
蘇稚杳回想起場票的事:“之前托您的福,我才能聽到港區國際藝節的演奏,特別彩,下回到紐約,我請您吃個飯。”
Advertisement
電話里,zane笑了幾聲:“你的場票,是賀出的面,他沒和你說嗎?”
窗外一陣清風拂面而過,揚起蘇稚杳鬢邊的一縷碎發,又輕悠悠落下。
怔忡著問:“您說的是……賀司嶼?”
“沒錯,我還以為你們已經相識了。”
蘇稚杳在風中靜止住,通話終了,還愣著,無形中有一召力,若有所思垂下眼,去看上那個來自京市的包裹。
鬼使神差,將包裹一層層拆開。
一只白玉雕花的首飾盒,別有幾分眼,打開來,里面竟是曾經搶先賀司嶼競拍下的那對graff稀世鉆的其中一顆。
蘇稚杳不可思議,頭緒有些,驚奇地順著包裹預留信息,艱難得到寄件方的電話。
“您好,這里是華越國際。”
耳邊響起前臺工作人員清悅的聲音,蘇稚杳眼中的疑更濃,言簡意賅地將自己收到包裹的事復述一遍,詢問況。
“您稍等。”工作人員前去接,幾分鐘后,電話對面換了人,一個男聲道:“您好,蘇小姐,我是盛先生的助理。”
蘇稚杳心跳莫名急促起來,握手機,應了一聲,隨后便聽見助理向說明。
他說,先前賀先生為在華越國際投放生日巨屏和燈秀,這對鉆是他作為與盛先生的換,不過盛先生只需要一顆,所以另一顆歸原主。
原來生日那天,給了全京市最盛大排面的人,是賀司嶼。
蘇稚杳嚨一哽,呼吸難以自控地加重。
怎麼好像全世界同時在提醒,賀司嶼的好。
那天晚上,蘇稚杳在書房練琴。
的手指行云流水地起落在琴鍵上,每個音階的節奏都準無比,可聽來明顯虛浮在表面,緒如一片寂靜的死海,古井無波,的手有如敲琴鍵的機,靈活,但沒有。
Advertisement
saria扶了扶墜鏈老花眼鏡,目從書里抬起來,過去,凝眉道:“杳杳,你心不在焉。”
琴音一止,尾聲漸漸如風消散。
蘇稚杳指尖蜷了蜷,雙手離開琴鍵,垂下去,擱到上悄悄手指,低悶的聲音在書房里顯得有些空遠。
“……對不起。”
的問題并非技巧上的,saria放下書,起走到邊,掌心落到肩膀,輕輕一握:“親的,你有心事。”
蘇稚杳低著頭默認。
的確有心事,心事在心臟上,得快要不過氣。
“在想他?”saria一語破的,活到這歲數,很多事輕易就能看出一二,何況曾經也有過小孩的時。
蘇稚杳心跳停了一秒,仰起臉。
寶石般漂亮的淺褐瞳眸前,仿佛輕籠著一層迷霧,看不清前路,模樣像一只迷失森林,沒有方向的鹿。
saria俯下,心疼地了下的臉,擁住,語氣溫:“我可憐的孩子,今晚好好睡上一覺,明天就好了。”
蘇稚杳臉埋在前,無力地閉上眼,還是為自己今晚的不認真道歉:“對不起……”
saria搖搖頭,拍的背。
蘇稚杳泄下一勁,闔著眼睛不愿意睜開。
這種覺太折磨,哭不出來,無法宣泄,但腔明明白白被緒堵塞著,從沒有這樣過。
逃避之所以這麼難,覺得。
自己可能有一點喜歡他……
……
初賽的前一天。
鄰居辦生日派對,邀請saria和蘇稚杳過去共同慶祝,蘇稚杳心還是低落,原本想要婉拒,在家中練琴,但saria極力勸,表示需要放松。
Advertisement
再推辭不禮貌,蘇稚杳便答應下。
saria拿出奧地利的傳統服飾給,一套碎花伐利亞,里面是花苞短袖的亞麻白襯衫,外面的背心收腰,連著大擺,刺繡的碎花,鑲邊墨綠條紋。
蘇稚杳穿著正好合。
派對還在準備,saria在別墅里與鄰居談,房子里忙碌的都是老一輩,蘇稚杳想幫忙,被大人們笑哈哈地推到小朋友那一撥里頭。
于是蘇稚杳就去到草坪,和孩子們一起玩。
春日的和地照著草坪,孩子們都很有活力,蹦蹦跳跳,追逐打鬧。
蘇稚杳雙手捧著臉,想蹲在一旁看,但孩子們都很熱,跑過來拉起,要加。
們想要玩一種卡迪的游戲,只是簡單玩鬧,并沒有賽場上那麼激烈,規則或許類似于中國的老鷹抓小。
蘇稚杳一向不喜歡奔跑追趕,但被一群朝氣蓬的小孩染,多日以來心的抑郁在那一刻煙消云散。
從茫然被,到逐漸融,蘇稚杳很快就和們玩開了。
笑著和孩子們追逐起來,一蹦一跳,又撲又閃,伐利亞跟著搖擺。
玩游戲難免磕磕絆絆,蘇稚杳被追的時候,一連后退幾步,猝不及防踩到一雙皮鞋,跌倒的瞬間下意識回過。
還沒看清踩著誰了,人穩不住,一聲驚呼下,帶著慣往前,撲進一個溫暖實的懷抱。
那人被撞得往后一仰,摟住腰雙雙倒了地。
蘇稚杳沒摔在草地,在了他的上。
天旋地轉后,雙手扶著他的肩,支起上半,一抬起頭,看到男人的臉。
濃眉,高鼻,薄,右眼尾淚痣淺淡……
Advertisement
落在他的黑短發,他的臉,還有他被撞得散開的西裝外套上,仿佛灑下金。
蘇稚杳呼吸窒住,眼前出現迷幻暈。
回過神,忙不迭想要起,橫在后腰的那只胳膊突然往回一勾,驀地往下撞回進他懷里。
連著,連著。
下落的瞬間,鼻尖和他的輕輕一,剎那間被他滾燙的氣息和上的烏木香包圍。
屏著氣,注視著彼此的眼睛。
“跑什麼?”賀司嶼輕聲。
低低的音節仿佛石子墜落進的心湖,漾起一圈圈的波瀾。
蘇稚杳心臟怦得厲害,快要不能思考:“你……你怎麼過來了?”
他逆著,微微瞇起眼,低啞的嗓音從間慢慢出。
“來抓某只始終棄的壞貓。”
蘇稚杳徹底喪失思考能力,不敢呼出一氣。
賀司嶼極近距離盯著。
右耳邊別著一只雪絨花發夾,長發凌的散落下來,有幾掃著他的臉。
臉瓷白亮,雙頰暈著剛剛運過的紅,這套伐利亞在上格外修,鎖骨前著一片雪白,部夠勾勒得圓潤,腰肢纖細,握著很有手。
奔跑在草坪上,像個麗的牧場郎。
方才遠遠看到的第一眼,賀司嶼就生出一個強烈的心思。
想要。
猜你喜歡
-
完結853 章

他是人間妄想
人間妖精女主VS溫潤腹黑男主 三年後,她重新回到晉城,已經有了顯赫的家世,如膠似漆的愛人和一對可愛的雙胞胎。端著紅酒遊走在宴會裡,她笑靨如花,一轉身,卻被他按在無人的柱子後。他是夜空裡的昏星,是她曾經可望不可即的妄想,現在在她耳邊狠聲說:“你終於回來了!” 她嘴唇被咬破個口子,滿眼是不服輸的桀驁:“尉先生,要我提醒你嗎?我們早就離婚了。”
148.9萬字8 178796 -
完結455 章

成了前任舅舅的掌心寵
“你是我陸齊的女人,我看誰敢娶你!”交往多年的男友,娶了她的妹妹,還想讓她當小三!為了擺脫他,顏西安用五十萬,在網上租了個男人來結婚。卻沒想到,不小心認錯了人,她竟然和陸齊的小舅舅領了 證。他是國內票房口碑雙收的大導演,謝氏財團的唯一繼承人,也是那個惹她生氣後,會在她面前跪搓衣板的男人!有人勸他:“別傻了,她愛的是你的錢!” 謝導:“那為什麼她不愛別人的錢,就愛我謝靖南的錢? 還不是因為喜歡我!”
39.9萬字8 23728 -
完結4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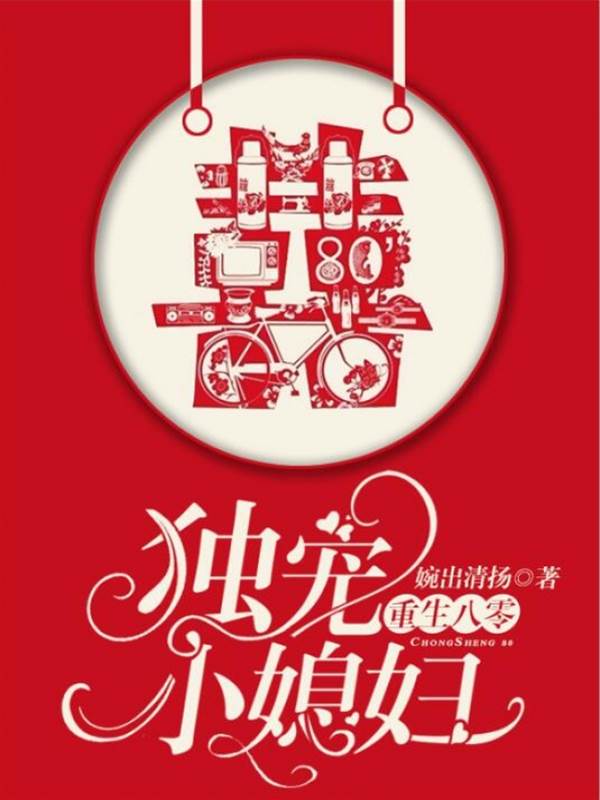
重生八零:獨寵小媳婦
九十年代的霍小文被家里重男輕女的思想逼上絕路, 一睜眼來到了八十年代。 賣給瘸子做童養媳?!丟到南山墳圈子?! 臥槽,霍小文生氣笑了, 這特麼都是什麼鬼! 極品爸爸帶著死老太太上門搗亂? 哈哈,來吧來吧,女子報仇,十年不晚吶,就等著你們上門呢!!!
72萬字8 960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