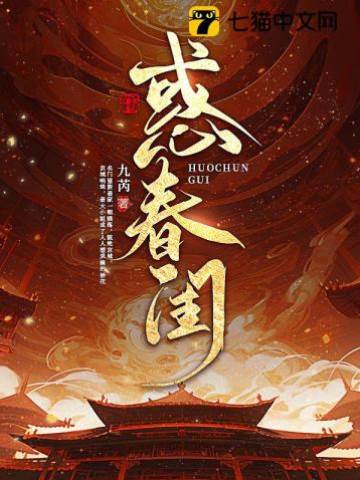《醫妃難囚:王爺請聽命》 第六百五十一章 滴水之恩 湧泉相報
林醉柳滿意地點點頭,又急急忙忙地轉過子,看著廖鑾的臂膀,皺了皺眉,把他上方才扎的針,又一一地取了出來,放置在一旁。
「放心吧銘玄,這方面阿柳的技可是比我厲害多了。」看著銘玄還是一臉皺著眉,不大放心的表,倉青也在一旁勸說著他。
銘玄沒有靜,過了片刻,才重重地點了點頭。
林醉柳看了他一眼,無奈地笑了笑,作嫻地捻起一銀針,在那燭焰上一略而過。
接著,眾人還沒怎麼看清,只見林醉柳的手一晃,那銀針,已經是扎紮實實地落在了蛇的皮上。
作乾脆利落,毫不拖泥帶水。
是淺淺地刺了進去,周遭一點跡也看不見。
銘玄懸著的心,放心了。
接下來,林醉柳一套行雲流水般的作,那蟒蛇上,深深淺淺共刺進去約莫二十銀針,看上去有些恐怖。
銘玄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氣,心裏覺得有些心疼,不忍看。
「等個幾刻鐘便可。」林醉柳說道。
本想讓銘玄休息一會兒,喝些水,可是看他的樣子,也是不願意離開,張兮兮,林醉柳便把到了邊的話給咽下了。
其他三人,便陪著銘玄一起等。
「好了。」林醉柳一看時刻到了,趕上前,把那銀針一一利索地取出來。
取到最後一的時候,那蟒蛇的整個子猛然一!
「這!」銘玄的心,立馬就提到了嗓子眼。
「莫要張。」林醉柳一邊說著,一邊把那最後一針放在燭焰上炙烤著。
這針可是扎過劇毒的蟒蛇,得好好理一番再收起來才行。
「方才不過是刺激到神經了,這自然反有些大了,它還不會醒過來,約莫得到了晚上再進行一次針灸方可。」林醉柳說道,一臉認真地在理銀針。
Advertisement
銘玄卻是一直皺著眉。
還要等到晚上?
林醉柳瞥了他一眼,似乎是看得出來銘玄心裏在擔心什麼,便起了子,示意銘玄自己去看看那蟒蛇的況。
銘玄立馬上前蹲下,指尖輕輕地到那蛇的皮,知著。
他的表,倒是忽然放鬆了,自然,銘玄到了,這蛇的況好了很多。
「辛苦了。」銘玄起,朝著林醉柳道謝。
「不必多謝,既然是倉青的朋友,便是我的朋友。」林醉柳大大方方地回到。
聽見這句話,銘玄倒是忽然抬起頭,看著林醉柳,雙眸的目很是複雜。
廖鑾看著銘玄的目,微微皺起了眉頭。
到了晚上,兩人又照例過來為那蟒蛇針灸。
林醉柳說的果然沒錯,一整套下來,沒過一會兒,那蟒蛇便睜開了疲倦的眼睛,不過看上去還是極其虛弱。
銘玄大喜,手,輕輕安這那蟒蛇的緒。
「激不盡,這接下來的調養,就不勞煩王妃了。」他拱手作揖,說道。
林醉柳點點頭,還想再聽銘玄說些什麼,銘玄倒是沒了下文,還有要送客的意思。
一臉迷,看向廖鑾。
廖鑾倒是一臉淡然,回了林醉柳一個意味深長的笑。
「銘玄醫師,可否借一步說話?」廖鑾開口。
銘玄自然,是沒有拒絕的。
就是他沒有想到,這大晚上的,北環的王爺,竟是把自己帶到了房頂上。
「銘玄醫師,此前可是聽說過本王。」廖鑾先開口道。
「冷鎮南王,南疆誰沒聽說過你的名號,雖說我先前常年在山中,但是我師父也提起過你。」銘玄回答道。
「那你見了本王覺得如何,可是配得起冷二字?」廖鑾又問到。
銘玄皺了皺眉。
倒也,不是那麼冷。
「蛇也是王妃救得,若說王爺心冷心熱,講實話老夫看不大出來,但看在王妃的面子上,王爺應當也是個好人吧。」銘玄馬馬虎虎地說。
Advertisement
「你與倉青,可是和解了?」廖鑾冷不丁地冒出來一句。
銘玄只覺得這王爺的問題,越來越無厘頭了。
其實是廖鑾找倉青聊過了,也知道,當年的所有事,甚至知道,銘玄心裏,這麼多年一直揮之不去的那個坎兒。
「倉青變了很多。」銘玄半晌沒有說話,才憋出來這一句話。
他沒有說是否和解,是因為不清楚倉青怎麼想,不過是想聽倉青說出當年的,就這麼困難嗎。
那時同在一個師門,可是無話不談的好兄弟啊……
「人總是會改變的,曾經本王以為,這世上,遇不到會讓本王心的子了。」廖鑾輕笑一聲,頗有慨地說道。
「你想說什麼?」銘玄趕打斷了廖鑾的話,問到。
他怕再讓廖鑾說上去,自己怕不是要聽上一大段的,這王爺和王妃的故事?
「哎,你當真以為,本王回來,單純是為了救你的蛇?」
「王爺請繼續講。」銘玄愣了愣,旋即便恢復了。
「一來,是王妃擔心倉青應付不了,路上一直在想那蛇為何遇害,也想出了些眉頭。而來,則是本王的私心了。」
廖鑾不不慢地說道。
「私心?」銘玄疑。
他心裏並不難過,倒是很意外廖鑾願意跟自己說實話。
「本王雖與倉青不悉,但是也認識的久了,看得出,這學醫,在倉青心裏還是個執念,靖王此前也與本王聊過,找人三番五次請倉青去這靖王殿做太醫,他盡數拒絕。」
「想必,是時候不對吧,若是倉青剛出山時,靖王能拋出橄欖枝,如今的倉青,怕不就是靖王殿頗有資歷的老太醫了。」
廖鑾開始講起了當年的事兒。
「王爺這話,是說倉青當初離開的時候,很缺銀子?」銘玄疑不解。
Advertisement
「看來你當真是什麼都不知道。」廖鑾看著銘玄的表,無奈地搖了搖頭。
「這些事都是柳兒告訴我的,既然倉青沒有告訴你,看來是他自己不想了,本王也不是在背後嚼舌的人。他不想說,就罷了。」
廖鑾繼續說著。
「只不過是想告訴你,倉青一直沒有忘記自己的初心。」
「可王爺說了這麼多,還是沒有說到,王爺的私心,到底是什麼。」銘玄著眉頭,說道。
廖鑾看著銘玄,笑了笑。
說了這麼多,是因為他必須讓銘玄卸下些防備,自己才好意思說出口啊。
「百毒宴的獎品,銘玄醫師可是有信心拿到?」他開口。
銘玄笑了笑,到底還是帶著目的來的。
「有!老夫此行,便是為了那東西。」他想也不想地就回答道。
那東西?
廖鑾不著痕跡地挑了挑眉,聽銘玄這語氣,似乎是知道,百毒宴的最終獎品是什麼了?
「哪東西?」他還是決定試探一下,便明知故問道。
「一整套茶罐。」銘玄說道。
他向來不在意百毒宴的那些規矩。
聞言,廖鑾卻是皺起了眉頭,看來自己的猜想倒是沒錯,這靖王為了拖住自己,私自將獎品更換了。
「那茶罐,可是有什麼來頭?」廖鑾不聲,繼續問著。
「來頭大了,不過是現在不方便與王爺再講了,本來這獎品,似乎就是百毒宴的大忌。」銘玄說道。
廖鑾將雙手支撐在手,撐了個舒服的姿勢,懶洋洋地開口:「既然是大忌,銘玄醫師又是如何知道的?」
「我自有我的辦法,百毒宴要是沒有我,也到不了今天這地步。」銘玄滿不在乎地說道。
「若是本王告訴你,今年百毒宴的獎品,其實是個朝帶,本不是你說的什麼茶罐呢?」廖鑾滿臉的戲謔。
Advertisement
「朝帶?不可能。」銘玄一口否認。
可是下一秒,他心裏也有些不安了。
廖鑾沒必要拿這件事兒騙自己呀,這明天就會公佈答案的事兒……
「要是你不相信,明日看看便是。」廖鑾輕聲說道。
銘玄不說話了。
他也知道那朝帶的來歷和效用,可即便是這樣,自己也對那朝帶一點兒也不興趣,倘若獎品真是朝帶,還不如昨個順水人,把東西送給王爺。
畢竟這王爺的樣子很明顯,就是為了那朝帶來的。
不過,要真如這北環的王爺所說,那今年的百花宴,靖王可就算是老老實實地,把自己給得罪了,這筆賬,銘玄是必算不可的。
「不必等到明日,今晚我自有方法知道,明日一早,我會告訴王爺答案的。」銘玄說道。
廖鑾點了點頭,看著一臉嚴肅的銘玄,甚是滿意。
「若當真是朝帶,那便歸王爺所有,不興趣的東西,老夫也不奪人所,也正好,藉此還了王爺與王妃的救命之。」銘玄很是直接地說著。
雖然這話聽起來似乎有些不大舒服,但是廖鑾心裏,還是對即將能夠看到的結果到興。
翌日一早。
「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銘玄淺淺地笑著,看上去初見面,了很多的敵意。
「看不出來,銘玄醫師還在意這些。」
林醉柳也大大方方地回道。
看來,是廖鑾昨晚上跟銘玄的談話起了作用。
而且,看銘玄今日的反應,自己似乎是,不用厚著臉皮去跟銘玄要朝帶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349 章

逆天廢柴:邪君的第一寵妃
「禽獸……」她扶著腰,咬牙切齒。「你怎知本君真身?」他擦擦嘴,笑的邪惡如魔。一朝重生,她以為可以踏上一條虐渣殺敵的光明大道,豈料,拜師不利,落入狼口,任她腹黑的出神入化,也逃不過他的手掌心中。終有一日,她忍不可忍:「說好的師徒關係呢?說好的不強娶呢?說好的高冷禁慾呢?你到底是不是那個大陸威震八方不近女色的第一邪君?」他挑眉盯著她看了半響,深沉莫測的道:「你被騙了!」「……」
154.2萬字8.18 48509 -
完結478 章

狂傲世子妃
一、特工穿越,一夢醒來是個完全陌生的地方,絕境之中,各種記憶跌撞而至,雖然危機重重,但步步爲營,看一代特工如何在宮廷中勇鬥百官滅強敵,譜寫自己的傳奇。我狂、我傲,但有人寵著,有人愛,我靠我自己,爲什麼不能。
84.4萬字8 16623 -
完結264 章

權貴休妻后迎來火葬場
還是公主時眾人眼裡的沈夢綺 皇上、太后:我家小夢綺柔弱不能自理,嫁給攝政王少不得要被欺負了,不行必須派個能打的跟著她。 閨蜜洛九卿:公主她心性單純,孤身一人在攝政王府指不定要受多少委屈,要給她多備點錢財打發下人,那幫人拿了錢,就不好意思在暗地裡給她使絆子了。 通房程星辰:公主明明武力值爆表能夠倒拔垂楊柳,為何偏愛繡花針?難道是在繡沙包,偷偷鍛煉?不行我得盯死她! 攝政王:我家夫人只是表面冷冰冰,私下還是個愛偷吃甜點糖糕的小朋友呢 沈夢綺本人:在越雷池一步,本公主殺了你
53.5萬字8 7963 -
完結77 章

首輔的早死小嬌妻
永安侯離世后,侯府日漸衰敗,紀夫人準備給自己的兩個女兒挑一個貴婿,來扶持侯府。沈暮朝年少有為,極有可能金榜題名,成為朝中新貴,精挑細選,沈暮朝就成了紀家“魚塘”里最適合的一尾。紀夫人打算把小女兒許配給沈暮朝,可陰差陽錯,這門親事落在了紀家大…
29.4萬字8 6103 -
完結227 章

重生盛世醫女
顧重陽怎麼也沒想到自己會回到十歲那年。母親還活著,繼母尚未進門。她不是喪婦長女,更不曾被繼母養歪。有幸重來一次,上一世的悲劇自然是要避免的。既然靠山山倒,靠水..
89.8萬字8 10504 -
完結1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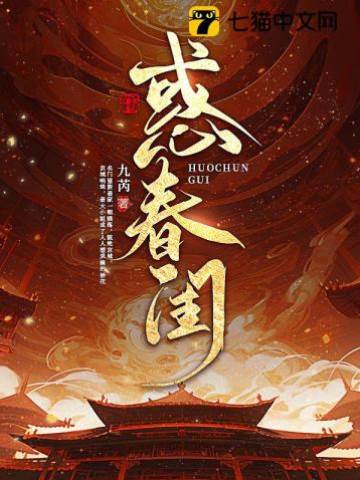
惑春閨
名門望族薑家一朝隕落,貌絕京城,京城明珠,薑大小姐成了人人想采摘的嬌花。麵對四麵楚歌,豺狼虎豹,薑梨滿果斷爬上了昔日未婚夫的馬車。退親的時候沒有想過,他會成為主宰的上位者,她卻淪為了掌中雀。以為他冷心無情是天生,直到看到他可以無條件對別人溫柔寵溺,薑梨滿才明白,他有溫情,隻是不再給她。既然再回去,那何必強求?薑梨滿心灰意冷打算離開,樓棄卻慌了……
31.5萬字8.18 789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