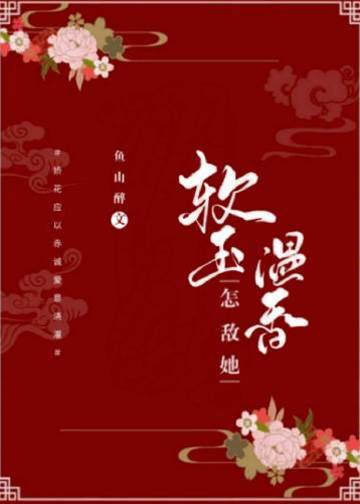《神醫毒妃之踹掉瘋批王爺》 第77章:我不能給你擦眼淚了
王府柴房。
淺溪灰頭土臉地劈著柴,的上還有些傷,那是素素昨個兒半夜來的時候打得,著斧頭,眼底盡是淚花。
昨個兒素素來的時候,還特意支開了其他的人,將關到了一間矮小的屋子里面,拿著藤條了七八下。
如果無冤無仇的話,素素怎麼可能大費周折地過來,就為打這個不起眼的人?
定然是沈容煙指使的,一定是痛恨王妃娘娘,所以陷害王妃娘娘不夠,還要拿自己出氣。
淺溪越想越氣,越想越害怕。
被關在柴房里面都免不了一番痛打,如今王妃娘娘在地牢里面,豈不是...
淺溪生生地將眼淚了回去。
看了一眼天,夕已經快落到了山頭下,淺溪眼底閃過幾分決然。
如今能夠救王妃娘娘的人,只有了!
...
楚樂是被疼醒的,傷口灼燒的發疼,猛地吸了一口冷氣,臉頰痛的不行,不敢張,因為一張,角的傷口就會被扯開。
Advertisement
楚樂慢吞吞地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指。
被沈容煙夾過的地方,已經腫的像一小胡蘿卜。
楚樂眉心擰了幾分,看了一眼門口的侍衛。
看守的只有兩個侍衛,估計是因為這個地方很蔽,不用擔心被外人找到,所以人手才這麼。
楚樂的眸了,估算著要是跑出去,會有幾分勝算。
想了想,楚樂才意識到,的雙手被綁著,又怎麼可能跑出去?
楚樂無力地垂下了頭,默不作聲地忍著傷口帶來的痛楚,那種蝕骨鉆心的覺,無時無刻不在折磨,忍著,咬破了,嘗到了的味道。
那子腥味兒纏在了的嚨間,楚樂連忙咳嗽了幾下,擺了那種味道。
這時候,楚樂才后知后覺地反應過來,已經一天多都沒有吃飯了。
從被關進來,到現在,估計正好是一天。
被沈容煙折磨了那麼久,楚樂的渾都虛了,想,如果面前有一大桌子飯菜的話,可能會吃到撐死。
Advertisement
就在這時,一道急促的腳步聲傳了過來,“我奉王爺之命給王妃娘娘送來一些吃的,開門!”
楚樂子一僵。
的思緒翻涌了起來,一雙冷漠的眸子,漸漸有了幾分溫度和亮,楚樂僵、緩慢地抬起頭來,看見了牢門外的人。
剎那間,心尖上跳躍起了一道星火。
是淺溪!
很快,楚樂的眉心就擰了起來,那道星火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熄滅了下去。
是怎麼過來的?難不...
淺溪張的了飯桶,著頭皮對上了兩位侍衛的眼神,“怎麼?不信?難道要我王爺過來親自跟你們說麼!”
那兩個侍衛看了彼此一眼,顯然是不相信淺溪,“王爺派人過來都會帶一些信。”
淺溪心中一,費了千辛萬苦才跑回了榮樂閣,拿出了丞相給王妃娘娘的那些銀票,花了不的銀子才讓廚房弄了這些飯菜。
Advertisement
本就是假借元夜寒的名義,怎麼可能有信呢?
思及此,淺溪一咬牙,從袖子里面掏出來了一張銀票,“只要能讓我進去給王妃娘娘送一些飯菜,這一萬兩就是你們的了,屆時如果王爺問起來,你們就怪在我上,說我騙了你們,橫豎王爺不會對你們如何。”
一萬兩啊,那可能是他們一輩子都賺不回來的銀子!
他們只是普通的侍衛,并非是暗衛,錢財對他們來說,是必不可的東西,如今一萬兩擺在他們面前,還不需要他們承擔風險,這個,可謂是極大的。
兩個侍衛接過了銀票,打開了牢門,催促著:“趕進去,別被人發現了。”
淺溪松了一口氣。
提著飯桶,進了牢房,一靠近楚樂的周,就聞到了一子濃重的腥味兒。
淺溪頓時大驚,一雙眸子閃爍著淚花,低聲囁嚅道:“王妃娘娘,他們對你做什麼了?”
Advertisement
楚樂渾繃著,越張,腥味兒就越濃,眼看著淺溪要急哭了,楚樂更急,的手指掙扎著,想要為淺溪去眼淚,嗓音沙啞:“你別哭...我不能給你眼淚了,你得忍住。”
楚樂斷斷續續地說著,這句話,拿走了大半的力氣,沈容煙的惡行,已經讓楚樂奄奄一息了。
猜你喜歡
-
完結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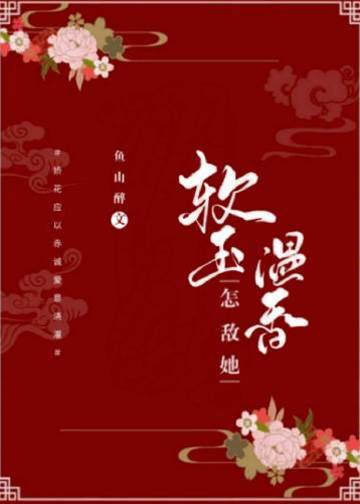
怎敵她軟玉溫香
提起喬沅,上京諸人無不羨慕她的好命。出生鐘鳴鼎食之家,才貌都是拔尖兒,嫁的男人是大霽最有權勢的侯爺,眼見一輩子都要在錦繡窩里打滾。喬沅也是這麼認為的,直到她做了個夢。夢里她被下降頭似的愛上了一個野男人,拋夫棄子,為他洗手作羹湯,結果還被拋棄…
21.9萬字8 10754 -
完結356 章

養丞
童少懸第一次見到家道中落的唐三娘唐見微,是在長公主的賞春雅聚之上。除了見識到她絕世容貌之外,更見識到她巧舌如簧表里不一。童少懸感嘆:“幸好當年唐家退了我的婚,不然的話,現在童家豈不家翻宅亂永無寧日?”沒過多久,天子將唐見微指婚給童少懸。童少懸:“……”唐見微:“知道你對我又煩又怕,咱們不過逢場作戲,各掃門前雪。”童少懸:“正有此意。”三日后,唐見微在童府后門擺攤賣油條。滿腦門問號的童少懸:“我童家
150萬字8 1898 -
完結559 章

一念桃花
八年前,常晚雲在戰亂中被一名白衣少年救下,她望著眼前的少年,俊美,有錢,當場決定我可以; 八年後,常晚雲終於知道了少年的身份。 當朝皇帝的九皇子,裴淵。 重新見面,晚雲作為醫聖唯一的女弟子,來到裴淵身旁為他療傷,阿兄長阿兄短。 裴淵日理萬機,只想將她送走,甚至當起了紅娘。 豈料趕人一時爽,追人火葬場。 晚雲冷笑。 憑本事踹的白月光,為什麼還要吃回去?
95.3萬字8 1050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