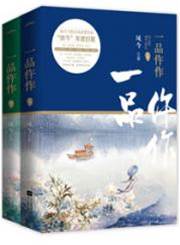《郡主有喜,風光再嫁》 第188章 木牛流馬
這會兒沒有丙烯,沒有油漆。
不過卻是難不倒腦筋的人,蕭四爺他們調制出的料,像丙烯和油漆一樣,有鮮麗的彩,牢固的效果,且還沒有刺鼻難聞的味道。
“堅持三五個月不問題,到時候不那麼鮮亮了,就正好再畫一次,也算練手了。”蕭四爺笑瞇瞇的看著自己和學生們的大作,滿意的點頭。
載著蕭四爺和其學生的漫畫,兩輛分外惹眼的校車,招搖過市,宣傳著學館的啟蒙班。
招收四五歲以上,八九歲以下的孩子。
啟蒙班也分為兩類,一類是還不識字,沒讀過什麼啟蒙書籍的孩子。
還有一類就是已經識得一些字,也會提筆寫幾個字的大些的孩子。
大人們許是不放心將自己的“眼珠子”,就這麼送到學館里去上學。
可小孩子們不住那“豪華”校車的。
紛紛在家撒耍賴,也要到學館去上學。
從宛城來參觀新校的陳曦月,甚至還專門為學館的啟蒙班設計了春夏秋冬,四季的校服。整日呆在煙雨樓中,在姑娘們爭奇斗艷之中,倒是熏陶出了不俗的眼。
設計出的校服,時新又靚麗,小娃們穿起來,俏如小公主。
小郎君們的服,則赫赫威風,略像騎裝的校服,還配了異族的小短靴,更顯的瀟灑倜儻。
這校服自然是先給重午和長康穿了。
兩個孩子,重午威武,長康纖瘦。但這校服量所做,穿在上,格外的神好看。
重午像是個得勝歸來的小將軍。長康也添了幾分英氣。
兩個孩子坐在校車上,在校車沿街飛馳宣傳之時,他們就站在窗邊,朝外頭揮手打招呼。
宛如巡視的大將軍一般。
Advertisement
那小孩子們見了這雕玉琢的小娃娃,更生羨慕。
不人都給蕭玉琢投了拜帖,前來詢問啟蒙館的事宜。
能上啟蒙館的多是貴胄家的孩子。
蕭玉琢自然也不敢大意,“可以先試讀半月,若覺得可行,再做決定也不遲。若覺得不行,回到家中也不耽誤族學里的功課。”
“啟蒙的先生是我家祖父,還有祖父的故,大儒顧先生。”
“每日都由校車接送孩子們,校車的路線是固定的,長安城里有五兵馬司巡邏,學館里也會派出人手專門護送孩子。只需按時送孩子上車,接孩子下車即可。”
……
有了蕭玉琢一番保證,這才陸續有孩子報名啟蒙班。
待啟蒙班開始授課,已經又到了年末了。
重午可不管年末年初,他像是一只被放出籠子的鳥兒一般,晨起再不用娘一請再請,娘剛喚一聲,他就從床榻上躥起來。
他自己興還不夠,還要再把長康也從熱乎的被窩里拽出來,陪他一起撒歡兒似的,穿上校服,蹬上滾了白皮草的小皮靴,匆匆用了飯,就到門口等著校車來接他們。
校車是阿娘提供的,校車上的畫兒是外祖父畫的,學館里大小事務中長能見到姨母的影,授課的先生是他曾外祖父。
小重午在這樣的環境中,免不了就有些囂張。
好似他已自封了孩子王,不服管教的孩子,他都要“教訓”人家一番。
他不是班里最大的孩子,且他們這樣的啟蒙班上,多有在家里說一不二的嫡子長孫。這些個孩子人不大,心氣兒卻是不小。
爭執總是難免發生。
一般都要專人看管著。
但這麼多的孩子,總有眼睛一,就看不住的時候。
Advertisement
沒過幾日,班里就有個孩子被重午給打了。
重午自己也掛了彩,但是他回家沒敢說。
那孩子的家人尋到蕭家,找到蕭玉琢的時候,才知道這件事。
人孩子的母親以往同蕭玉琢也算是有些,話說的還算委婉,“孩子們之間,有些口角,磕磕都是難免的。我們也不是為著這事兒就來尋孩子的不是的。兩個人有口角,總不會是一個人的錯。”
蕭玉琢連連點頭,“說的是。”
“但是聽家中的幾個孩子說,蕭家的這位小郎君,總是自封為王的,還要指揮這個,調遣那個……這可不太好吧?”那孩子的母親方氏,別有深意的看了蕭玉琢以眼,笑著說道。
蕭玉琢臉面一僵,繼而又笑起來,“都是孩子戲言,他那里知道什麼是王,能調遣指揮個什麼勁兒?不過倒也是我疏于管教了。”
“咱們在閨中的時候,就是手帕了,這話若是換做了旁人,我也不能專門來人家家里提醒。”方氏笑道。
方氏的公公是朝中史,雖說孩子言無忌的,可他若是抓著家人管教不嚴來做文章,在圣上面前參奏一番,對蕭玉琢來說,也是一大麻煩。
蕭玉琢連忙謝過方氏,“是你記著我們的閨中誼,這才專程來告訴我,我心中激,定會好好教育這孩子。你且放心,日后學館里先生仆從們的看護,也會更加的嚴謹,斷然不會再出現今日這事兒了。”
方氏笑著點了點頭。
蕭玉琢又人送了五芳齋新出的點心,蕭四爺新作的漫畫,和一些南方送過來的稀罕水果,人給送到了方氏的車上。
方氏又跟聊了會兒閑話,這才滿意的走了。
蕭玉琢送走了方氏,把重午從長公主面前提溜回來的時候,臉嚴謹的重午都有些怕了。
Advertisement
“阿娘……”重午低著頭,攥著兩只糯白的小手。
蕭玉琢見他這會兒這乖巧的樣子,又氣又無奈。
“過來,到阿娘邊來。”蕭玉琢招了招手。
重午磨磨蹭蹭的不敢。
“阿娘不罵你,只想問你幾句話,你過來吧。”蕭玉琢自問從未打過重午,便是有時嚴厲些,也注意著分寸,怎至于重午這般怕?
小重午往前走了幾步,湊到蕭玉琢面前。
蕭玉琢手拉著他,在自己邊坐下,“阿娘聽說,你今日和同窗發生了口角?”
小重午悶悶的嗯了一聲。
“他阿娘說,他上青了幾塊。你呢?可有傷?”蕭玉琢本想責罰他的,見他小心翼翼的,不由放緩了語氣。
小重午癟癟,“男子漢大丈夫,便是些小傷又有何妨?”
蕭玉琢一噎,這話,怎麼那麼像景延年的語氣?真不愧是是他的兒子。
“爹爹教我防的招數了,不過是我技藝不,才他到了我。”小重午梗著脖子說道。
蕭玉琢無語翻了個白眼,景延年教兒子功夫,是不是也教的太早了?
“阿娘,你可別告訴爹爹啊,他知道了定要笑話我的!”
“他笑話你什麼?”蕭玉琢瞪眼。
“我跟他說我很厲害的,結果卻在劉家那孩子面前也吃了虧,他能不笑話我麼?”小重午眼睛里閃爍著的是稚的自尊。
蕭玉琢嘆了口氣,景延年給兒子的都是些什麼東西?
這麼小的年紀,他打架?還不能吃虧?
“爹爹說,他小時候從來不會被人打趴下的,比他大的孩子都怕他!”小重午鼓道。
“你爹那個時候,跟你現在的況可不一樣。你爹他是被人欺負,不得不反抗來保護自己,而你呢?你曾外祖父是國相,外祖母是長公主,爹爹是吳王,娘親起碼也是個郡主!你不招惹別人,別人斷然不敢欺負你!”蕭玉琢扶額道。
Advertisement
“那若是有人欺負我呢?”小重午瞪著一雙眼睛。
“有人欺負你,也得想辦法他們不敢欺負你才是!手腳,都是野蠻人!”蕭玉琢道。
小重午迷了,“爹爹是野蠻人嗎?”
蕭玉琢很想點頭說,本來就是。
可考慮到應該維護景延年在兒子心中的形象,只好道,“那不一樣,你爹是武將出,本就應該為國為君為守護天下百姓而拳腳。他不會為了欺負旁人,為了仗勢欺人而拳腳。知道麼?”
重午點了點頭,“兒子明白了。”
“那今日的事,你反思一下自己的過錯,寫個檢討給曾外祖父過目。”蕭玉琢說道。
重午苦了臉,“不會寫的字怎麼辦?”
“不會可以問啊?”蕭玉琢看他,“可不能懶。”
“曾外祖父一定會笑話我的字,寫的像爬……曾外祖父的字多漂亮啊!”小重午哀嚎。
蕭玉琢瞇眼笑看著兒子。
這麼大點兒的小屁孩兒,自尊心還強。
不過沒有心,“這是給你個機會,如果再讓我知道,你在學校里仗勢欺負你的同窗們,你就不用去學館里上學了,好好在家呆著吧!”
小重午最喜歡外頭彩紛呈的世界,最討厭被拘在家里頭。
聽聞這話,他立時就老實答應,自己會好好反思,好好寫檢討。
蕭玉琢以為這次的事,肯定會給重午一個教訓,他長長記。
還專門去見了景延年,警告他別誤導孩子,小小的孩子,教他什麼拳腳?
還炫耀他小時候打架厲害?有他這麼教育兒子的麼?
景延年沉默了好一陣子,別的都答應,偏偏不他教兒子拳腳這一條,他說什麼都不肯答應,“習武能夠強健是其一,其二,你怎麼知道習武,將來不能在關鍵時候保他的命呢?你是一子,尚且知道應當自強,他一個男兒,怎能不自強呢?”
瞧瞧,又帶了別歧視吧?
這會兒他們說的是孩子的問題,提什麼男呢?
蕭玉琢和他說不通,只覺的景延年這人是太固執。
沒曾想,真他給說中了。
還未到將來,年下學館里就要放假的時候,卻是出了一件大事兒。
若不是重午年就開始習武,腳快,跑得快……這會兒的后果還真是不堪設想呢!
蕭玉琢想起來都覺得后怕。
這事兒發生在臘八的前一天。
蕭玉琢正在看梁生送來的賬目。
晴空萬里的,臘月雖冷,天空卻湛藍而晴好,萬里無云的,宛若秋日明朗高闊的天空一般。
蕭玉琢信手翻了一頁書。
忽聽“轟隆——”一聲響。
好似天邊打了個響雷一般。
詫異的放下賬冊,舉目看了看窗外,“怎麼像是一聲春雷啊?”
“娘子,這會兒不會有春雷的,天氣這般晴朗,且還是臘月呢!”梅香說道。
“那剛才一聲響,你沒聽見麼?”蕭玉琢狐疑。
梅香皺眉點點頭,“婢子聽見了呀,也不知那是什麼聲響?”
蕭玉琢歪了歪腦袋,這聲音倒像是穿越前那會兒,老家崩山開礦的聲音呢。
皺眉,約覺得心下難安,但也并未在意。
又看了一本賬冊,才見竹香急匆匆的從外頭回來。
進的屋的時候,只見臉都是煞白的。
“娘子,學館里出事了!學生的寢房走水了!小郎君也傷了!”竹香息說道。
蕭玉琢手中的賬冊,咣的就砸在了地上。
“重午傷了?!”
轉就向外奔去,心里頭焦灼擔憂,如被人拿油鍋煎烤著一般。
沒等人套車,直接翻上馬,打著馬就往學館沖去。
蕭玉琢趕到學館的時候,寢房的火尚未被撲滅呢。
不過火勢倒是被控制住了。
只是那寢房,和連接在一起的三四間房子都毀了。
已經撲滅火的地方,看著也是焦黑一片。
房子的瓦片木片,飛濺的到都是。
這可不像是單單起火那麼簡單,更像是發生了一場炸!
蕭玉琢飛下馬,抓過學館里的人就問,“重午呢?重午在哪兒?”
這會兒急的,眼睛里滿是紅紅的。
“阿娘,我在這兒呢。”重午怯懦的聲音從后傳來。
蕭玉琢此時聽聞,直覺猶如天籟。
立時回過頭,看見重午那一剎那,眼淚就像洶涌的洪水一般,決堤而出。
“重午,阿娘的小重午!”
蹲把小重午給抱在懷里,抱得地。
“不是說你傷了麼?傷著哪兒了?傷得怎樣?香呢?快香來看看!”蕭玉琢一連說道。
小重午臉煞白煞白的。
他整日的有長公主寵著縱著,鮮有這般害怕的時候。
蕭玉琢以為他傷得很重,在他上,卻也沒有看到什麼外傷的痕跡。
“傷著哪兒了?怎的不說話?”蕭玉琢急道。
小重午低著頭,用極小的聲音說道,“我跑的太快,崴了腳了。”
“嗯?”蕭玉琢看了看他的腳。
果然有一只腳腕微微的腫了起來。
心疼不已,卻還是松了口氣,“沒事,別怕啊,香的醫可好了,肯定能治好你的腳的。”
“阿娘,我錯了……你別趕我回家……”小重午卻癟癟,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蕭玉琢被他哭得懵懂,“崴了腳嘛,我不會趕你回家的呀?”
重午卻是搖著頭,只是哭。
他撲在蕭玉琢懷里,忽的小小的子都抖起來。
蕭玉琢又心疼又著急,“究竟是怎麼回事,你告訴阿娘?”
猜你喜歡
-
完結46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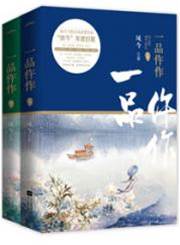
一品仵作
這是一個法醫學家兼微表情心理學家,在為父報仇、尋找真兇的道路上,最後找到了真愛的故事。聽起來有點簡單,但其實有點曲折。好吧,還是看正經簡介吧開棺驗屍、查內情、慰亡靈、讓死人開口說話——這是仵作該乾的事。暮青乾了。西北從軍、救主帥、殺敵首、翻朝堂、覆盛京、傾權謀——這不是仵作該乾的事。暮青也乾了。但是,她覺得,這些都不是她想乾的。她這輩子最想乾的事,是剖活人。剖一剖世間欺她負她的小人。剖一剖嘴皮子一張就想翻覆公理的貴人大佬。剖一剖禦座之上的千麵帝君,步惜歡。可是,她剖得了死人,剖得了活人,剖得了這鐵血王朝,卻如何剖解此生真情?待山河裂,烽煙起,她一襲烈衣捲入千軍萬馬,“我求一生完整的感情,不欺,不棄。欺我者,我永棄!”風雷動,四海驚,天下傾,屬於她一生的傳奇,此刻,開啟——【懸疑版簡介】大興元隆年間,帝君昏聵,五胡犯邊。暮青南下汴河,尋殺父元兇,選行宮男妃,刺大興帝君!男妃行事成迷,帝君身手奇詭,殺父元兇究竟何人?行軍途中內奸暗藏,大漠地宮機關深詭,議和使節半路身亡,盛京驚現真假勒丹王……是誰以天下為局譜一手亂世的棋,是誰以刀刃為弦奏一首盛世的曲?自邊關至盛京,自民間至朝堂,且看一出撲朔迷離的大戲,且聽一曲女仵作的盛世傳奇。
203萬字8 27667 -
完結352 章
毒妃太撩人:王爺休書請拿好
姜姮被親手養大的妹妹弄死了,但是禍害遺千年,她又活了,一睜眼,成了敵國王妃,夫君是以前的死對頭,腿殘了還是被她給廢的。原主為太子自殺,死對頭嫌她丟臉,將她遣還娘家,還送來了休書一封!這誰能忍?于是她還了他一封休書。你休我我休你,扯平了咱繼續相看厭吧。后來,舊賬翻出來了。“要命一條要腿兩條,想要報仇拿去就是,我就不帶怕的!”“命和腿都不要,把你自己賠給我就好了。”啥玩意兒?這種事情還能以身相抵?
66.1萬字8 20989 -
完結579 章

穿越當夜我把王爺踹下榻
震驚!母胎單身20年的她,剛穿越竟然遇到美男偷襲!鳳吟晚一個回旋踢,直接把罪魁禍首踹下榻。敢吃老娘豆腐,斷子絕孫吧你!輪番而來的:渣男、綠茶、小白蓮。她欣然應戰,虐渣、搞事、賺錢錢,只盼著能跟某男一拍兩散。眼見她臉蛋越來越美,腰包越來越鼓,身板越挺越硬,某男盯著她日漸圓潤的小腹,面上陰晴不定。這事不小,和綠色有關!鳳吟晚:“嚯,大冤種竟是你自己。”
88.7萬字8 17446 -
完結546 章
攝政王你又被挖墻角了
【1v1+醫妃+養成+女強爽文】 他是權傾朝野的攝政王,她是葉家頭腦蠢笨的傻女,更是醫毒雙絕的鬼醫聖手。 渣爹奪盡她的家產,後娘欺她似狗,庶姐們欺淩辱駡,渣男悔婚利用,無妨,她一手醫毒術,打遍天下無敵手。 白蓮花陷害,一把毒藥變傻子。 後娘下毒,叫她毀容。 渣男踩著她上位,一根銀針叫他斷子絕孫。 人後撕天撕地撕空氣,人前可憐兮兮小白兔:“皇叔,我手手疼......” 男人眸光乍冷:“誰欺負了本王的愛妃? “ 被打得痛哭流涕的眾人:攝政王,您老人家可睜睜眼吧!!
50.8萬字8 3910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