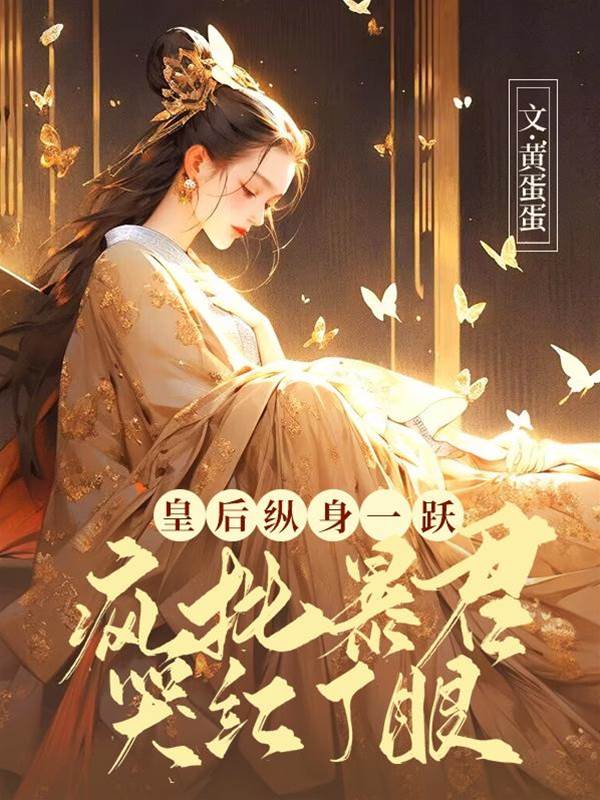《東宮美人(荔簫)》 第 38 章 第 38 章
宦躬著,一邊挑燈給太子引路一邊回話。他知道楚奉儀合太子的心意,著意繪聲繪地把楚奉儀那些話都重復明白了,最后收尾道:“所以,徐良娣、黃寶林和羅寶林就都走了,只剩下云寶林、廖奉儀和楚奉儀用完了膳,還人唱了兩支曲兒,才回去歇著。”
沈晰忍笑忍得很艱難:“知道了。”說罷隨手賞了這宦一錠銀子,徑直往綠意閣行去。
宜春殿里,太子妃趙氏回東宮后小睡了一覺,醒來也問了問后宅的事。聽聞家宴不歡而散,秀眉皺得的:“這楚氏真是沒規沒矩。大過年的鬧這個樣子,一點分寸也不知道。”
這事是匪夷所思了些,白蕊方才回話時就知太子妃要生氣,眼下連眼皮都不敢抬:“楚奉儀確是脾氣沖了些。”
“目無法紀!”趙瑾月神肅然,不快地想了想,吩咐白蕊說:“著人去綠意閣傳個話,讓楚氏明天一早來宜春殿,給我把事解釋個清楚。”
想,這個正妻就在這兒擱著呢,底下的妾室豈有鬧得這樣難看的道理?
如若傳出去,讓的臉面往哪兒擱?外人都要笑話的!
.
綠意閣里,楚怡原本都躺在床上快睡著了,沒想到沈晰翻上床就開始笑,生生把的睡意給笑沒了。
“笑什麼啊!”睜開眼來瞪他,他趴在旁邊笑得肩頭直搐。
莫名其妙!
被攪擾了睡眠的楚怡心里不爽,氣哼哼地不理他了,翻過面朝著墻壁,抱住被角要繼續睡。
他卻又賤兮兮地湊過來,拍著的肩頭說:“真毒,一桌六個人讓你懟跑了三個?”
楚怡瞬間清醒,一下子彈坐起,臉都紅了:“不是那麼回事!”
Advertisement
懇切地著太子說:“是們先惹我的!”
“我知道我知道。”他攬著躺回去,還給掖了掖被子,幔帳里稍稍安靜了一會兒,他又沒忍住撲哧了一聲。
太可樂了,本忍不住啊!
楚怡被他笑得無地自容,往下拱了拱,將臉蒙進了被子里,他又揭開被子把了出來。
然后他親了親的額頭:“不過我覺得黃寶林說得也對。”
楚怡:“?”
詫異地看看他:“殿下是說……云詩沒為臣妾說話不對?臣妾覺得不是那樣的,云詩就是膽子小而已,見了殿下就恨不得找個躲起來,哪敢跟殿下提要求啊?”
沈晰笑地聽著說完,道:“不是那句。”
楚怡:“?”
“是說你的位份也該晉晉了,這大半年也就你總侍奉在側,不能讓你白干活不是?”
楚怡又一次:“?”
接著凌道:“不不不不不……別了吧!臣妾當這奉儀好,逍遙自在!”
“給你晉個位妨礙你逍遙自在嗎?”沈晰不解地鎖起眉頭打量,促狹道,“就憑你這張,也沒人能妨礙你自在吧。”
“……不是,不是那麼回事兒。”楚怡絞盡腦,迅速想了一套比較好聽的措辭,“臣妾就……就覺得位份不重要!殿下您看咱現在兩相悅是不?那虛位有什麼要的,好好過日子不就行了嘛!”
這話可太好聽了。
好聽得都不像說的了。
沈晰于是饒有興味地看著:“你說實話行嗎?”
楚怡:“……”
回被子里:“實話是……”
沈晰淡笑著凝視著的臉。
“臣妾……”
沈晰目不轉睛。
楚怡閉眼,將心一橫:“臣妾覺得自己到現在都沒侍寢過還晉位很不合適!”
Advertisement
沈晰噗地一聲,大笑剛涌到嚨,余瞥見有人進屋便下意識地回過頭,定睛一看,是個宜春殿的宦。
太子便坐起了:“怎麼了?”
那宦單膝跪地:“殿下安。太子妃殿下聽聞了今晚家宴的事,傳奉儀娘子明日一早去宜春殿解釋一二。”
楚怡聞言撐坐起:“這事分明是……”
太子抬手止住了他的話。
他看了看那宦,淡聲道:“你去回話,就說是黃氏出言不遜在先。”
宦不敢多言,一叩首就要走,沈晰又添了句:“記得說清楚,是底下人稟話說的。”
他不能讓太子妃覺得是楚怡跟他說了什麼。否則就太子妃那個想東想西的脾氣,絕不會相信他是早就聽了這事覺得楚怡沒錯而后才到的綠意閣,只會覺得他是為了袒護楚怡而駁的面子。
沈晰這般想著,頗有些郁結于心地暗自咂了咂,待得那宦退出去,才又扭頭看向楚怡:“這下晉位是得放放了。”
說罷便見楚怡眉眼一彎:“可以的!”
沒心沒肺。
沈晰瞇眼,躺回去攬住:“不過你若忐忑于自己尚未侍寢,孤給你個機會啊。”
“……”楚怡安靜得連呼吸聲都沒了。
沈晰一臉的好笑:“那你覺得怎麼著合適?你看,你我現在也算起來了吧,你難不要一直這麼……你懂,然后守著奉儀的位子守幾十年?”
當然不是。
楚怡心復雜地在被子里扭了一下。
其實想說,我想試著努力斗斗,等你什麼時候把你完全收囊中、讓你對我一心一意了,我們再滾床單。
但理智告訴,這確實太難了。
雖然太子的的確確已經有大半年沒過別人,可這是因為后宅的人還、別人都不合他的意,并不是為了。
Advertisement
以后注定還會有更多妃妾進后宅的,等他登基為帝,這個數量會更多,就是人數過百都不稀奇。
期待的事像是一座空中樓閣,好地懸浮在的夢境里,但因為沒有基,注定無法在現實中構。
能做的其實只有跟現實達和解,告訴自己既然沒有空中樓閣,那在宮里有一致華麗的住也不錯。
不然能怎麼樣呢?又不是沒幻想過離開他,可他明明白白地說了讓死了那條心,難道還能自己挖地道出去,然后再游過護城河嗎?
完全不現實好吧。
楚怡于是理了理心緒,弱弱道:“殿下讓臣妾準備準備。”
沈晰點點頭,沒再多說這件事:“對了,父皇讓我過年好好歇一歇。初三之前都要在宮宴上,之后你想四走走不想?我帶你一道去。”
能出去玩?
楚怡眼睛一亮,旋即又黯了下來:“臣妾初四之前不一定能準備好……”
“……”沈晰窘迫地盯了半天,“我也沒那麼急好嗎?”
楚怡:“……”
沈晰:“……”
剎那間,兩個人各自翻,一個朝里一個朝外地背對背蒙住被子睡下了。
尷尬,床上的事兒這麼拿出來聊真尷尬!
楚怡想好了,自己做好準備就得趕推倒他,不能再給他這麼問的機會!再問幾回,怕是連跟他聊天都要覺得別扭了!
.
宜春殿里,趙瑾月聽那宦回稟完正事倒沒覺得有什麼不妥,不滿意歸不滿意,可既然連下人都覺得不是楚奉儀的錯,那這事不提便也不提了。
但接下來,那宦說出的另一件事令猛地涼氣倒吸:“你說什麼?!”
“是,下奴聽得真真兒的。”宦跪地叩首,“先前大約是在說給楚奉儀晉封的事,而后下奴聽到楚奉儀親口說,覺著自己都還沒侍寢過,再行晉封不合適。”
Advertisement
趙瑾月僵坐在了那里,半晌都沒說出一句話。
知道楚氏得寵,但沒想到是這樣的得寵。
一強烈的怒火在中燃燒起來,一個聲音在心里喊:憑什麼!
楚氏憑什麼能得到這樣的殊榮!父親是罪臣,自己當過宮奴。除卻一張好看的臉外,一無是。
何德何能,讓太子這樣待!
而太子,已經很久沒有留宿過宜春殿了。
最初是因為這個太子妃有孕,薦給他的妃妾又不合他的意。可后來,生完了孩子、出了月子,他也再沒有宿在宜春殿過。
曾也生出過淡淡的嫉妒,覺得楚氏這樣纏著太子讓獨守空房。但現下,聽聞楚氏連侍寢都沒有過,又覺得更加怒不可遏。
憑什麼,究竟憑什麼!
趙瑾月翻來覆去地想著這句話。
是沒在東宮后宅里立好規矩,還是楚氏太過狐?
久久得不到答案,最后也只能蹙著黛眉,朝那宦擺了擺手:“知道了,你退下吧。”
.
綠意閣里,沈晰在天尚黑時就起了床。年初一又要忙一整日,單是早上的元日大朝會就不能怠慢。
他沒想醒楚怡,但洗著臉一有靜楚怡就醒了,邊眼睛邊打哈欠地從床上爬起來。
沈晰臉上還掛著水珠,側頭跟說:“你睡你的。”
還真就咣嘰倒回去了,他邊轉頭臉邊埋在帕子里笑。
然后聽到背后懶懶地說:“這麼早就出去,也沒空用膳吧?不嗎?”
“啊。”沈晰惆悵嘆氣,“但能怎麼辦,朝中之事又不能由著我不去。你睡吧,晌午我若得空就回來跟你一道用膳。”
楚怡邊醒神邊想了想:“殿下想喝點昨天晚上的湯嗎?”
“……”滿屋的宮人都斜著眼瞧。
楚怡重新坐起來:“昨天宵夜有道牛湯可好了,但我就喝了那麼一小碗,別的要麼是今兒個賞給宮人喝要麼就倒了。現下這麼冷,放一夜也不會壞,讓他們煮開了再下點面,殿下吃幾口再走唄?”
青玉立在榻邊,恨不得塊帕子把的堵上。
讓太子喝昨天的剩湯,聽都沒聽說過!
但楚怡真沒覺得這有什麼不行。就是在二十一世紀,質資源那麼富的年代,大家還不是經常把當天沒吃完的菜收一收擱冰箱,第二天熱熱再吃嗎?
古代本東西就,吃口剩的咋的了?寒冬臘月膳房里灶火一封,溫度估計比冰箱冷藏室還低。
再說了,太子不是嗎!大冬天著肚子在太和殿外站一上午,多啊!
都在萬人之上的位子了,為什麼要這種沒必要的委屈?
沈晰剛聽那麼問的時候,下意識地皺了皺眉。但聽又是牛湯又是煮面的,沒骨氣地了。
“真會過日子。”他嗤笑著招手來張濟才:“別讓旁人知道,讓膳房熱湯去。”
吩咐完之后他覺得吧……這招是不錯,又省事又實用,只不過讓外人聽了確實不太好,尤其容易給惹事。
他便又向張濟才道:“給綠意閣添個小廚房吧,人手你親自挑。”
“是,下奴知道了。”張濟才低眉順眼地應下。
院子里有自己的小廚房,起碼得是良娣的位子才行,楚怡離良娣還差著兩級呢。
但東宮是太子的東宮,太子說行就行,真有人問下來,回一句是太子想自己用膳方便合口一些,也就得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183 章

貴妃每天只想當咸魚
蕭兮兮穿越回古代,成了太子的小老婆之一。 本應該是宮斗的開始,可她只想當咸魚。 爭寵?不存在的! 咸魚才是生存之道,混吃等死才是人生真諦! 可偏偏, 高冷太子就愛她這一款。 …… 蕭父:閨女,你要爭氣啊,咱家可就指望你攀龍附鳳了! 蕭兮兮:不,我只是一條咸魚 宮女:小主,您要爭氣啊,一定要打敗那些綠茶婊成為太子妃! 蕭兮兮:不,我只是一條咸魚 太子:愛妃,你要爭氣啊,孤就指望你傳宗接代了! 蕭兮兮:不,我只是一條咸魚 太子:無妨,咸魚我也可以。 …… (1V1寵文,雙潔,超甜!)
191.1萬字9.48 5393384 -
完結563 章

丞相府的小娘子
沈梨穿越了,穿到一窮二白,剛死了老爹的沈家。上有瞎眼老母,下有三歲幼兒,沈梨成了家里唯一的頂梁柱。她擼起袖子,擺攤種菜,教書育人,不僅日子越過越紅火,就連桃花也越來越多,甚至有人上趕著給孩子做后爹。某男人怒了!向來清冷禁欲的他撒著嬌粘上去:“娘子,我才是你的夫君~”沈梨:“不,你不是,別瞎說!”某人眼神幽怨:“可是,你這個兒子,好像是我的種。”沈梨糾結:孩子親爹找上門來了,可是孩子已經給自己找好后爹了怎麼辦?
87.5萬字8 21269 -
完結1427 章

娘娘是個嬌氣包,得寵著!
現代牛逼轟轟的神棍大佬林蘇蘇,一覺醒來發現自己成了個棄妃,還是有心疾那種,嬌氣得風吹就倒。爭寵?不存在的,鹹魚保命才是生存之道!可偏偏,身邊助攻不斷!太后:趁著皇帝神志不清,快快侍寢,懷上龍子,你就是皇后!林父:皇上受傷,機會難得,閨女快上,侍疾有功,你就是皇后!只有宮妃們生怕她林蘇蘇一朝得寵。於是!今日宴席,皇上微熏,絕不能讓林蘇蘇去送醒酒湯!遂,一眾妃嬪齊心協力,把林蘇蘇困在了冷宮。可誰來告訴她! 冷宮那個眼尾泛紅的男人是誰啊!到底是哪個不長眼的,又把皇帝送到了她眼前啊!!
128.6萬字8 80306 -
完結3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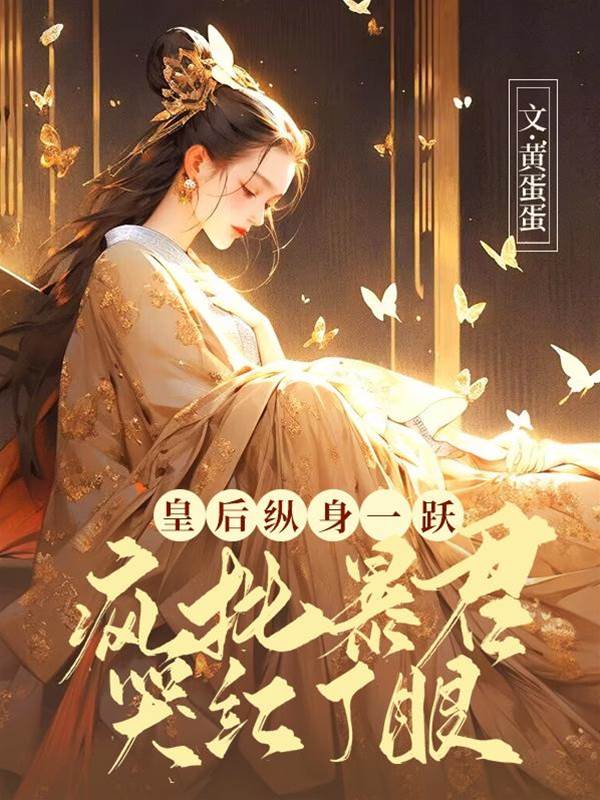
皇後縱身一躍,瘋批暴君哭紅了眼
【1v1,雙潔 宮鬥 爽文 追妻火葬場,女主人間清醒,所有人的白月光】孟棠是個溫婉大方的皇後,不爭不搶,一朵屹立在後宮的真白蓮,所有人都這麼覺得,暴君也這麼覺得。他納妃,她笑著恭喜並安排新妃侍寢。他送來補藥,她明知是避子藥卻乖順服下。他舊疾發作頭痛難忍,她用自己心頭血為引為他止痛。他問她:“你怎麼這麼好。”她麵上溫婉:“能為陛下分憂是臣妾榮幸。”直到叛軍攻城,她在城樓縱身一躍,以身殉城,平定叛亂。*刷滿暴君好感,孟棠死遁成功,功成身退。暴君抱著她的屍體,跪在地上哭紅了眼:“梓童,我錯了,你回來好不好?”孟棠看見這一幕,內心毫無波動,“虐嗎?我演的,真當世界上有那種無私奉獻不求回報的真白蓮啊。”
53.4萬字8.18 4176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