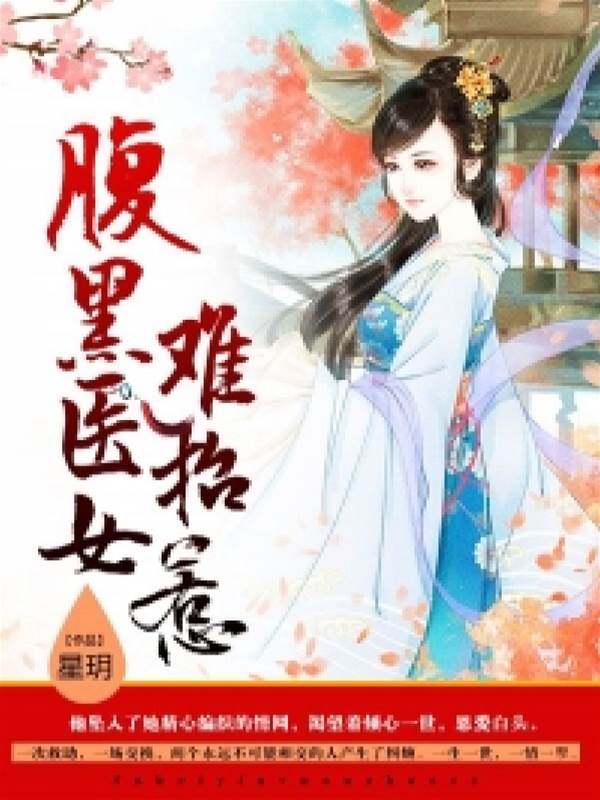《做太子侍寢的她逃了》 第21章
見眼下正好有些閑暇工作,了刑春和桐桐到自己廊下來,把學的字練一練。
程玉酌讓刑春找了黑炭,看著兩人在地上寫。
靜靜跳來跳去,程玉酌把它抱在臺階上,讓它老實看著。
刑春確實有點像說的那樣,記不如桐桐。
寫了兩個字,就寫不出來了,很不好意思了,連道自己不行。
程玉酌連忙安,“有的人讀書識字快,有的人畫畫做詩快,這有什麽?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連聲安著,刑春又繼續寫了起來,在旁指點,刑春終於寫得像樣多了。
刑春額頭上出了汗,了額頭,問程玉酌。
“姑姑在宮裏是,自然要識字,可我們這些尋常婦人,認字也沒什麽大用。”
程玉酌笑說,並非因為是才要識字,而是因為識了字,才能做上。
“讀書識字是本事,多懂一些,到了外麵行走,也不會隨便被別人欺負。”
程玉酌說起了自己小時候。
“我爹娘還在那會兒,我同妹妹、弟弟都是同一年歲啟蒙的,雖然有一說法,說子無才便是德,可是本事是長在自己上的,用的人還是你自己。”
刑春連連點頭,不由問程玉酌。
“姑姑也是讀書人家出,怎麽進宮做了宮人?”
本朝的宮人大多是尋常良家子,富裕些的人家,可不舍得兒進宮為奴為婢。
程玉酌輕歎一聲,“時運不濟,家父被貶西南邊陲,病逝在了上任路上,母親也沒多久便去世了,我那舅父賣了我弟妹,讓我頂了他的兒進宮。”
刑春一聽就來了火氣,“怎麽還有這樣的舅父?!”
程玉酌搖搖頭沒有多言。
刑春見不言,替抱屈,半晌又問。
“姑姑本是家,落到這般,可怨恨?”
Advertisement
程玉酌笑笑,“不怨是不可能,但怨了又有何用?好好活下去才是要的。”
似是不想多言,了刑春和桐桐一起喝茶歇一歇。
趙凜在窗下看書,聽著窗外傳來的聲音,書頁被風吹翻了幾頁,也沒在意。
“彭。”
彭立刻走了過來。
趙凜看著箬竹隙裏影影綽綽的程玉酌三人,問他。
“程玉酌父親被貶所為何事?”
“回爺,十三年前,程司珍之父任揚州儀真縣知縣,因治下一人寫反詩而被牽連,貶西南,病逝路上。”
寫反詩的人並不是程玉酌的父親,他隻不過是因父母的份被牽連。
趙凜什麽都沒說,合起書,站了起來。
箬竹那邊,程玉酌搬出了的紅泥小火爐,招呼著刑春和桐桐一起吃茶。
“是黑虎泉的水,咱們嚐嚐鮮。”
果然如所言,沒有帶著怨氣活著。
趙凜卻想到了他找了五年的那人。
程玉酌與的子,倒也有幾分相像。
不知道許多年過去了,是否也像程玉酌一般活得通,拋去了許多迷惘。
*
歸寧侯府,滿園春花爭奇鬥豔。
歸寧侯老夫人老夏氏看著滿院子的客人,尤其特特看了一眼在貴婦人中遊刃有餘的紅子,轉頭問韓平宇。
見眼下正好有些閑暇工作,了刑春和桐桐到自己廊下來,把學的字練一練。
程玉酌讓刑春找了黑炭,看著兩人在地上寫。
靜靜跳來跳去,程玉酌把它抱在臺階上,讓它老實看著。
刑春確實有點像說的那樣,記不如桐桐。
寫了兩個字,就寫不出來了,很不好意思了,連道自己不行。
程玉酌連忙安,“有的人讀書識字快,有的人畫畫做詩快,這有什麽?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連聲安著,刑春又繼續寫了起來,在旁指點,刑春終於寫得像樣多了。
Advertisement
刑春額頭上出了汗,了額頭,問程玉酌。
“姑姑在宮裏是,自然要識字,可我們這些尋常婦人,認字也沒什麽大用。”
程玉酌笑說,並非因為是才要識字,而是因為識了字,才能做上。
“讀書識字是本事,多懂一些,到了外麵行走,也不會隨便被別人欺負。”
程玉酌說起了自己小時候。
“我爹娘還在那會兒,我同妹妹、弟弟都是同一年歲啟蒙的,雖然有一說法,說子無才便是德,可是本事是長在自己上的,用的人還是你自己。”
刑春連連點頭,不由問程玉酌。
“姑姑也是讀書人家出,怎麽進宮做了宮人?”
本朝的宮人大多是尋常良家子,富裕些的人家,可不舍得兒進宮為奴為婢。
程玉酌輕歎一聲,“時運不濟,家父被貶西南邊陲,病逝在了上任路上,母親也沒多久便去世了,我那舅父賣了我弟妹,讓我頂了他的兒進宮。”
刑春一聽就來了火氣,“怎麽還有這樣的舅父?!”
程玉酌搖搖頭沒有多言。
刑春見不言,替抱屈,半晌又問。
“姑姑本是家,落到這般,可怨恨?”
程玉酌笑笑,“不怨是不可能,但怨了又有何用?好好活下去才是要的。”
似是不想多言,了刑春和桐桐一起喝茶歇一歇。
趙凜在窗下看書,聽著窗外傳來的聲音,書頁被風吹翻了幾頁,也沒在意。
“彭。”
彭立刻走了過來。
趙凜看著箬竹隙裏影影綽綽的程玉酌三人,問他。
“程玉酌父親被貶所為何事?”
“回爺,十三年前,程司珍之父任揚州儀真縣知縣,因治下一人寫反詩而被牽連,貶西南,病逝路上。”
寫反詩的人並不是程玉酌的父親,他隻不過是因父母的份被牽連。
Advertisement
趙凜什麽都沒說,合起書,站了起來。
箬竹那邊,程玉酌搬出了的紅泥小火爐,招呼著刑春和桐桐一起吃茶。
“是黑虎泉的水,咱們嚐嚐鮮。”
果然如所言,沒有帶著怨氣活著。
趙凜卻想到了他找了五年的那人。
程玉酌與的子,倒也有幾分相像。
不知道許多年過去了,是否也像程玉酌一般活得通,拋去了許多迷惘。
*
歸寧侯府,滿園春花爭奇鬥豔。
歸寧侯老夫人老夏氏看著滿院子的客人,尤其特特看了一眼在貴婦人中遊刃有餘的紅子,轉頭問韓平宇。
“你可瞧見那紅子,那便是我跟你提起的秦玉紫,你以為如何?”
韓平宇早就看見了秦玉紫,卻沒看見自己親自邀請的程玉酌。
一問之下才知道,程玉酌本沒來。
他不免心中有些憋悶,又聽老夏氏繼續道。
“那子甚好,規矩禮數都不錯,還能寫會畫的。聽說在宮中的師父正是尚服局的尚服,那可是當年太後娘娘提拔上來的人,在皇後娘娘臉前也頗有麵子。秦玉紫本出不高,但貴在通著宮裏貴人,能說的上話,你意下如何?”
老夏氏前後問了兒子兩次,但卻得到兒子不敢興趣的答複。
“兒子續弦也要多考慮亭兒,能待亭兒好才是好。”
歸寧侯膝下隻有一,是年僅五歲的韓亭。
老夏氏不以為意,“亭兒是姑娘家,況且有你我在,人家怎麽會苛待?”
說著,見兒子還皺著眉頭,有了個主意。
“先讓來給亭兒做教養,正好讓亭兒親近親近,你也悉悉,可好?”
韓平宇聽進了這話,卻一下子想到了另外的人。
兒這個年紀,確實該找個教養的人,若不是秦玉紫,而是程玉酌呢?
Advertisement
若是程玉酌來做教養姑姑,是不是也能通自己母親識一番?
韓平宇有了這麽個想法,莫名就坐不住了。
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麽回事,同大夏氏親多年,也從未有過這般覺。
不僅沒有這般,這些年與大夏氏冷冷淡淡,兩人之間好像隔了厚厚的牆。
說不通,捅不破。
連帶著對那些妾室同房也提不起興致。
韓平宇曾見過旁人夫妻恩,琴瑟和諧,不能會其中滋味。
可如今,好似湖麵吹風、春湧一般,他甚至連眼前這一杯茶都喝不完了。
韓平宇再坐不住了,尋了個借口走了,打馬直奔程家小院而去。
*
程家,趙凜也被分到了黑虎泉的水泡出來的茶。
程玉酌泡了一壺龍井,茶葉不過尋常,用的這套茶卻有些意思。
是一套小兒戲水的彩,畫中小兒嬉笑打罵栩栩如生。
他以為程玉酌這般嫻靜的子,不會喜歡這些熱鬧的東西。
但一想到靜靜,好像也不奇怪。
程玉酌泡茶的手藝很是不錯,同專司其職的宮不相上下。
沒在宮裏做過茶水活計,可見是為了自己。
趙凜暗覺好笑,程玉酌倒是同那些在宮中幾十年的老嬤嬤一般,看多了也看淡了,不如眼下要。
可也不過二十五歲,竟有這份淡然。
趙凜喝著茶,聽著程玉酌教桐桐和刑春背三字經。
靜靜不好好聽課,跑去竹林下捉老鼠。
春風從窗欞吹進來,再一次吹了趙凜手邊的書。
趙凜長舒了口氣。
好像很多年沒有過這樣悠閑而靜好的日子。
他著此刻,但彭來報。
“歸寧侯爺來了。”
趙凜的緒卡了一下。
“他怎麽又來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139 章

皇後有旨:暴君,速侍寢!
夏梵音一度覺得當公主是件很爽的事,隻需要負責貌美如花,可是真的穿越後,她發現事情好像不太對勁??那一年,權傾天下的九千歲看上當朝最受寵的小公主,強勢掠奪,整個皇室反抗無效。“本尊要的女人,誰敢說不?”“……”沒人敢!經年流轉,九千歲榮登帝位,強勢立她為後,“朕會對你負責的。”“你不舉!”“舉不舉,你昨晚還沒嚐夠嗎?”梵音老臉一紅,“丫給我滾!”男人似笑非笑,“看來確實沒滿足你。”那一晚,梵音的腰差點折了。………………梵音曾一度不解,這該死的男人明明是個太監,為什麼總纏著她要要要?直到後來每天每夜都下不了床,她才明白這貨根本就是個假太監!【男女雙潔】
98.2萬字8 25227 -
完結130 章

猶記驚鴻照影
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 妹妹出人意料的逃婚,讓她無從選擇的嫁入天家。 從大婚之夜的獨守空閨,到知曉夫婿刻骨銘心的曾經,她一直淡然處之。 嫁與皇子,本就注定了與愛無關。她所在意的,不過是護得家人安寧。 她伴著他,一步一步,問鼎天下。她看著他,越是微笑就越是冷漠的眼睛。 從未想到會有一天,自己所信仰的一切,被他親手,毀滅得支離破碎。
29.7萬字8 6755 -
完結25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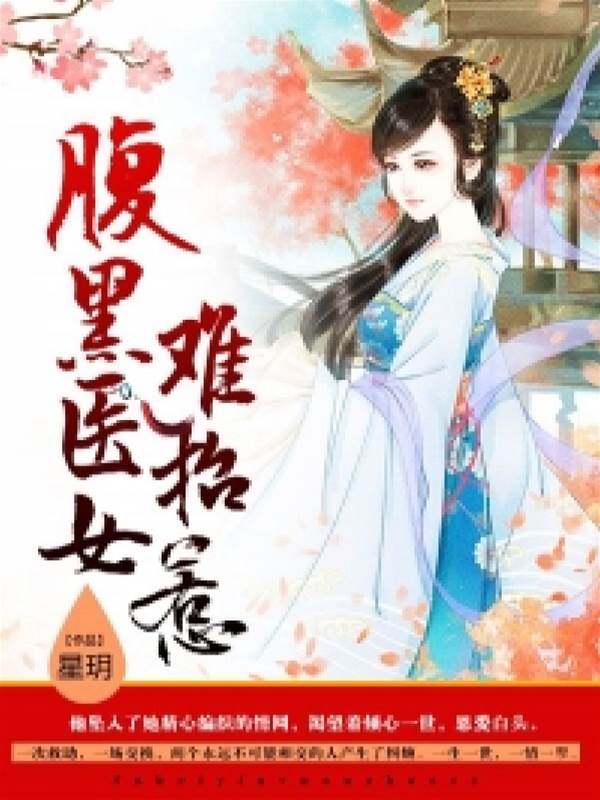
腹黑醫女難招惹
她本是現代世界的醫學天才,一場意外將她帶至異世,變成了位“名醫圣手”。 他是眾人皆羨的天之驕子,一次救助,一場交換,兩個永遠不可能相交的人產生了糾纏。 一生一世,一情一孼。 他墜入了她精心編織的情網,渴望著傾心一世,恩愛白頭。 已變身高手的某女卻一聲冷哼,“先追得上我再說!”
42.7萬字8 12262 -
完結397 章

嫁給權臣後,女配被嬌寵了
《嫁給權臣後,女配被嬌寵了》在魏國賤民唯一一次前往上界,經受鑑鏡鑑相時,鑑鏡中出現了天地始成以來,傳說中才有的那隻絕色傾城的獨鳳,所有人都在為魏相府的三小姐歡呼,樣貌平凡的我納悶地看著手,如果沒有看錯的話,在鑑鏡從我身上掃過的那一息間,鑑鏡中的鳳凰,與我做著同一個動作……
72.5萬字8 255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