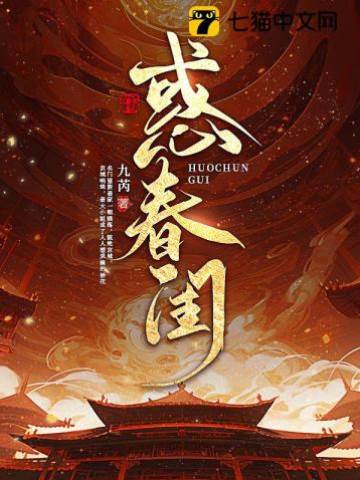《誤入樊籠》 第76章 出游(一更)
出了京兆尹, 剛踏出大門,二王子反手就給了烏剌一掌。
“蠢貨!”
胡人個個悍,手掌像扇一樣。
烏剌猝不及防, 這一掌打下去, 直接被打的趔趄了一步。
暈了半晌,烏剌才勉強直起。
手一,指上都是。
烏剌攪了攪口中的沫,盯著二王子:“大王為何怒?”
“你還敢問?”
二王子揚起又要打下去, 被邊的侍從拉住才住了手。
“大王不讓問,我如何能知。”
烏剌吐出了口中的沫, 呲著帶的白牙仍是一副桀驁的樣子。
“你數數,你已經鬧了多事了!”二王子沒打下去, 但卷起黃胡子已經氣得飛起來了, “你存的什麼心別以為我不知!”
他走近, 幽綠的眼珠惡狠狠地瞪了烏剌一眼:“若是這回當真出了事,你也別想回去。”
烏剌勾笑了:“我哪兒敢破壞盟誓,大王想多了。”
“你最好是。”二王子忽然走近, 一把攥住他的脖子猛地摔在了墻上,“再讓我發現,我就直接擰斷你的脖子!”
“奴不敢。”
烏剌被攥的臉紅漲,二王子才憤憤地離開。
他走后, 烏剌捂著嚨咳了幾聲。
接著, 他原本順從的眼神忽然狠起來,沖著那背影重重啐了一口:“什麼東西!”
“將軍, 大王這回是當真生氣了, 那我們還要不要繼續。”烏剌旁的人問道。
“你管他作甚!”烏剌斜著眼, “辦不好差事回去了一樣沒法代。”
怪只怪他預料錯了, 這太子和崔氏一方倒是能忍,他三番五次挑釁,連個反對盟誓的奏疏都看到。
“一群骨頭,兒孫都被分尸了還能無于衷。”烏剌磨了磨牙,心煩躁,“先喝酒去!”
Advertisement
京兆尹離琴行不遠,大清早的這一幕爭吵全然落到了崔璟眼里。
那兩人用的是突厥語,李臣年聽不懂,但崔璟倒是明白。
李臣年看著他攥著拳的手越握越,出言勸道:“你莫要沖,現在正在簽訂盟約的節骨眼上,等訂立了盟誓再收拾他也不遲。”
“簽了也沒用的。”崔璟搖頭。
“這三年我失憶流落西域,差錯間在不同的部落里轉了幾回手,倒是對突厥各部落的關系了個明白,突厥語,粟特語,吐火羅文字也學了個遍。這位二王子是聯姻公主所生,上留著一半漢人的,對大周頗為親近,可其他人本不是。”
“我猜……”崔璟繼續道,“此次續約不過是為了拖延時間備戰罷了,即便是簽了對方也隨時可撕毀,遲早是要有一戰的。”
“所以,烏剌是故意挑釁?”李臣年明白了。
崔璟點頭:“他既來了長安,我絕不能放過他。”
“你想做什麼,莫要把自己陷進去。”李臣年勸道。
“二王子已起了殺心,我不過幫他一把罷了。”
崔璟淡淡道,也說出了和崔珩一樣的話。
“何況我在旁人眼里已經是個‘死人’了,正好便利行事。”
他眼神篤定,把握充足。
李臣年仿佛看到了他昔日的彩,他也不再勸:“你想做就做吧。”
的確,大仇不報,崔璟就永遠難以真正站起來。
***
七月七是乞巧日。
大夫人、二夫人這些夫人們早已過了這個年紀,倒是府中的孩子們個個頗為歡喜,兩三日前便開始聚在一起,對月穿針,比比誰的手更巧。
滎來信的事已經送到了,大家都猜到鄭琇瑩與二公子不日便要定下了,于是紛紛往邊靠,變著花樣地恭維。
Advertisement
鄭琇瑩臉上雖笑著,但心里卻愈發地苦。
若是婚事不,崔璟再回來,的臉面可要徹底丟盡了。
雪聽了,心里微微有一遲滯,但須臾又恢復平靜。
果然還是同夢的一樣,二表哥還是要娶妻了。
不抱希,自然不會失。
是以當崔珩派人傳了口信要把乞巧的當晚空出來的時候,雪完全沒猜到他的意圖。
只是疑,這樣的日子,他不去找鄭琇瑩,反過來找做什麼?
“二表哥讓我出去做什麼?”雪問秋容。
“奴婢也不知,公子只讓您晚上這邊安排好,不要讓人發現。”秋容答道。
雪能有什麼安排,每回與他私會都要讓晴方守了門罷了。
雪問不出,只好點了頭,
日子很快就到了。
這一日不施宵,街市上紅男綠,人頭攢。
剛夜,各個酒家的燈籠便掛了出來,酒旗招展。除此外,賣糖人的,賣磨喝樂的,還有猜燈謎的呼和聲此起彼伏。
雪坐在馬車里走馬觀花地看著,眼中興味盎然。
“想看就大大方方的看,只掀開一簾能看得到什麼。”
崔珩假寐的眼睜開,看只敢兩指掀開一簾,悄悄的看著外面的樣子不悅道。
雪一噎,不是怕燈火吵了他休憩嗎。
“隨便看看而已。”雪放下了簾子,又問他,“二表哥帶我出來究竟做什麼?”
“不做什麼就不能帶你出來了?”崔珩反問。
雪不清他的意圖,便閉了不說話。
崔珩卻直接下了馬車,時候還早,他打算先帶在外面逛逛。
可崔珩在外面站了一會兒,沒等到人下來,又轉頭:“你不下來?”
“人太多了,萬一被人認出來了怎麼辦?”
Advertisement
雪踟躇,畢竟如今算是他的弟妹,一起出游,實在太容易惹閑話。
“把冪籬戴上。”
崔珩指了指馬車里放好的冪籬。
雪拿起來比了比,這冪籬長到腳踝,但紗質極為輕薄,既能遮住人,又不會憋悶,倒是很不錯。
這才放心地下了馬車,戴著冪籬遠遠的走在他后。
崔珩余里看退避三舍,眉間又皺起:“跟了,今日人多,你是想被拐走?”
“知道了。”
雪打量了一眼形形的人群,也有些害怕,碎步上了前。
這還是他們頭一回在這麼多人面前一起并肩。
雪總覺得有人在看他們似的,頗為不自在。
事實上郎才貌的,一個長玉立,一個纖秾合度,的確引得人頻頻回頭。
人群里有個看的出神的,一不小小心踩到了擺撞了雪一下,雪腳步不穩差點摔倒,幸而被崔珩扶了一把。
“這麼不小心?”崔珩聲音不悅。
但垂在側的手卻向出,他隨口道:“握了,省的被人沖走。”
那只出的手修長有力,雪頓了頓,不敢去牽,只輕輕握住了一中指:“這樣就夠了。”
“真出息。”
連手都不敢牽。
崔珩低笑了一句,直接將整只手包住,一把反握在了手里。
雪試圖去掙,崔珩眼眉一凜,眼神又怯了下去,不得不被握了跟在他側。
二表哥今天似乎有點怪。
雪不著頭腦。
但那只手真大啊,將包的嚴嚴實實的。
雪斂了斂眉,沒再反抗。
今日有花燈,一盞盞形狀各異的燈籠懸在一起,亮堂堂的格外引人注目。
燈下還懸了字條,大約是用來解謎的。
攤主遠遠的瞧見二人過來,料想是識文斷字的,連忙招呼道:“二位可要看看燈謎,猜對了這燈隨意挑選。”
Advertisement
雪駐足,盯著那盞上面花了只兔子的燈不。
“想要那個?”崔珩問。
“可以嗎?”雪抬頭。
“想要就去。”崔珩語氣隨意。
“娘子真是好眼力,這兔子燈今年可歡迎了,就是不好猜。”攤販笑道。
雪是真的心,但這字謎也的確不好猜。
“半青半紫……”
捋著紙條,眉心蹙的極。
“這些都是給尋常百姓玩的字謎,至多不過拆字拼字。”崔珩提醒道。
雪眼睛立馬亮了起來:“是個‘素’,對不對二表哥?”
那眼神太亮,崔珩猛然被晃了一下,頓了頓,才將人轉過去:“看我做什麼,對他說。”
雪鼓起勇氣重復了一遍,那小販笑了:“小娘子真機靈,沒錯,這燈是你的了!”
萬事開頭難,過了這個坎之后,雪便茅塞頓開,又點了幾個燈。
“公而忘私——是個‘八’。”
……
一臉猜對了四五個,眼睛撲閃撲閃的,比燈籠還亮。
直到攤販臉上出了為難之,雪過度的興才冷靜下來,對攤販解釋:“我只要一個,其余的都不要。”
那攤販頓時又喜笑開:“小娘子不但機靈還心善,郎君您可真有福氣!”
雪抿著,是機靈的,可關二表哥什麼事?
崔珩倒是頗用,隨手丟了個銀錠過去,勾著又攬著陸雪的腰往前:“走了。”
雪正滋滋的提著燈,也不計較這點話頭,點了點頭又隨他走。
那攤販撿了個銀錠,半晌回過神來,笑的更歡了:“您慢走!”
這貴人就是大方!
今日街市上格外熱鬧,過了花燈,不遠又支起的鋪面前擺放了花花綠綠的磨喝樂小人,引得不人駐足,尤其是。
崔珩一貫不喜這些花花綠綠,雪腳步倒是慢了下來。
“你喜歡這個?”他問。
“沒有。”
雪覺得不好意思,這麼大的人了還和一群小孩子喜歡一樣的東西。
雖說如此,那磨喝樂實在太吸引人了,眼神忍不住停了片刻。
“要哪個,自己挑。”
崔珩揚了揚下頜,把推過去。
“郎君真是好眼力,這是最新出的式樣,一套十二個,小娘子挑挑哪個喜歡。”
小販殷勤地跟雪介紹著。
雪聽的天花墜,越看越花了眼,拿起一個又放下,十分糾結。
“不知道要哪個?”
崔珩看著秀氣的眉微微擰著,眉梢了。
“我再想想。”雪一手一個,遞到了他跟前,“這兩個哪個好?”
“都要吧,有什麼可糾結的。”
崔珩看躊躇的樣子,直接開了口。
雪眨了眨眼:“不用了,用不著這麼多……”
崔珩已經讓楊保付了錢:“這一套都包起來。”
于是雪除了燈,手中又多了一大盒磨喝樂。
再往前走,看出了他們是個富貴的且崔珩是個大方的,那些小販都鉚足了勁的招徠著。
雪每多看一眼,崔珩便直接讓楊保付錢。
吃的,用的,戴的,買了一堆,楊保跟在后面,兩手都提滿了,懷里更是堆的跟小山一樣,引得不人議論紛紛,那些小販們更是雙眼放,一個勁的吆喝。
雪莫名覺得恥,扯了扯他的袖子:“這麼張揚不好吧?”
“你不喜歡?”崔珩問,毫不覺得不妥。
“那也不能買這麼多啊。”雪指了指楊保,“你看,楊小哥都快抱不下了。”
崔珩眉梢微挑:“你是擔心帶不回去?再個人來提不就行了?”
崔珩作勢又要讓楊保回去人。
“我不是這個意思。”雪急了,重重地握了下他的手,臉頰微微紅著,“旁人都在看,太破費了。”
這算什麼,不過是買了些東西。
連崔茵茵逛街的陣仗都要比這個大,更別提尋常的貴。
崔珩覺得可笑,但一低頭看見陸雪寵若驚,眼神慌的樣子,忽然又有些不是滋味。
因為沒人這麼縱過,寵過,所以只是一點這樣微不足道的對待,都覺得承不起。
也不敢相信他當時說要娶的話是真的。
這子真是又惹人生氣,又讓人心疼。
崔珩眼神復雜,攬著的腰靠的更近些,但語氣仍是冷:“給你你就拿著,那麼多話做什麼。”
雪愣了片刻,接著崔珩卻直接把一個裝滿銀子錦囊塞到了手里,將推了出去。
“看上什麼自己挑,花不完不許回來。”
哪有人著別人花錢的!
還給了這麼多。
雪捧著沉甸甸的銀子,一時不知道該做什麼。
可崔珩說的仿佛是真的。
認真算起來,他們之間的每一筆都清清楚楚,誰也不欠誰的,只等三個月后婚事解除,兩不相欠。
然而二表哥今天的表現似乎不太對,他仿佛是在單純的對好。
這算什麼?
他為什麼這樣?
雪心里有點,只好著頭皮上前:“我試試。”
躊躇了半晌,當走到一鋪子時,才終于停步,掏了所有的銀子。
崔珩背著遠遠地站著,并不拘想買什麼。
好半晌,后傳來腳步聲,他才回頭:“用完了?”
“用完了。”
雪輕輕點頭,手背在后。
肯用,算是有點長進。
“買了什麼?”
崔珩據不遠的鋪子估測著,大約是買了些子用的胭脂水之類的。
可是當陸雪的手從背后出來,慢慢展開時,他原本漫不經心的眼神卻忽然頓住。
“這是什麼?”崔珩問,額角的青筋突突。
“檀香手串。”雪捧到了他眼前。
“我知道。”崔珩換了種問法,“我是問,給誰的?”
“給你的。”雪輕輕地開口,“正好把銀子用完了。”
他給的銀子,盡數買了給他的東西。
言外之意,還是兩不相欠。
可真懂事,太過懂事了,懂事到讓人生氣。
“你到現在還不明白我給你銀子的意思?”
崔珩并沒接那手串。
雪茫然,垂頭看了眼手串,轉又要折回去:“二表哥可是不喜歡這手串,如果不喜歡,我再拿去換別的……”
“和手串無關。”崔珩語氣忽有些冷,“你就一定要這麼懂事嗎?”
雪不明白。
崔珩聲音低了下來,生氣中又夾雜一無奈:“你就一定要跟我分的那麼清楚?”
猜你喜歡
-
完結98 章

正妻不如妾ll
她驕傲跋扈,笑靨明媚指著他鼻子,道:“你完了。趙鈞默,你愛上我了,你永不能再愛他人了,因我不許。” 經年流轉,他卻淡淡地道:“明晰,能不能有些肚量容下她。” 當自己的丈夫和兒子站在了敵人的陣線上,當所有人都心存同情之情安撫從她手中偷去丈夫的女人,當所有人視她這個正妻為毒蛇猛獸囂張狠毒時,她漸漸死寂了下去。 他忍痛將她死死摟在懷:“是我對你不住。再看我一眼一眼便好,就一眼……”
22.6萬字8 40968 -
完結4591 章

神醫廢柴妃
清冷的眼眸再次睜開,她再也不是昔日懦弱被人毆打的她。當廢物變成天才,她光芒萬丈,誰與爭鋒!洞房花燭夜,他霸道的承諾,「從今以後,你是我唯一的女人!」她翻身,勾起他的下巴,狂傲道,「今晚開始,你是我的男人,要是敢背叛,先奸後殺!」
830.5萬字8 54623 -
完結393 章

和離后嫁給渣王死對頭
容落歌一朝穿越成性子軟弱的齊王妃,大婚之夜就飽受屈辱,丈夫與外室女容黛情投意合當著她的面茍合。你若無情我便休,腳踢渣男,手撕賤女,轉身給齊王的死對頭太子殿下做幕后軍師,聯手將渣男踩在腳底不能翻身。哪知道一不小心從軍師坐到了太子妃的位置,那個別人口中陰狠毒辣,敏感多疑的太子卻一點點將她吞吃下腹,寵成了京都人人羨慕的美嬌娘。
70.7萬字8.08 319966 -
完結593 章
錦鯉醫女,被八個哥哥團寵了
【錦鯉+團寵+萌寶+隨身仙山+神農鼎+醫術+經商種田】中醫世家女家主,穿成流放醫官家的三歲小萌娃。祖父去世,偏心祖母就要把撿來的她賣了。惡毒大房、勢利眼小姑,找茬分家。爹爹木訥,娘親病弱,四個哥哥未成年。沒關系,被吞下的,她通通會要回來。繼承了隨身仙山,稀有神農鼎。加上她超凡的醫術,藥食同源開成了全國連鎖。某日一向高高在上的男子,帶著她失散已久的四個哥哥,前來提親!!嗯!哥哥們留下,你可以走了……某男:……?
104.3萬字8 19596 -
完結183 章

風流債
沈初姒當年嫁給謝容珏的時候,還是先帝寵愛的九公主。縱然知曉謝容珏生來薄情,也以爲他們少年相遇,總有捂熱他的那日。 直到後來父皇病逝,兄長登基,沈初姒就成了沒人撐腰的落魄公主。 京中不少人私底下嘲笑她,跟在謝容珏身後跑了這麼久,也沒得到那位的半分垂憐。 沈初姒恍然想起當年初見。原來這麼多年,終究只是她一個人的癡心妄想。 謝容珏生來就是天之驕子,直到他和沈初姒的賜婚旨意突然落下。 這場婚事來得荒唐,所以等到沈初姒說起和離的時候,謝容珏也只是挑眉問道:“可想好了?” 沈初姒將和離書遞給他,只道:“願世子今後,得償所願。” 直到後來的一次春日宴中,兩人不期而遇。 沈初姒面色如常,言笑晏晏,正逢彼時的盛京有流言傳出,說沈初姒的二嫁大概是大理寺少卿林霽。 衆人豔羨,紛紛感慨這也是一樁不可多得的好姻緣。 卻無人可見,那位生來薄情的鎮國公世子,在假山後拉着沈初姒,“殿下準備另嫁林霽?” 沈初姒擡了擡頭,掙開被他拉着的手,瞳仁如點墨般不含情緒。 “……謝容珏。” 她頓了頓,看着他接着道: “你我早已和離,我另嫁何人,與你又有什麼關係?”
29.6萬字8 9798 -
完結1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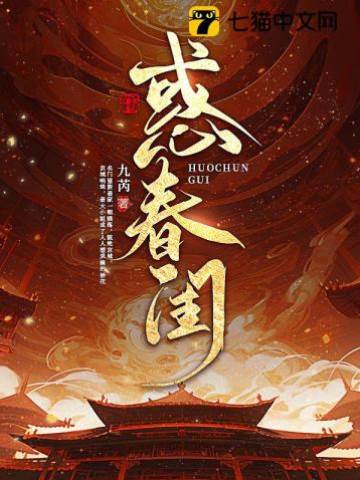
惑春閨
名門望族薑家一朝隕落,貌絕京城,京城明珠,薑大小姐成了人人想采摘的嬌花。麵對四麵楚歌,豺狼虎豹,薑梨滿果斷爬上了昔日未婚夫的馬車。退親的時候沒有想過,他會成為主宰的上位者,她卻淪為了掌中雀。以為他冷心無情是天生,直到看到他可以無條件對別人溫柔寵溺,薑梨滿才明白,他有溫情,隻是不再給她。既然再回去,那何必強求?薑梨滿心灰意冷打算離開,樓棄卻慌了……
31.5萬字8.18 789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