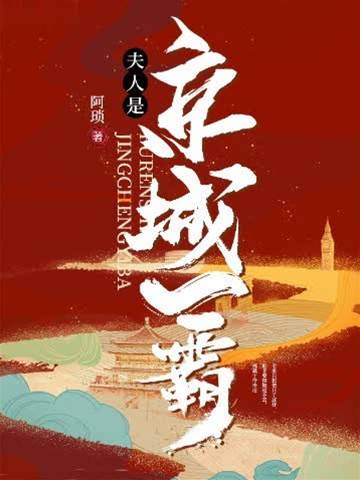《誤入樊籠》 第43章 一更
晴方原本是被帶著去取茶葉的。
誰知,取完了茶葉,那使格外的多話,又拉著閑聊了好半晌。
中途幾次想折回去都不行,直到聽到了主屋里傳來橫木砸落的聲音,才明白過來事不對勁。
應該是被刻意支出來了。
晴方撒手丟了茶葉便要去沖出去,可使們早有準備,捆了的手腳,堵了的,將在了柴房里任憑如何掙扎都不準出去。
捱了一晚上,直到清早的時候,柴房里出一縷,一聲輕的嗓音喚了,朦朦朧朧一睜眼,才發現是娘子來救了。
“娘子!”晴方嗚嗚地朝掙,發凌,格外可憐。
雪上前,彎替解開了繩子和塞在里的布:“你怎麼樣,有沒有欺負?”
“沒有,們只是不讓我出去。”晴方搖頭,眼下更擔心的是,“娘子可曾欺負了?”
“這里不是說話的地方。”雪沒直接回答,了發僵的手腳之后,便領著人出去,“蓮姨娘,我的使我帶走了。”
蓮姨娘不反蝕把米,被眼神一瞥,臉訕訕。
但二郎并未說什麼,此事也未鬧大,蓮姨娘便也息事寧人,掩著帕子咳了咳:“誤會一場,昨日院子里丟了東西,我也是誤會了你的使手腳不干凈,既都查清楚了,那合該讓你帶走。”
明明是他們蓄意設的局,現在反倒來誣的使。
但畢竟是仰人鼻息,此事即便鬧到了姑母面前,無憑無據的姑母也不可能會替出頭。
雪只扯了扯角,忍下怒意:“那姨娘且好好歇著,我便不打攪了。”
一主一仆,兩個人趁著天剛明回了廂房去。
蓮姨娘盯著雪窈窕的背影看了許久,見腳步虛浮,上穿的服雖與昨日相仿,但若仔細查看仍是能發現并不是同一套,便明白五郎所言非虛。
Advertisement
“的確是從清鄔院出來的?”蓮姨娘偏頭問道。
盯了一晚上的小廝湊上前,點了點頭:“千真萬確,從昨晚進去之后一直到今早上才出來。”
樣貌這麼清麗,平時一副格外矜持的樣子,蓮姨娘原以為當真是個貞潔烈,沒想到不過是嫌他們五郎份不夠,想要揀二郎的高枝罷了。
但二郎豈是那麼好攀的,到最后恐怕連個妾都撈不著!
蓮姨娘收回了輕佻的眼神,暗自鄙夷,又是個想飛上枝頭變凰的。
只是鄙夷的時候,全然忘了自己也只是個妾。
崔五著額上的腫包,看著窗外的影也恨的直咬牙切齒,不過一想起陸雪虛浮的腳步,他又嗤了一聲,得了幾分安。
為了避免陸雪說話,這藥是他花了大力氣弄來的三日醉。
這藥可不是那麼容易解的,以的板,被二哥那樣的武將玩弄上三日,興許需臥床休養一段時日。
到時候那傷比起他的額上的傷來,恐怕也不遑多讓。
崔五磨了磨牙,記痛快之余又有些心有不甘,若沒被二哥截胡便好了,那這三日便該是他來。
直到那抹纖細的影徹底消失,他才憤懣地轉進去。
但這剩下的藥卻是不能再留了,崔五忍著心痛,讓人把藥悄悄地埋在了柳樹下。
雪還全然不知曉上這藥的來歷,昨晚明明解了一回,還是渾發著虛汗。
一路上走走停停,好半晌才被晴方攙回西廂房。
陸雪凝一貫歇的早,起的晚,昨晚雪出去的時候已經是傍晚了,因此覺得長姐未必會發現。
不巧推開院門的時候,陸雪凝正起了床。
咦了一聲,用審視的眼盯著:“這麼早,你去哪兒了?”
Advertisement
“哦,沒去哪兒,今日天氣好,我原是想采些清給姑母送去。”雪拂了拂額邊的碎發,并了雙,盡量不讓看出些異常。
陸雪凝這兩日正在興頭上,聞言也并未懷疑,反而過去拉了的手:“你是個有孝心的,想必姑母知曉了定然十分欣,也不枉白疼你一場,打算把你配給三表哥。”
連長姐都知道沖喜的事,難不消息已經散出去了……
雪瞬間抓了手心:“是麼,這是什麼時候的消息?”
“姐妹一場,這樣的好事你還瞞著我呢。”陸雪語氣親昵,“父親的信已經到了,我清早去請安的時候正看見姑母拿起,姑母還說讓你這兩日好好將養將養,養的氣紅潤一些,等后日老太太回來,趕著十五的正日子,大家伙兒都去請安的時候領著你去見一見,當眾把事給定下來呢。”
當眾定下來,這豈不是再無回旋的余地了?
雪聞言心底沉甸甸地墜著,久久不過氣。
“怎麼,高興傻了?”陸雪凝有意戲謔,“三表哥可是這國公府的嫡子,能嫁給他是求都求不來的福氣,你可要好好珍惜。”
雪看出了眼中的嘲諷,慢慢出了手,垂下了眼皮:“這自是我的福氣,不過趕在長姐定婚屬實是有違禮儀,也愿長姐早些覓得良人才是。”
“我的婚事自有我母親心,不勞妹妹關心了。”陸雪凝不悅。
可不是像一樣毫無倚仗,有母親和姑母在,就算嫁不了二表哥,也不至于淪落到沖喜,嫁給一個病秧子!
大早上的便聽聞了這麼一樁噩耗,雪一整日都渾渾沌沌的。
不知是不是藥效未散的緣故,甚至還覺得渾發,打不起神來。
Advertisement
雖則二表哥昨晚沒真正,但他畢竟換了種方式幫了。
盡管當時已經意識迷離,但那解了的松快還是記得住的。
為何這會兒還是有些燥意,難不這藥藥效還殘留著麼……
雪實在使不上力氣,便吩咐晴方悄悄了水洗了一番,闔著眼小憩。
可是越休息,越覺得不對勁,里仿佛還是一邪火在竄,燒的比昨日更旺。
剛換上的服沒多久便被汗了,蜷在榻上,死死抓著枕頭,努力不去想里翻滾的熱意。
越忽視,反而越明顯了記。
控制不住地想起了二表哥,想起他上的涼意。
他大約是被惹惱了,吻著的時候極為兇狠,撕咬的瓣鮮淋漓,可更加淋漓的還有被他所之。
雪閉了眼,努力不去回想他的模樣。
越是不去想,反倒記得越清楚,連那指關節上的一道微微凸起的疤痕都能覺出來。
這藥,大約本就沒解吧……
也對,依著崔五的脾,他怎會如此輕易放過?
整整一夜,雪又害怕又難,睡得極不安穩,晴方是幫換便換了三次。
最后一次,當看到整個人快虛了,無力伏在床榻上氣的時候,晴方忍不住咒罵起這座公府來。
一個兩個,都各懷心思,偏偏把們姑娘攪合進去,了爭權奪利的件,任人擺弄。
如今一個尚未通人事的大姑娘,竟被下了這樣惡毒的藥,真是天煞的。
然而這種藥下到子上,怕毀了名聲,們又本不敢去請大夫,只能這麼苦苦煎熬。
熬了一整晚,第二日清晨的時候,雪才稍稍回轉。
實在不住了,便是二表哥不應,請他替悄悄請個大夫也。
Advertisement
要不然單是這副態,遲早要瞞不過人眼。
沉了許久,才忍著恥朝清鄔院走去。
此日休沐,走了不久。遠遠的便瞧見二表哥正在竹林邊,似乎是剛從大夫人那里請安回來。
他今日穿的是常服,一月白襕袍,長玉立,負手站在一叢綠竹前,倒真有幾分儒雅君子的風范。
前提是——
若是雪不知曉他執劍的手有多有力的話。
雪眼神從他微曲的指關節上移開,用帕子了發燙的臉頰,才鼓足了勇氣上前。
然而尚未靠近,竹林后的鄭琇瑩忽然繞了過來,手中拿著一個青瓷瓶沖著崔珩欣喜的:“二表哥,你說的沒錯,這里的竹果然很多,稍稍片刻,便已采了半罐了,多虧有你,否則我這清酒還不知何時能釀。”
鄭琇瑩晃著手中的青瓷瓶,一向端莊的臉上難得出了粲然的笑意。
“舉手之勞。”崔珩淡淡地應聲。
余里,當瞥見不遠的一角白,目頓住。
“等釀了我一定第一個你嘗!”
鄭琇瑩小心翼翼地將瓷瓶遞給侍,再順著他的眼神看過去,忽然看到了陸雪,笑意凝固在角。
上次端節的時候,原以為陸雪是在與外男私會,但昨日去給大夫人請安的時候才明白了因果,原來這個表姑娘只是不想給崔三郎沖喜。
是個可憐的。
但不想沖喜,也不能往二表哥上攀。
鄭琇瑩心生警惕,揚了揚臉,沖笑道:“咦,這不是陸妹妹,今日怎有空到大房來?”
“我……”陸雪原是想去求二表哥的,但他邊站著鄭琇瑩,雪又忽地想起了他們要定婚的傳言。
當著二表哥未婚妻的面,去求他一記自己,雪實在拉不下這個臉。
藥效和恥翻滾在一起,整個人幾乎快燒起來。
雪偏了頭,只低聲道:“巧路過,便過來行個禮。”
鄭琇瑩哦了一聲,又邀一起來采竹:“這清鄔院的竹極其甘甜,用來做酒再好不過,陸妹妹不妨一同過來采些。”
雪能忍著灼燒的熱意過來已經很勉強了,哪里還敢再上前。
搖頭,遠遠地往后退:“不了,我還有事,二表哥和鄭姐姐留步。”
鄭琇瑩見頗為識趣,客氣了一番也沒再留。
崔珩眼神從上掠過,察覺到了一不對勁。
似乎有話要說。
鄭琇瑩站在他側,約察覺到了他緒的變化,擔憂地湊過去:“怎麼了?”
“無事。”崔珩掩下了緒,“你不是說想一同去山上祭拜兄長,可以手準備了,我記得,兄長最吃你做的荷花。”
若當年沒出意外,鄭琇瑩原本是應當嫁給他兄長的。
一提起大表哥,鄭琇瑩怔忡了片刻,手中的帕子無意識地絞,半晌才敢應聲:“好。”
鄭琇瑩走后,崔珩便吩咐著準備祭拜的事。
等忙完正事,晚上回到清鄔院之后,他不知怎的又想起了陸雪白日里說還休的樣子。
的雙頰似乎太紅了些,臉也有些蒼白,又讓他不自地想起了昨晚攀著他,整個人弱無骨地往他上蹭的景。
既妖且麗,不是已經幫了了?大白日的怎麼還像昨晚中了藥那般勾人?
崔珩抿了杯涼茶,才下了那尚未紓解的躁郁。
但這原本不燃香的屋子里,卻仿佛都縈繞著一一縷若有似無的香氣,愈發讓人心煩。
打開了窗,滿腦子的綺思旖念才稍稍散去。
他問道:“我讓你去查的慧覺又如何了?”
楊保就知道公子是個面冷心熱的,雖趕了表姑娘走,但當晚便吩咐他去查慧覺的底細了。
“已經讓人去查了,只不過這慧覺是個云游僧,原是在江左出家的,這一來一回還要些時日。”
查人的確費功夫,但祖母已經回來了,二嬸又已經拿到了回信,不出意外明日大概便要趁著請安的時候哭慘,求得老太太心,擱置長之序先為三郎定親了。
僅剩一天的時間了,陸雪現在定然十分著急。
崔珩不用想,眼前便浮現出了那張泫然泣的臉,微微有些分神。
“除了慧覺的事,您讓我盯的五郎君那邊也有了消息。”楊保將一個紙包從袖中掏出來,“這是從柳樹下挖出的,我拿去驗了驗,是一種做三日醉的迷藥。”
“三日醉?”崔珩倏地回頭,方才的不解瞬間了然。
這是一種萃取過的催藥,藥效強勁,所以戲稱三日醉。
崔五竟對陸雪用了這種藥,怪不得他明明幫了一回,今日還是一副臉頰緋紅的樣子。
若是如此,那昨晚是怎麼捱過去的?
今日更是,是那雙眼,眼里便能掐&30記340;出水來,更別提別。
崔珩執著杯子的手久久未,忽地想起了纏著他不放的樣子,著杯子的指骨驟然收。
“今晚有來嗎?”他回頭問道。
這院子里來來往往自然是不缺人的,楊保愣了片刻,才反應過來公子問的是誰。
“沒有。”楊保低著頭。
崔珩抿著茶,久久未語。
今日不過是巧見到他邊站著鄭琇瑩,便退的遠遠的。
指能厚著臉皮學會取悅他,這輩子算是不可能了。
一杯涼茶飲盡,當時候已經到了亥時的時候,崔珩擱了杯子,還是起了,沉聲吩咐楊保道:“把披風取來。”
猜你喜歡
-
完結184 章
穿書之我成了暴君的掌中嬌
玄風淺不過是吐槽了一句作者無良後媽,竟穿越成了狗血重生文裡命不久矣的惡毒女配!為保小命,她隻得收斂鋒芒,做一尾混吃混喝的美豔鹹魚。不成想,重生歸來的腹黑女主恃寵生嬌,頻頻來找茬...某美豔鹹魚掀桌暴怒,仙力狂漲百倍:“今天老子就讓你女主變炮灰,灰飛煙滅的灰!”某暴君霸氣護鹹魚:“寶貝兒,坐好小板凳乖乖吃瓜去。打臉虐渣什麼的,為夫來~”
32.1萬字5 22571 -
完結78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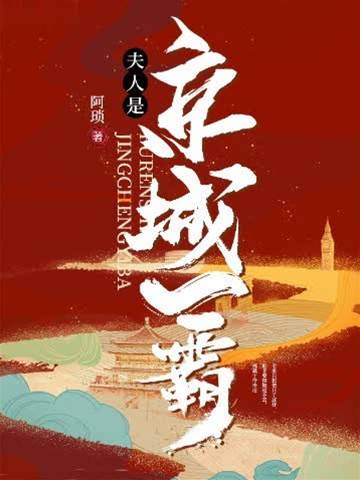
夫人是京城一霸
七姜只想把日子過好,誰非要和她過不去,那就十倍奉還…
123.2萬字8 19066 -
完結1064 章
全能毒妃:世子降不住
穿越到死人的肚子裏,為了活下去,晞兒只好拚命的從她娘肚子裏爬出來。 狠心至極的爹,看都沒看她一眼,就將她歸為不祥之人。 更是默許二房姨娘將她弄死,搶走她嫡女的位置。 好在上天有眼,她被人救下,十四年後,一朝回府,看她如何替自己討回公道。
186.1萬字8 19787 -
完結791 章

齊歡
她可以陪著他從一介白衣到開國皇帝,雖然因此身死也算大義,足以被後世稱讚。 可如果她不樂意了呢?隻想帶著惹禍的哥哥,小白花娘親,口炮的父親,做一回真正的麻煩精,胡天胡地活一輩子。 等等,那誰誰,你來湊什麼熱鬧。
153.4萬字8 968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