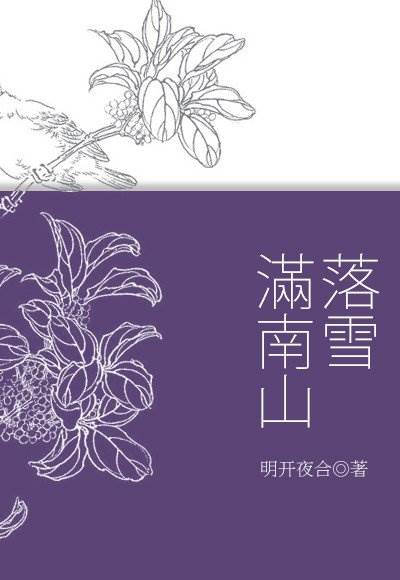《溫柔臣服》 第 88 章 小野貓(七)
檸原本在玩著手機,聽他這麼說,終于把注意力從手機上轉移到他上,蹙眉:“你說什麼呀?”
鐘深今日穿的是黑的西裝,白襯衫,領帶是檸上次送給他的,斜條紋,低調的;因著剛剛的緒外泄,鐘深此時仍舊有些不適。
他問檸:“那你今晚想住哪兒?”
檸放下手機。
前面的司機兢兢業業地開著車,不敢聽不敢看。
檸掉鞋子,紅長下一雙修長雪白的沒有穿子,著意直了,搭在鐘深的西裝上,蹭了蹭,笑:“當然是你那里呀。”
鐘深說:“下去。”
“我偏不。”
檸眼睛彎彎,見他不為所,反而更加放肆;又往前了,著迷一樣地看著鐘深的臉;鐘深沒有直視的眼睛,下頜線冷,哪里還有平時笑的模樣?
檸上去,撒:“鐘深呀,你今天怎麼回事啊?怎麼這麼不通人呢?”
“不通人?”鐘深笑了笑,著興風作浪的手,問:“那你覺著什麼算通人?”
說到后來,聲音低下去;鐘深剛想推開,檸了一聲,委委屈屈的:“你弄疼我了。”
鐘深松開手。
檸說:“我好不容易回來,這麼久了,你就不想我?”
故意撥,兩人本來就是相互取悅;檸放得開,膽子也大,沒過多久,前排的司機聽到鐘深略帶低啞的聲音:“回家。”
司機立刻變道。
檸不知道鐘深今天的糟糕緒到底怎麼回事,也懶得去思考。
有一萬種可以用來對付鐘深的方法。
上上策就是睡他。
如今鐘深在明京的房子自然不會再是當初的小公寓,檸連晚飯都沒有吃;檸來鐘深這邊房子的次數不多,但最喜歡頂層小閣樓的房間,鋪著絨絨的地毯,玩偶,書籍,檸覺著今天的鐘深有點魯,沒幾下,推開他,皺眉:“疼。”
Advertisement
鐘深臉仍舊沒有好轉,看檸里氣不了的模樣;他單膝跪在毯上,著檸的臉,問:“這就疼了?”
檸努力直腳尖,毫不客氣地踢了鐘深一腳;鐘深著的胳膊,看了一陣,終于站起來。
檸說:“今天晚上我睡在哪里?”
還真是沒心沒肺。
這個節骨眼上問出這種話,鐘深穿好睡:“你想睡在哪兒?”
剛說完,檸笑瞇瞇地蹭上來,自后抱住他:“當然是你房間呀。”
“不嫌疼了?”
“不呀,”檸著他的手腕,勾著他脖頸;頭發長長了不,只是發尾仍舊有點泛黃,垂在口、肩膀,發尖掃過他的手腕,眼睛亮晶晶,“那你不要了,換我自己來好啦。”
鐘深的一腔火氣都被一句話輕輕巧巧下去半截。
不知死活。
以前的鐘深這麼點評尚稚氣的檸,如今他依舊可以拿這個詞來點評。
十幾歲時的檸是初生牛犢不怕虎,才敢那樣肆意地招惹他;現在的檸是準地知道他每一要命的點,多了幾分有恃無恐。
等到檸玩夠了心滿意足地睡覺,鐘深才起。
檸還沒陷沉睡狀態,手拽了拽他的服:“去哪兒呀?”
“衛生間。”
檸終于松開手,呢喃一句:“那你快去快回呀。”
抱著被子,搭在上面,這次是真累了,眼睛都沒睜開。
鐘深換好襯衫,走出去;集團將在下周召開新的董事會議,他需要在這個時候得到梁雪然手中的選票。
確認自己此時穿著妥當之后,鐘深坐在書房中,發出視頻通話邀請。
半分鐘后,對方接。
大屏幕上,鐘深清晰地看到梁雪然頭發噠噠地站在屏幕前,一臉嚴肅的魏鶴遠坐在后,正在給吹頭發。
Advertisement
鐘深笑了:“魏先生真有閑心啊。”
因著先前的事,魏鶴遠對鐘深的觀并不好;他冷著臉,頗為高冷地應一聲。
梁雪然推開他的手:“等下再吹,我和鐘深有正經事要說。”
“頭發吹不干會冒,”魏鶴遠不悅,“你們聊你們的,不用管我。”
梁雪然無奈地朝著鐘深攤手。
聊完了董事會的事,魏鶴遠也吹干了頭發;梁雪然好奇地問鐘深:“檸檸呢?”
鐘深說:“睡著了。”
放好吹風機的魏鶴遠抬頭看鐘深,臉上終于不再是那種“你個小妖還有多花招”的表。
梁雪然說:“你和檸這都兩年了吧,怎麼還沒有更進一步?這進度條有點慢啊。”
面對著這樣明顯的調侃,鐘深嘆氣:“郎有妾無意,名不正言不順。”
梁雪然從他神中窺出不對勁來:“怎麼?吵架了?”
“我倒是希能和我吵,”鐘深說,“吵不起來。”
檸能意識到他生氣,如果心好,立刻就會搖著尾一樣過來哄他,親到他沒有脾氣;但若是也不開心,十天半個月不理他也是常事。
沒心肝的小東西。
永遠喂不的小野貓。
鐘深最終還是說了出來:“檸檸的前未婚夫訂婚,明天要去婚禮現場。”
梁雪然終于明白了,原來是醋了。
回頭看一眼大醋壇子,梁雪然笑地安他:“說不定檸檸是有苦衷呢。”
“不是那種人,”提到檸,鐘深有些無奈地笑了,“從來都不會人制約。”
這點倒是真的。
梁雪然還真的沒見過比檸更瀟灑的人。
魏鶴遠不滿意妻子同疑似前敵多聊:“然然,小蛋撻醒了,你要不要去看看?”
Advertisement
這句話果然是殺手锏,梁雪然同鐘深說了再見;魏鶴遠關掉視頻通話,轉過,去了嬰兒房。
魏鶴遠堅持要讓孩子從小就養分床睡的好習慣,雖然小蛋撻還沒到半歲,已經開始被迫“獨立”。畢竟從一開始選擇的就不是母喂養,晚上夜哭,也會有專門的月嫂來喂哄睡他。
在照顧小崽子方面,魏鶴遠信奉的第一原則就是堅決不能讓妻子累到。
小蛋撻的確醒了,剛剛喂過,睜著一雙黑葡萄樣的眼睛好奇地看著自己媽媽;梁雪然親親他的小臉頰,小蛋撻的手小,一點點,抓住媽媽的手指,笑起來。
逗了一陣小寶寶,魏鶴遠才開口:“鐘深——”
“指天發誓,他真的在很認真地追求檸檸,”梁雪然笑,“我都和你說過好多次啦,一開始鐘深的確是提過商業聯姻,但真的也只是基于利益的建議啊。”
魏鶴遠毫不留地說:“追個孩追炮友關系,也真夠沒用。”
梁雪然看著小蛋撻在打哈欠,出手指,親親自己的小崽崽。
站起來,笑著對魏鶴遠說:“你可別說這種話,當初你不是也這樣麼?”
魏鶴遠面坦然:“我升級比他快。”
可不是麼?不到一年時間,魏鶴遠功晉升為丈夫,以及孩子他爸。
現在鐘深和檸還停留在約約約的層面上。
“我和檸檸不一樣,你和鐘深也不一樣,”梁雪然想了想,告訴魏鶴遠,“檸檸……有一點點缺乏。”
魏鶴遠低頭看。
梁雪然想了想,告訴他:“當初我會再接你,就像你說的那樣,我一直心里有你;但檸檸不一樣,心里面沒有鐘深,只在乎自己。倒也不是自私,天生的不會察覺到這種。”
Advertisement
缺乏同心,不會同。
檸太冷靜了,永遠都知道自己怎麼做能得到最好的東西,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讓自己過的更舒服。
檸給做了兩年的助理,梁雪然對的脾也了解的差不多。
小蛋撻睡著了,梁雪然抱住魏鶴遠,個子不夠高,夠不到他的;魏鶴遠自覺地微微彎腰,好讓小妻子能夠心滿意足地摟住他脖子,送上一個親親。
梁雪然總結:“所以呀,鶴遠哥,你不要再吃醋啦。”
-
檸一覺睡醒,鐘深已經不見了蹤影。
打著哈欠穿服下床,離請柬上的時間還差一段時間;檸也不著急,慢吞吞地挑小禮,化妝……等抵達請柬上地點的時候,恰恰好趕上婚禮開始。
當年明京高權貴落馬不,幸存的這些人家一個個夾了尾做人,這兩年也低調了不;檸打量著周遭婚禮現場的布置,不由得喟一聲幸虧自己當時沒和陸清把這麼個婚約繼續下去。
那時候還打算在海島上舉辦婚禮呢。
看來陸家近兩年也不太行,迎娶安甜那麼個千金大小姐,竟然也只是在這樣的地方。
婚禮還沒開始,檸跟著指引坐下;好巧不巧,旁邊的位置就是鄭蝶。
鄭蝶今天邊沒有那個熊孩子,但看到檸之后,仍舊是震驚地手一。檸對毫無興趣,慵懶坐在旁邊的空位置上,難的主開口說話:“好巧。”Μ.166xs.cc
“……你怎麼來了?”鄭蝶低聲問,很快想到一個不可思議的念頭,大吃一驚,“你該不會是想攪黃安甜的婚禮吧?”
檸如同看一個智障看著:“我還沒那麼不要臉。”
挲著包里面的手機。
檸起初并沒有來觀陸清婚禮的打算。
對來說,陸清這個前未婚夫的地位其實并不比路邊一株野草強多,當初兩人的事一拍兩散,檸也發表不了什麼想法。當初爸媽已經算得上是畏罪自殺了,陸家人除非是豬油蒙了心,堵了眼睛,才會繼續把這門親事繼續下去。
沒有利用價值了。
至于陸清和曾經的死對頭安甜結婚,檸心里面也沒什麼想法。
反正娶誰不是娶嘛,在明京里面,檸沒有幾個真正的朋友,倒是有不真正的敵人。
反正又不喜歡陸清。
兩天前,安甜給打了電話,說婚禮請柬已經送到檸家中了,誠摯地邀請檸參加的婚禮。
在檸明確表示自己沒有毫興趣之后,安甜笑了:“那你對鐘鳴的死也沒興趣嗎?”
檸眼皮一跳。
鐘鳴落水亡前見過的最后一個人就是鐘深。
一家便利店的攝像頭清楚地錄下兩人在大街上的爭執、肢沖突。
當鐘鳴溺亡之后,這段錄像也被翻了出來;因為這錄像,直接把鐘深列為目標嫌疑人——誰都知道這一對孿生兄弟并不和睦。
雖然是雙胞胎,但一個從小就長在梁老先生膝下,另一個在原生家庭中,兩個人幾乎沒有任何際。
當初都在傳,是鐘家父母想要認鐘深回去,鐘深嫌棄鐘鳴擋了自己的路,才會對自己的親哥哥痛下殺手。
他們都不知道,就在鐘鳴落水亡的前一個月,他曾經在醉酒后妄圖染指檸,被鐘深生生踢斷了兩肋骨。
檸咬著手指,沒有理會鄭蝶的目。
安甜說,手上有鐘深最想銷毀掉的東西;是什麼,沒說,但檸聽的口氣,和當初鐘鳴落水有關。
檸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
時間到。
新娘子穿著麗的婚紗,手捧著潔白的百合,微笑著走過紅毯,走向正中央燈璀璨的地方。
檸瞇著眼睛看了看陸清,覺著后者似乎比之前胖了不;沒有那種玉樹臨風的年了,乍一看上去,和普通人沒有多大區別。
陸家老爺子退休之后,陸清的父親一直升不上去,他們人脈漸漸凋零,如今已經遠離了明京中心,為了邊緣人。也難怪會在這個時候選擇和安甜結婚,畢竟安甜家里還有個近期很得勢的哥哥。
前期檸在這里坐立難安,知道安甜的目的,無非是在面前耀武揚威最好在秀個和陸清的恩;讀書期間人人都知道安甜倒追陸清癡心不改,偏偏陸清最后和檸訂了婚。
按理說,檸不可能會來這里白白的委屈。
但偏偏還是來了。
檸也覺著自己莫名其妙。
就像現在,安甜故意把安排在昔日的朋友中央,無論怎麼劃線基本上都是和檸有過節的人。滿桌的人看看檸,皆和好友心領神會的一笑。
安甜可太狠了。
檸面無表地想。
的確不了這些人看落敗者的眼神。
婚禮結束,新郎新娘挨桌敬酒過來,一直到了檸這桌,陸清終于看到了檸,臉上的笑容頓時消失的無影無蹤,手中杯子里的酒傾斜灑出來,澆到子上也好似沒有察覺,失神地盯著看。
他旁邊的安甜仍舊保持著優雅知的笑容:“檸檸,好久不見,真是越來越漂亮了。”
安甜挽住陸清的胳膊,一只手舉著酒杯,同陸清一笑:“傻站著做什麼呀?快敬酒啊。”
陸清如大夢初醒,笑了笑,眼神復雜地看著檸,著酒杯的手微微抖。
旁邊人都等著看好戲。
雖然都沒有說話,但心里面已經把檸劃到“干擾新郎新娘”這一派里。
當初檸和陸清訂婚的時候有多風,現在就有多麼狼狽;脾氣糟糕的前友來大鬧婚禮啊,這得多沒腦子多沒有眼力見兒才能這種事來?
對檸的反越多,對安甜的同酒越重。
檸面如常:“祝你們新婚大吉,白頭偕老。”
仰臉,剛想把那杯酒喝進去,猝不及防,一雙手自背后出,從手中溫而堅定地奪走杯子。
檸神怔忪。
黑黑的鐘深站在側,一手攬著肩膀,另一只手舉著酒杯,微笑著對陸清說:“抱歉,檸檸最近不舒服;這杯酒,我替喝。”
猜你喜歡
-
完結782 章
帝國總裁小嬌妻
“薄少,不好了,您那個巨醜的前妻偷偷回來了。”“又想糾纏我,來人,抓她去申請世界吉尼斯最醜記錄。”“不是的,薄少,她突然變漂亮了。”“有多漂亮?”“追她的人可以繞地球一圈。”“我親自去看看!”“恐怕不行,她說前夫與狗不見。”
72.7萬字8 32658 -
完結347 章
重生後,病嬌大佬花式寵妻
【腹黑強大男主vs乖巧堅韌女主/甜寵+萌寶+娛樂圈+校園+後期女強】容司城上輩子被人陷害,眾叛親離,落魄殘疾后只有葉晴安全心全意照顧他,重生后,他對葉晴安每天花式寵! 酒局上,葉晴安吐了有潔癖的容司城一身,周邊的人驚恐,趕緊讓她給容爺道歉。 “對不起,容爺!” 葉晴安膽怯地開口。 “容爺也是你叫的!” 容司城臉色陰沉,隨即捏住她的小臉道,「乖,叫老公! “這是一個病嬌大佬重生後花式寵嬌妻的甜膩故事。
48.5萬字8 45384 -
完結6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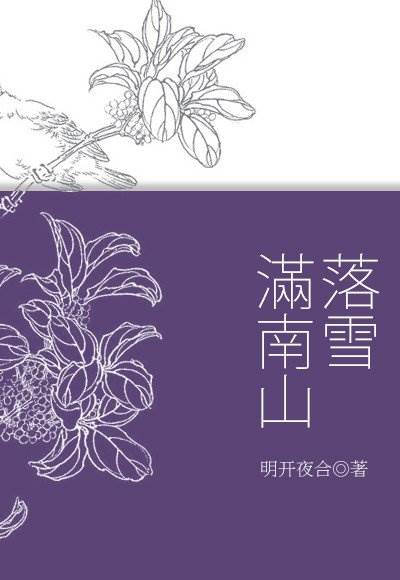
落雪滿南山
[小說圖](非必要) 作品簡介(文案): 清酒映燈火,落雪滿南山。 他用閱歷和時間,寬容她的幼稚和魯莽。 高校副教授。 十歲年齡差。溫暖,無虐。 其他作品:
18.5萬字8 2384 -
連載282 章

總裁大叔的小嬌妻
你有沒有這樣的體驗:和男朋友好著好著,忽然就發現了男朋友的一些不可言說的二三事。比如說洗澡洗完之后,他會像狗一樣的忽然開始搖擺身體甩干水滴?比如說接吻接著接著,他的頭上忽然就冒出了耳朵,身后忽然就冒出了長長的尾巴?你有沒有這樣的體驗:明明在公司里存在感很低,但是每次就總是能在開小差的時候被上司逮到然后就是一頓被收拾?身為上市公司的總裁,陸蒼黎向來注重同下屬之間的關系問題,而這一點,寧晞得到了充
72.2萬字8.18 69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