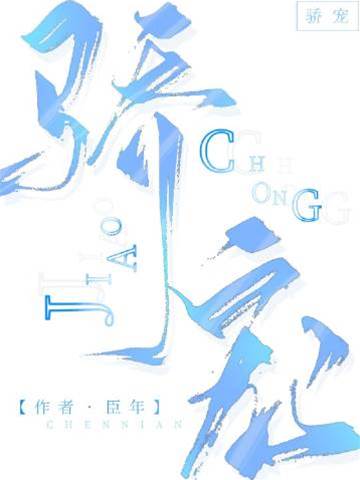《南城》 045
「就停這裏吧。」汽車行到老柳巷外,清溪輕聲對司機道。
司機看向車外,老柳巷對面就是南湖,湖畔行人來來往往,卻更襯得狹窄的巷幽靜荒涼,讓一個滴滴的小姐單獨回家,司機不放心,出了事,回頭他無法向行長待。
「我送小姐到門口。」司機語氣恭敬地堅持道。
清溪做賊心虛,點點頭。
司機便一直將車開到徐宅外。
清溪下了車,站在門口朝司機擺擺手。
司機這才離開。
清溪躲在門牆側,一邊聽汽車的距離,一邊聽院的靜,確定沒驚門房,清溪鬆口氣,再悄悄地往巷子外走去。街坊門前都掛著燈籠,每隔一段距離還有路燈,清溪並不害怕,而且知道,顧懷修的人肯定在暗中保護。
離巷口近了,一陣湖風猛地灌了進來,清溪了巾,順便往上遮了遮,擋住下。
未婚的姑娘瞞長輩去私.會外男,這有違清溪自的家訓,怕被人認出來,微低著頭走路。柳園位於湖東,出了老柳巷再往南行十來分鐘就到,岸邊圍滿了等著看煙花的人們,或是全家出遊,或是人攜手,亦或是男、夥伴們結伴,一個人走在馬路對面的清溪,怎麼看怎麼可憐。
柳園乃南湖名景,園種了一片片柳樹,鬱鬱蔥蔥地在頭頂結綠傘。那是春夏秋的景,這會兒柳樹都禿了,但因為臨湖,園還是滿了人。清溪遠遠地著,腳步漸漸變慢。顧懷修為何約在這裏?就為了「月上柳梢頭」嗎?
遲疑著,清溪來到了柳園正門外,剛站好,就見草叢裏竄出一道黑影,嚇得連退好幾步。
來福無辜地著未來主人。
清溪本來有點冷的,被來福這一出弄得,渾都熱乎乎的了。試著走向來福,來福卻扭頭往裏跑,黑黑的一條大狗幾乎與夜融為一,如果不是清溪先看到了它,目一直追著,極有可能發現不了,就像來福經過的那些路人。
Advertisement
三分鐘后,來福跳上岸邊一條畫舫,門路地鑽進蓬去了。
清溪知道,顧懷修就在裏面。
可是,終於要見到了,突然很張。
「小姐,三爺日落就過來了。」守在岸邊的黑屬下走過來,低聲道。
日落?現在七點半了,豈不是說,顧懷修已經等了兩三個小時?
清溪連忙上了船。
挑起厚重的簾子,裏面還有兩扇木板門,清溪手放到門上,竟在輕輕地抖。
就在此時,有人從裏面將門拉開了。
清溪驚愕地仰頭。
對面站著那個穿黑西服的男人,他好像矮了一截,因為清溪看他不用仰得那麼費勁兒了,但他冷峻的臉龐與年前最後一次見面時幾乎沒有變化,凌厲拔的眉峰,冷如深潭的黑眸,蒼鷹似的看著。
腦海里一片空白,清溪忘了那些擔憂,也忘了什麼矜持,慌地別開眼。
「進來吧。」顧懷修側道。
清溪嗯了聲,他站在門左,清溪一邊張地往右看一邊往裏邁步,結果預期的船板並不存在,清溪一腳踩空,整個人就朝里栽了下去。完全出乎意料的反應,冷靜如顧懷修臉上都掠過異,長臂一就將小姑娘摟到了懷裏。
清溪埋在他口,眼淚不爭氣地就下來了,說不清是因為剛剛差點摔了一個大跟頭,還是因為這一晚的所有忐忑。才見面就丟了這麼大的人,也不想起來,就想等眼淚憋回去,不他察覺才好。
「扭到腳了?」顧懷修看著懷裏一聲不吭的姑娘,又瞥了眼後的兩層臺階。
清溪搖搖頭,然後離開他懷,低頭快步往前走,地去眼角最後一點水兒。
船篷四周都鋪著厚厚的簾子,蓬燃著無煙炭,居然很暖和,紅木茶座旁,面對面擺著兩張沙發靠椅,一看就溫暖的那種。清溪在跟自己賭差點摔跟頭的氣,一生氣就忘了平時比較在意的規矩或講究,沒等顧懷修招待,自己就坐下了,低著腦袋假裝看腕錶。
Advertisement
顧懷修見坐穩了,先讓船夫開船,他再走過來,坐在對面。
「去哪兒?」清溪悶悶地問。
「小瀛洲,這邊人多,太吵。」船在晃,顧懷修穩穩地給清溪倒了一碗茶,放到面前。
白瓷蓋碗,棗紅普洱,在和的燈下,那漂亮極了。
清溪自怨的氣消了,茶碗取暖,低聲道:「謝謝,不過我得在九點之前回家,來得及嗎?」
顧懷修:「可以。」
清溪放心了,到男人在看,清溪不自在地端起茶碗,一副要喝茶的模樣。
顧懷修默默地打量孩。才兩個月,好像沒怎麼長高,大概是過年期間不用起早貪黑,臉蛋依稀圓潤了些,白皙瑩潤,比手裏的白瓷碗還細.膩。這次見面,讓顧懷修意外的是的扮相,米白大領下出大紅的旗袍,紅底金鑲邊的領,襯得脖子白如雪,如脂,而且今晚長發全部用簪子束了起來,看起來竟有了幾分人的風韻。
「好像長大了。」顧懷修低聲說。
清溪小臉明顯地紅了起來,剛剛被忘卻的重新佔據了大腦,捧著茶碗,視線從對面他口以下繞了圈再迅速繞回來,語無倫次了:「三爺,三爺約我出來,有事嗎?」
顧懷修剛喝了口茶潤嗓,聞言放下茶碗,淡淡道:「沒事。」
清溪睫微,輕輕地「哦」。
「就是想看看你。」顧懷修又說。
清溪耳垂髮燙,喝茶掩飾。
接下來,兩人就不說話了,顧懷修素來沉默寡言,清溪是不好意思說,顧懷修俯端茶碗,就假裝歪頭觀察船佈局,顧懷修順著的視線看過去,清溪再端茶品用。安靜的船蓬,只聞外面規律的劃水聲。
清溪卻並不覺得無聊。
Advertisement
.
小瀛洲是南湖中的一座島嶼,與柳園隔水相,遊船很快靠岸,清溪跟在顧懷修後往外走時,看看腕錶,差一刻八點。
「小心腳下。」到了門前,顧懷修突然回頭提醒。
清溪頓時又記起自己的丟人事,咬咬,搶先出去了。
結果一出來,眼便是一片黑暗,黑漆漆的小瀛洲,只有湖中心有些亮,月下樹影森森,乍一看很是嚇人。清溪忽然意識到,這是一座湖中孤島,而後的男人,了解一些,但也說不上太悉……
「還有一刻鐘,去亭子看。」顧懷修接過船夫遞來的燈籠,然後轉,自然而然地握住清溪手。
哪有這樣一聲招呼不打就隨便拉手的?
清溪當然要回來。
「路不平,不怕再摔了?」顧懷修平靜地問,彷彿孩說不怕,他就會鬆開。
「不怕。」清溪小聲說,繼續使勁兒。
「走吧。「顧懷修卻沒有鬆手,稍微用力,清溪就被他拽著走了。
清溪試了幾次沒用,也不掙扎了,乖乖地跟他走,燈籠搖搖晃晃,將兩人的影子拉的好長好長,清溪看著地上的影子,腦海里只剩一個想法,被他牽著的左手好暖,右手好涼。清溪裏面的旗袍是短袖,大雖厚,卻不住島上風大寒,右邊小臂有點冷了。
顧懷修走在迎風側,並不知道的況。
就在煙花開始燃放的前一分鐘,兩人進了湖北一座涼亭,亭子位於背風,風吹不到,顧懷修放燈籠的時候,清溪走到北面的人靠上,坐好了,藉著月看腕錶。
「快開始了。」興地說,抬起頭告訴前面的男人。
顧懷修看向。
他的後,突然傳來咻咻的破聲,無數煙花爭先恐後地飛起、綻放,五彩繽紛。
Advertisement
清溪看到了,但分不清,此時此刻驚艷的,究竟是空中的煙花,還是煙花下的男人。
獃獃地著顧懷修。
十六歲的孩,孤零零坐在那兒,修長的大顯得越發小,臉龐被煙花照亮,杏眼像月下最清澈乾淨的兩汪泉水,映照出夜空中的朵朵絢爛,那無法形容的中,彷彿有他的影。
兩人就這麼互相著,直到第一波煙花放完。
周邊重新陷黑暗,只剩一盞燈籠蒙蒙的,清溪低下頭,心跳越來越快了。
顧懷修在邊坐下,見低著腦袋絞手,顧懷修再次將的左手拉了過來。
然而只是十來分鐘沒握,手就涼了。
「冷?」顧懷修皺眉問。
清溪搖頭,但顧懷修不信,鬆開便開始解自己的外套。
清溪在船里就注意到他穿的不多,裏面似乎就一件襯衫,穿大都冷,他若只穿襯衫,還不凍壞了?
「不要,你自己穿。」跳起來,背著手拒絕。
「我不怕冷。」顧懷修追上去,非要給披上。
「我不要!」手臂被他抓住,外套已經披上來了,清溪生氣地扭躲閃,顧懷修就算勉強幫穿上,下一刻清溪便扯下來,重新摔到他上。
煙花又開始放了,看著因為發怒愈發明亮的杏眼,顧懷修只好自己披上。
清溪收了氣焰,坐到人靠上,仰著頭專心賞煙花。
顧懷修往這邊靠,清溪知道,但以為男人又來抓手了,搶先往胳膊上用力準備拒絕,至不能讓顧懷修覺得很願意被他手,可清溪正暗暗防備呢,不期然整個人都被他抬了起來,等清溪回神,居然坐在了顧懷修上!
惱怒:「你……」
「這樣你我都不冷。」顧懷修聲音平和,雙臂收,不容拒絕。
清溪連手都不習慣呢,又怎會乖乖給他這麼親.地抱著,遂一邊著讓他放開,一邊氣呼呼地扭了起來。煙花不知疲倦地燃放,亭中男心思卻都不在空中。顧懷修低頭,看小孫猴似的在他懷裏徒勞掙扎,角帶著難以察覺的笑意,但沒過多久,顧懷修便再次抿了。
「別。」他冷聲說。
清溪一怔,顧懷修什麼時候都是冷的,但剛剛那兩個字裏的冷,不一樣,像是生氣了。
清溪便不敢了,無法否認,自己從來都是怕他的。
顧懷修將往前挪挪,隨後便陷了沉默。
清溪仰頭,就見男人俊臉微揚,在認真地看煙花,五俊,下線條冷,結……
看得神,下突然被人住,作輕地將腦袋往外轉:「看煙花。」
清溪臉如火燒,不知不覺地,忘了兩人現在的姿勢。
.
煙花會持續燃放一小時,但清溪要提前歸家,八點半,顧懷修便帶回了船上。
還是面對面坐著,心卻與來時大不相同,清溪垂著眼簾,小手一下一下地.挲茶碗。
這個小時,過得真快啊。
「你裏面,穿的旗袍?」
他突然開口,清溪下意識了領子,茫然地點頭。
「我看看。」顧懷修看著水潤的杏眼,低聲說。。
猜你喜歡
-
完結572 章

傲嬌總裁狂寵妻
「總裁,夫人找到了!」在哪?「在您的死對頭那……他們……他們什麼?」「他們還有一個孩子。」陸承蕭氣絕,這該死的女人,頂著我陸夫人的頭銜還敢勾搭別的男人,被我抓到你就死定了。葉挽寧,「喂,陸大少,誰說我的孩子是其他男人的。」
82.2萬字8 97646 -
完結7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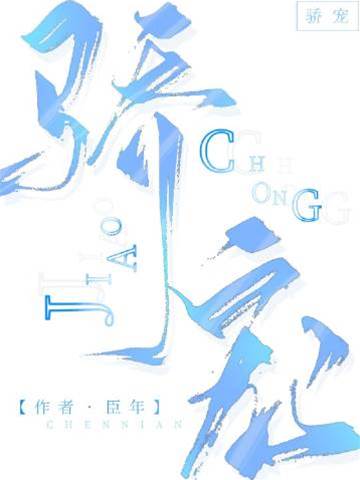
驕寵
作為國家博物館特聘書畫修復師,顧星檀在一次美術展中意外露臉而走紅網絡,她一襲紅裙入鏡,容顏明艷昳麗,慵懶回眸時,神仙美貌顛倒眾生。后來,有媒體采訪到這位神顏女神:擇偶標準是什麼?顧星檀回答:我喜歡桀驁不馴又野又冷小狼狗,最好有紋身,超酷。網…
31.3萬字8 4218 -
完結182 章

驚!禁欲裴總回國后化身寵妻狂魔
【甜寵+雙潔+寵妻狂魔+偏執+爽文+古靈精怪+多CP】[禁欲狼狗總裁VS嬌軟小甜心]被前男友劈腿后,簡今辭酒吧醉酒,錯把京城只手遮天的偏執大佬當成極品鴨王調戲,強吻了他。再次見面,酒會上,她被繼妹算計受傷,偏執大佬不顧賓客眼光,將她橫打抱起送往醫院,繼妹被狠狠打臉,妒火攻心。某天,禁欲大佬誤會她對前男友念念不忘,醋精上身后,以絕對占有的姿勢將她堵在角落強吻她,強勢又霸道。她氣憤被他冤枉,失手甩了他一巴掌后眼眶泛紅,聲音不受控制顫抖:“裴硯舟……你疼不疼啊。”大佬他溫柔拭去她臉頰上的淚,柔聲哄她:“不疼,你手疼不疼?”她越哭越兇,攤開手給他看:“可疼了,手都紅了。”大佬他心疼壞了,低聲哄著:“下次我自己來。”她只知大佬寵她無上限,卻不知大佬有另一個身份,出現在她身邊是蓄謀已久。得知他另一個身份后,簡今辭眼眶泛紅,哭了許久。她漆黑世界的那抹光回來給她撐腰了。 ...
27萬字8 55769 -
完結348 章

深淵蝴蝶
秦佳苒自知和謝琮月是雲泥之別。 他是貴不可攀的頂豪世家繼承人,是光風霽月的謝大公子,宛如高臺明月,是她不能動心思的人。而她,只是秦家最可有可無的存在。 沒人會蠢到認爲這兩人有交集。 當然,亦沒人知道,那輛穩重的勞斯萊斯後座,溫雅貴重的謝公子,也會強勢地握住女人的腰,目光隱忍剋制,低聲問一句: “那麼秦小姐,勾引我是想要什麼。” — 秦佳苒沒有想過自己能成爲摘月之人。和他情到濃時,京城落了雪,她留下一封分手信不告而別。 此事鬧得沸沸揚揚,都傳八風不動的謝大公子中了蠱,爲找一個女人丟了半條命。 出租屋內沒有點燈,男人在黑暗中靜坐,指尖夾煙,一縷火光暈在他雋冷眉眼,聽見樓道傳來腳步聲,他漫不經心擡頭。 開門的剎那,秦佳苒嗅到一縷熟悉的淡茶香,她僵在原地,面色蒼白下去。她知道躲不過。 謝琮月意味不明地笑了一聲,火光晃動,眸色莫名危險。 他慢條斯理靠近,實則咄咄逼人,手指撫上她面頰,聲音沉鬱:“苒苒,就你這點膽兒,怎麼敢玩我?” 秦佳苒很少見過謝琮月情緒外露。 他這樣事事從容的男人也會被她逼急,失控地吻住她,惱羞成怒質問:“從前說喜歡我,是不是都在騙我?” ——謝先生,蝴蝶的翅膀是飛不高的。 ——不用怕,我託着你。
54.1萬字8 7185 -
完結167 章

和佛子閃婚後,被抱進懷裏寵到哭
【女主先婚後愛 男主暗戀成真 前任追妻火葬場 日常甜寵 雙潔】【溫婉美人作曲家vs深情心機商圈權貴】, 南初愛了陸肆九年,卻在領證當天親眼見證陸肆和別人床上調笑:“一個孤女,她不配。”南初輕笑,髒了的垃圾,她不要了。分手拉黑一條龍,她卻陰差陽錯和京圈高冷大佬商凜領了證。世人皆知,商凜薄情寡欲,如禁欲佛子,高不可攀,無人敢染指。南初也不敢,婚後她日日電子木魚,謹守道德底線,力求相敬如賓。直到對她棄之如敝履的陸肆跪求她再給他一次機會,她被稱為薄情寡欲的商先生扼住後頸,困於懷中,男人聲色低微,目光瀲灩,“初初,請要我。”自此,矜貴冷漠佛子的男人,卻在每天夜裏哄著她,抱著她,甚至將她抵在牆角……後來,圈裏都在傳商凜為了南初走下神壇,唯有商凜知道,她才是他的神明,是他瘋魔人生的唯一月亮。
29.7萬字8.18 2883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