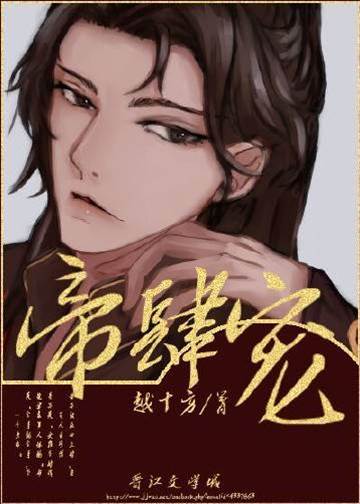《一品村姑》 苦盡甘來終成就好姻緣
二郎家的一聽,指著桌上的一百兩銀子道:「難道這是聘金,想的便宜,小姑子那個模樣兒,一百兩就想娶回家,哪有這樣的好事。」
大郎道:「本來這趟京城咱就不該來,你也別小姑子小姑子的,早就不是棗花了,是四月,當年一張賣契賣給了蘇家,死活不贖的,現如今咱們這樣兒,多有失厚道。」
大郎家的哼了一聲,沒好氣的道:「你倒是個心慈的,家裏兩個小子可都大了,就你們老蘇家哪點兒地,能頂上幾年,以後還得給兒子蓋房娶媳婦,這些銀子不指你妹子,指你能嗎,你要是有那個本事,誰還來這裏瞧人臉。」
大郎被他媳婦二沒頭沒臉的數落一頓,蹲到門邊上生悶氣去了。二郎道:「就算這個王掌柜有的是銀子,也想娶棗花,都給咱送了一百兩銀子,難不咱們還能上門再去要。」
大郎家的道:「二弟怎麼傻了,這銀子收下,趕明兒你跟大郎親自上門說要見見妹夫,見了面把咱家裏的境況一說,銀子倒還還說,讓他幫著咱們也開個鋪子,他的本事大,也開個竹茗軒那樣的茶葉鋪子,讓咱們管著,這錢生錢,比多現銀子不強,這才是個長久生銀子的營生。」
二郎琢磨琢磨大嫂說的在理兒,當初蘇家可是什麼人家,還不是窮的叮噹響,雖說比他們家強些,也不過糊弄個溫飽,再瞧瞧如今,這才幾年啊!家裏金山銀山都賺回來了,別說京城裏的宅子,就是冀州府兗州府那宅子蓋的,從這頭看到那頭,都是氣派的青磚院牆,一進一進的數都數不清,家裏使的家奴都比他們家的吃穿面。
四人又合計了合計,覺得這是條生財的道兒,第二日大郎二郎便登門去了,倒是找到了地兒,可到了門外,就被守門的攔住,上下打量他們一遭道:「往哪兒闖呢,知道這是誰的宅門嗎就瞎撞?去去去,一邊兒去。」
Advertisement
二郎被他幾句話沖的,臉青一陣白一陣的難看:「你別狗眼看人低,我是你們家老爺未過門的舅爺……」
看門的一聽他這話,嗤一聲樂了:「倒是個消息靈的,還知道我們家掌柜的要娶親了,行啊!有點子門道,可惜沒掃聽清楚就來撞騙,我們家未過門的家裏沒人了,就是家裏有人,也跟我們沒屁的干係,當年我們才七八歲的時候,在家裏可了大罪,缺吃喝的,差點沒糟蹋了小命兒,這樣還不樂意養活呢,你說是個什麼人家,連自己親骨親妹子都不管,了人牙子來掂量著,就要賣那腌臢地兒去,不是我們家二姑娘心善,如今還不知道什麼樣兒呢,似這等父母兄弟死絕了才好,跟你們說這些做什麼,趕走,趕走,我們家未來沒什麼兄弟,你們倆再不走,我可去衙差來了,到時把你們弄進衙門,一人打你們二十板子,皮開綻,想走都走不了了。」
大郎有些懼怕,一扯二郎的裳,兩人忙著回去了,他們剛走,王寶財從門裏走了出來,夥計上前道:「真讓掌柜的猜著了,還真找過來了,我就不明白,得了銀子,怎的還不回家好生貓著,跑咱們這兒來找不自在。」
王寶財道:「舉凡這人都過不去一個貪字,如果他們不貪,但能有點兒良心,也不會的跑到京里來。」
看門的道:「既如此,掌柜的怎還給他們一百兩銀子,給了銀子,豈不讓這些人的貪心更不足了。」
王寶財道:「我只是不想落個拿了周家的好銀子,就跟四月就值這一百兩銀子一樣,他們輕賤,我卻不能任由他們輕賤,只是這些人還想從我這裏佔便宜,真正打錯了主意。」
Advertisement
再說大郎二郎回去,跟兩個婆娘一說,兩個婆娘就惱了:「世上哪有這樣的事兒,想白娶了我們家的姑娘不兒,明兒我們去,我就不信了。」
兩個婆娘第二日還真去了,卻也被看門的幾句難聽話給頂了回來,氣的不行,又想進蘇家去尋四月,往日進去到容易,可今日想進去連門二都沒有,守著門的一看們直接往外轟,四個人就這麼回老家去,心裏又實在過不去,這個大便宜擺在前頭,誰也捨不得丟下,索在王寶財的新院子外面守著。
守了十天沒見著人,眼瞅著快出正月了,這日忽然發現裏外進出的都是人,門上也掛了大紅的綢子,雙喜字,大郎家的忙使喚了幾個錢,拉住從府里出來的買菜婆子掃聽。
婆子得了錢,也沒當回事兒,高興的道:「主子挑了明兒的好日子,讓四月姑娘嫁過來呢,府里早就收拾好了,今兒正是過嫁的日子,雖說是個丫頭,可是主子跟前得用又面的大丫頭,比那小戶人家的姑娘都強……」
這裏正說著就見從街一頭吹吹打打的過來一停人,兩人抬著一個個大紅箱籠,蓋子都是打開的,足有十抬,從屋裏的擺設用品到裳首飾,帳子,鞋,一應俱全。
兩個婆娘看著那兩大挑子裳料子和那一箱子上的四套頭面首飾,眼饞的不行,料子可都是正經的蘇綉杭緞,那頭面首飾就更了不得了,一套金的,一套銀的,一套金鑲玉的,一套銀子鑲著寶石的,華燦燦,閃的人眼花。
大郎家的恨道:「這丫頭倒是存了這些己,那幾年來找想要些銀子回去吃飯,竟是一口的沒有,瞧瞧這些嫁妝,隨便一箱子都夠咱們一家子吃上幾年了,可見是個沒良心的,連自己老子娘的死活都不管了,想就這麼嫁了,不,既然不要臉面,索明兒咱們就大鬧一場,一不做二不休,不讓咱們得錢,也甭想著過舒坦日子。」
Advertisement
大郎小聲道:「不然咱別鬧了,這裏畢竟是京城,再說蘇家哪位二姑娘可不是好惹的……」「什麼不是好惹的,說穿了,就一個丫頭片子,有什麼,腳的還怕個穿鞋的,鬧一場,給銀子便罷、不給銀子大家都別想著自在。」
扭回頭再說採薇,這些日子每日都去尚書府陪著鄭心蘭說話兒,兩人本來投契,又結了姐妹,親更是難捨難分,竟彷彿有說不完的話一般加上離別在即,連夜裏也捨不得分開,採薇便在尚書府住下了,住了五六日,實在上的事不開才回了家。
剛到家,王寶財就遣了人來說有事要見二公子,三月似笑非笑的瞧著四月道:「偏偏王掌柜的消息靈通,咱們這前腳剛回府,後腳兒就聽著了信兒,心裏不定多著急的要討媳婦二呢,這麼個一天半日都等不不了了。」
四月一貫沒有三月的頭伶俐,加上這事兒又被三月拿住了話頭,哪裏能應對的出,低著頭攪著手帕子,一張臉直紅到脖頸兒,倒是更顯出姿明艷出挑。
採薇看了一眼,木頭的葯是好,這才幾天,臉上的傷就剩下淺淺的一道,估再有幾日便能潔如初了,怪不得周子聰那病秧子非要謀了去。
說起周子聰,蘇採薇不哼了一聲,以前倒是沒瞧出,這是個有心計的,現在想來這個周子聰也沒存好心眼兒,當年他媳婦做出那樣的事,他們日夜都在一,採薇就不信他不知道,知道了還由著張氏那麼干,可見其心歹毒,從他謀四月的事而來看,說不得當初就是一招借刀殺人之計,心裏膩煩了張氏,又懼怕父母,不敢冷落,因此才順水推舟,這也是個損的男人。
Advertisement
虧得姐姐從周府分了出來,雖說仍算一府,可兩邊院子已經各是各的,且周家那些買賣,採薇早跟周伯升說了,姐這邊一文都不要,如今老人還都在,就這麼過著,趕明兒真到了那一日,連這宅子都不要,另有好的讓們小兩口過去,至於生計銀子,姐夫當不當的都隨他,府里有姐呢。
採薇知道,可著周家就周伯升一個明白人,因此就跟他把話先說在前頭,周伯升前面愧對二兒媳,加上真讓採薇給折騰服了,更知道人家這不是大話,自家那點兒家產放到蘇家眼裏真就不值一提,也就大兒子日算計著,就怕子明仗著老丈人家的勢,奪他的家產。
周伯升如今是真得罪不起蘇採薇,就盼著這姑能管他們家點兒事,可沒想到周子聰還敢謀蘇家的大丫頭。
四月這事兒出來后,蘇採薇直接寫了封信,讓人拿過這邊府里呈給周伯升,周伯升一看,氣的直哆嗦,你說這躲還躲不過來呢,還往上找,臉一沉,讓人了周子聰進來。
周子聰一進來,周伯升看見大兒子那個樣兒,就恨不得上去踹兩腳,以前真沒理會,媳婦一死,他倒放開了,房裏的丫頭抬了房不說,前兒聽說城東的紫雲閣里還包著個青樓子,這個病歪歪的樣兒,估八是從上面來的,尚且不知自己保養,自尊自重著,還要去謀弟媳婦屋裏的人,說出去都讓人脊梁骨,這個沒人倫的東西。
周子聰自來有些怕父親,一見他爹皺起了眉,嚇的在門邊上一不敢,心裏打了幾個主意,難不是四月的事兒他爹知道了,不能啊!這事兒他做的,說起來四月是他弟媳婦跟前的丫頭,跟蘇家有什麼干係。
想到此,便定了定神:「爹您找我來要問什麼事?」「什麼事?」周伯升哼了一聲:「我且問你,四月是怎麼回事」
一提四月,周子聰臉都變了,周伯升一看兒子的臉,就知道這事兒實打實了,一邪火上來,過去就是一腳,把周子聰踹到地上,待要踹第二腳,就被趕過來的周夫人抱住:「老爺,老爺,你這是做什麼啊!聰兒子弱,這才養好了些,你這一腳踹過去,豈不是想要他的命……」
周伯升畢竟年歲不小,加上又生了大氣,這一腳踹過去,第二腳剛抬起來就被周夫人抱住,一個踉蹌坐回到椅子上,指著周夫人道:「你還攔著,你知道他都幹了些什麼,這麼個子,還天想著那些烏七八糟的事,娶了一個,外頭養著一個,跟丫頭也不乾不淨還不足,的又去謀弟媳婦屋裏的人,傳出去,讓我這張老臉往哪兒擱。」
周夫人道:「說下大天來,不過一個丫頭罷了,誰屋裏的有什麼打,那丫頭模樣兒好,子健朗,我瞧著是個能生養的,能給子聰當個三房,更是八輩子想不到好事……」
周夫人話沒說完就被周伯升喝住:「放屁,都是你寵出來的,你還說,那是弟媳婦屋裏的人,就算沒有這一層,那四月說到底是蘇家的丫頭,子契攥在蘇採薇手裏,當年買的就是蘇採薇,這位親家姑娘是好惹的嗎,你忘了子聰媳婦兒的事了,先頭還說放開了,最後還不是找了善緣寺的慧遠大師來,雖說老大家的是自作孽不可活,可這樣的手段誰使喚的出,那就是個吃不得一點兒虧的主兒,又是國公府未過門的孫子媳婦,你去謀的人,你是不想要命了怎的,那最是個護犢子的,邊的人誰了委屈,必然要加倍找回來,更何況,四月跟的分又自不同,早聽說要把四月配給王寶財,別說,就是王寶財可是咱家得罪起的,王寶財說句話兒,咱手裏那些鋪子說不得就得關門了。」
周夫人吶吶的道:「怎麼著,咱們家也是蘇家的親家,他王寶財一個夥計敢怎麼著?」「敢怎麼著?」周伯升道:「你糊塗,蘇家誰掌著,不還是蘇採薇,蘇採薇手裏第一得用的人就是王寶財,他管著蘇家大小上幾十家鋪子,你以為是白管的,說是夥計,別說你,就是那些三四品的大,見著他也得客氣幾句,親家?蘇善長現在還記得明薇的事兒呢,過年時去他府上吃酒,還說,依著,就不讓明薇在咱家了,說從小就是窮到時候,也沒過什麼委屈,哪想到嫁人了差點連小命都丟了,說的我上不了下不去的。」
猜你喜歡
-
連載3575 章

錦鯉棄婦:隨身空間養萌娃
一覺醒來,安玖月穿成了帶著兩個拖油瓶的山野棄婦,頭上摔出個血窟窿。米袋裡只剩一把米;每天靠挖野菜裹腹;孩子餓得皮包骨頭;這還不算,竟還有極品惡婦騙她賣兒子,不賣就要上手搶!安玖月深吸一口氣,伸出魔爪,暴揍一頓丟出門,再來砍刀侍候!沒米沒菜也不怕,咱有空間在手,糧食還不只需勾勾手?且看她一手空間學識無限,一手醫毒功夫不減,掙錢養娃兩不誤!至於那個某某前夫……某王爺邪痞一笑:愛妃且息怒,咱可不是前夫,是『錢』夫。
322.4萬字8.08 312731 -
完結8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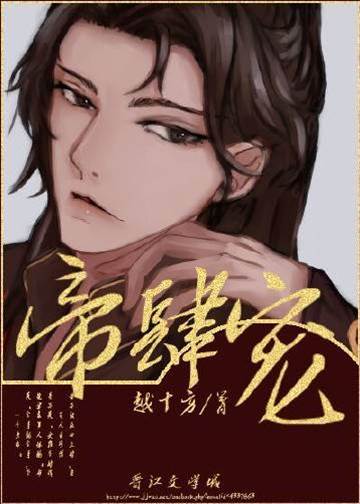
帝肆寵(臣妻)
從軍六年渺無音訊的夫君霍岐突然回來了,還從無名小卒一躍成為戰功赫赫的開國將軍。姜肆以為自己終于苦盡甘來,帶著孩子隨他入京。到了京城才知道,將軍府上已有一位將軍夫人。將軍夫人溫良淑婉,戰場上救了霍岐一命,還是當今尚書府的千金,與現在的霍岐正當…
28.8萬字8 26490 -
完結451 章

歡恬喜嫁
前麵七世,徐玉見都走了同一條路。這一次,她想試試另一條路。活了七世,成了七次親,卻從來沒洞過房的徐玉見又重生了!後來,她怎麼都沒想明白,難道她這八世為人,就是為了遇到這麼一個二痞子?這是一個嫁不到對的人,一言不合就重生的故事。
81.3萬字8 15677 -
完結532 章
醫庶無雙
原主唐夢是相爺府中最不受待見的庶女,即便是嫁了個王爺也難逃守活寡的生活,這一輩子唐夢註定是個被隨意捨棄的棋子,哪有人會在意她的生死冷暖。 可這幅身體里忽然注入了一個新的靈魂……一切怎麼大變樣了?相爺求女? 王爺追妻?就連陰狠的大娘都......乖乖跪了?這事兒有貓膩!
103.5萬字8 19342 -
完結206 章

賠罪
施綿九歲那年,小疊池來了個桀驁不馴的少年,第一次碰面就把她的救命藥打翻了。 爲了賠罪,少年成了施綿的跟班,做牛做馬。 一賠六年,兩人成了親。 施綿在小疊池養病到十六歲,時值宮中皇子選妃,被接回了家。 中秋宮宴,施綿跟在最後面,低着頭努力做個最不起眼的姑娘,可偏偏有人朝她撞了過來,扯掉了她腰間的白玉銀環禁步。 祖母面色大變,推着她跪下賠禮。 施綿踉蹌了一下,被人扶住,頭頂有人道:“你這小姑娘,怎麼弱不禁風的?” 施綿愕然,這聲音,怎麼這樣像那個與她拜堂第二日就不見蹤影的夫婿?
33.9萬字8.18 408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