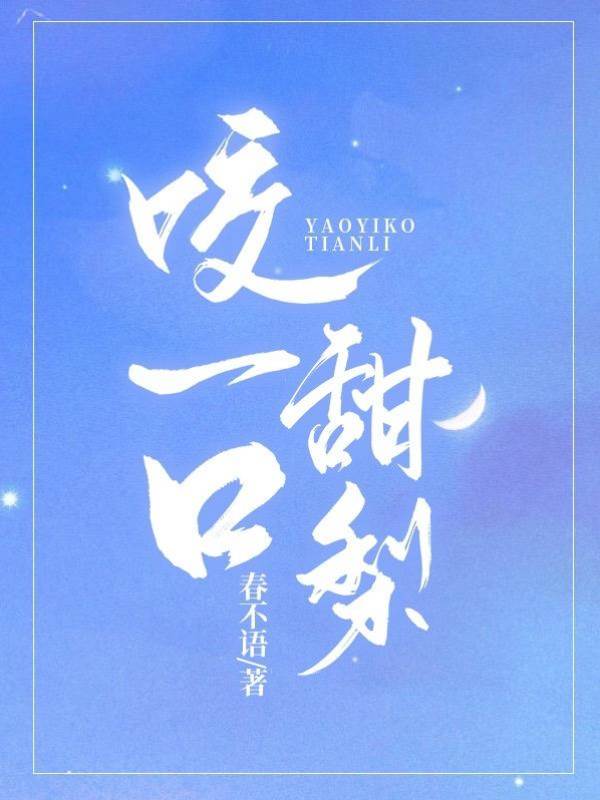《夢斷幽閣》 第272章 巧兒告夫
林濤果然想起了一件事,他說曾見林子輝寫過一個賬本,雖然不知賬本寫的什麼容,但是林子輝十分在意這賬本,并曾見他將其放在一個匣子里,就收在書房中,而且,林濤殺死王允后拿回來的那些金銀首飾也應該在他書房中,他的書房從來不準人進去,即便大夫人要進去也得在他允許后方可進。
既如此,柳奕之下令,搜查林子輝的家,務必要搜出些有用的東西來。
……
士兵和捕快同時出搜查林家,余氏坐地嚎啕大哭,鬧了個飛狗跳,仔細搜了一番,除了從臥室搜出一小盒余氏的首飾,并不見其他有價值的東西。
將那搜出的首飾給林濤查看,林濤搖頭說這些并非當時自己從王允拿回的東西。
看來此行是無功而返了。
而此刻余氏卻又鬧上衙門來,在門前哭了個昏天黑地,好在州府衙門與節度使治所鄰,此間百姓極,偶有路人被吸引過去,但見衙役和士兵皆立于門外,倒也不敢靠近,遠遠看看便匆匆離去了。
柳奕之大發雷霆,下令,若余氏再敢大鬧府衙,即刻抓捕,余氏再擔心林子輝也終是害怕府真把抓了,只得噎噎訕訕而去。
就在余氏走后不久,府衙外突然傳來陣陣擊鼓聲。
全哲問道:“門外何人擊鼓?”
衙役報:“大人,是一名年輕子。”
全哲微微蹙眉,“又是子?什麼名字?”
衙役道:“回老爺話,說姚巧兒,是林子輝的小妾。”
柳奕之啼笑皆非道:“嘿,沒想到這林子輝的妻妾對他還真不錯啊,大夫人剛鬧過走了,這小妾又打上門來了,居然還擊鼓,讓老夫打仗可以,可一見到這些人實在頭疼啊。”
Advertisement
全哲苦笑道:“頭疼的還有我這個知州大人呢。”
肖寒笑道:“前面那個是哭鬧,這一個倒是換了個方式,看來是有什麼話想說了,全大人,柳將軍,咱們不妨聽聽?”
全哲對衙役道:“那就帶進來吧。”
“是。”
須臾,進來一名子,但見不過二十出頭,長眉杏目,五清秀,只是雙頰略有些浮腫,額上纏著一圈紗布,量纖瘦,弱不風,高挽的烏發上斜一枚素銀簪,一玄青衫,看上去最是簡樸不過。
一見此,眾人實在難以將和林子輝小妾的份放在一起,單看大夫人余氏那養出的一,和滿頭珠釵,再看這子的憔悴和素樸,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子在堂中跪下,垂首施大禮:“民姚巧兒見過三位大人。”沙啞的嗓音中帶著一惶恐的抖。
全哲問道:“堂下何人,報上名來。”
“大人,民姚巧兒,是林子輝的妾室。”
“為何擊鼓?”
姚巧兒雙手無措地攥著自己的襟角,怯怯地說道:
“民、民要、要告狀。”
全哲問道:“姚巧兒,你狀告何人?”
姚巧兒垂首低聲道:“民要告,要告醫林、林子輝。”
聽得此言,三人皆大為震驚,全哲問道:“你,你說什麼?你告誰?你再說一遍!”
恐是全哲大驚之下聲音響了些,姚巧兒嚇的一哆嗦,頭垂的更低了。
柳奕之見甚為惶恐的樣子,忙溫言道:“姚巧兒,你別害怕,既然來到這里,有什麼話你盡管說,本將軍和全大人會為你做主。”
他抬手一指堂下坐著的肖寒,道:“你知道他是誰嗎?他可是當朝神龍軍統帥肖將軍,當朝二品大員,你有話且放心大膽的說出來,無人敢為難于你。”
Advertisement
聽得此言,那姚巧兒看向肖寒,見他向自己投來鼓勵的眼神,剎時仿佛有了主心骨一般,昂起頭來,深吸一口氣,高聲道:
“民要告醫林子輝。”
全哲道:“本問你,你既是林子輝妾室,為何要狀告自己的相公?”
姚巧兒沉默片刻,一雙布滿的雙眸騰然潤起來,開口道:“回大人話,民本是祥州一家梨園的角兒,三年前,林子輝去看堂會,我二人便認得了,那時,他對民花言巧語百般疼,說要娶我回家。原本民也顧忌他家中有個兇悍的妻子,故此雖念他的一片癡,卻也遲遲未曾應了他,直到半年前,他又提出要娶我,民見他對我多年來一直不離不棄一片真心,這才嫁給了他,并心甘愿做他的妾室,可是,萬萬沒想到的是,自從進了他家的門,他就變了臉,他與大夫人對民百般折磨,民盡凌辱,苦不堪言。”
說到此,將額上紗布解下,出一塊銅錢大的剛剛結起的新鮮疤痕,道:
“這是他將我的頭撞在柱子上留下的,我這臉上,不需多言,大人們也能看出來,是被他打的。”
又出自己那只左手來,那曾經折斷了,又被他復位的小手指,如今尚且紅腫著,顯然是新傷。
哽咽道:“這手指是被他生生掰折的。”
再挽起袖,手臂上皆為片片青紫,道:“這是他和大夫人打的。”
這些傷痕直看的柳奕之倒吸一口冷氣。震怒之下拍案道:“林子輝!居然對一個弱小子下如此狠手,與畜生又有何異?!”
姚巧兒垂淚道:“民素來膽小怯弱,不敢與相公和大夫人對抗,只能自己忍著。”
Advertisement
全哲強忍怒氣,盡可能讓自己的聲音溫和一些,道:“姚巧兒,既如此,我等便明白了,今日你狀告相公林子輝,告他什麼?”
姚巧兒抹了淚,緩緩直脊背,道:“醫林子輝與人勾結,倒賣藥材,以假真,以次充好,收賄賂,謀害人命,指使他人火燒軍庫。”
“什麼?”
柳奕之怔然,全哲怔然。
肖寒盯著姚巧兒,溫言道:“姑娘,起來說話。”
“多謝大人。”姚巧兒踉蹌地站起來。
肖寒道:“林子輝都做了些什麼,別怕,把你知道的都說出來吧。”
姚巧兒額首道:“是,大人。”
深吸了一口氣,說道:“林子輝的書房從來不讓人進去,尤其是他不在的時候,可是一日,大夫人找借口讓民去書房研磨,當時相公又不在家,為何要我研磨?民明知又想故意設計陷害我,可是卻不敢不聽的,就著頭皮進去了,我卻在無意中看見他桌上有一個冊子,就隨手翻看了一下,發現,居然是一個賬本……”
“賬本?”全哲心中一,問道:“可知里面容?”
姚巧兒道:“民不敢多看,只是草草瞟了一眼,上面似乎都是些藥材名,還有王允和錢大人的名字,還有注明的銀兩金額。”
柳奕之振道:“果然有這個賬本,看來必是分贓的賬本了。”
姚巧兒又道“當時我雖看見了卻絕對不敢說出去的,后來大夫人果然向林子輝告了狀,林子輝對我大打出手,我這手指便是那時被他掰斷的,我知道他是怕我看到賬本,我騙他說我不認字,他才沒有繼續追究。”
全哲狐疑道:“你們是夫妻,你認不認字他難道不知道?”
Advertisement
姚巧兒道:“大人有所不知,民本是認得幾個字的,雖然不多,只是在梨園時,師傅說子無才便是德,所以梨園子大都會說自己不識字。若非如此,他又怎會輕易放過我呢。”
全哲點頭。
姚巧兒道:“今日民也瞧見捕快去搜了書房,可如今這賬本早已不在書房,不過,民知道在哪里,待民把話說完,自會告知大人。”
全哲面喜,道:“好,你繼續講來。”
姚巧兒道:“前些日子的一個晚間,我見王允來到家中,他與林子輝去了書房談了許久,出來時懷中抱著一個盒子,匆匆地走了。隨后阿濤進了書房,我便在書房外聽,聽他與阿濤謀要火燒庫房和殺王允,我嚇壞了,怕他們發現,就趕回了房,一個時辰后,我就聽到庫房走水的消息。而第二日再有消息傳來便是……王允死了。”
“就在前兩日,晚間下雨,林子輝冒雨回了家,將下的服丟給我洗,民見他服上不僅有泥水,還有跡,便將服藏了起來,如今這衫便在民房中。隨后第二日就聽說阿濤也死了。這還用說嘛,殺人滅口,必是他所為。”
柳奕之問道:“姚巧兒,本將軍問你,你可知錢大人去你家?”
姚巧兒回道:“回大人話,這錢大人是昨日傍晚去的家中,是林子輝和大夫人作陪,民并不在側,只是,民因在賬本上見過錢大人的名字,故此心下留意,他們用過晚飯后便在書房說話,民不敢靠近,雖不知他們說了什麼,但是那個錢大人臨行前,在走出書房后對林子輝說了一句話……”
“什麼話?”柳奕之急問道。
“他說:記住,最近不要有任何舉,以免被懷疑,無論他們問什麼都要抵死不認,我回去自會跟大人匯報,一切都待風聲過去再說吧。”
全哲沉:“‘大人’?可知他口中的‘大人’是誰?”
姚巧兒搖了搖頭,道:“不知。”
“幾日前,林子輝和大夫人一同將那個裝著賬本的盒子埋在了院子東側墻腳下,上面著一塊石頭的便是。他殺阿濤時穿的那件沾了跡的服在西側我房中的床下。”
肖寒長長吐出一口氣,道:“看來,假藥一事林子輝的大夫人定然知。”
柳奕之道:“將軍的意思是,抓捕余氏?”
全哲拍案道:“我看可行,那余氏仗著表兄是錢崇蜀,從不將咱們放在眼里,如今看來,假藥案亦是知者,既是知者便是同謀,抓前來問詢并不為過。”
柳奕之頷首道:“既如此,那便抓吧。”
面對這個意料之外的收獲,全哲當機立斷,向捕頭下令,即刻抓捕余氏,挖地三尺,取出相關證。
猜你喜歡
-
連載223 章

總裁追婚記:嬌妻哪裏逃
三年前,初入職場的實習生徐揚青帶著全世界的光芒跌跌撞撞的闖進傅司白的世界。 “別動!再動把你從這兒扔下去!”從此威脅恐嚇是家常便飯。 消失三年,當徐揚青再次出現時,傅司白不顧一切的將她禁錮在身邊,再也不能失去她。 “敢碰我我傅司白的女人還想活著走出這道門?”從此眼裏隻有她一人。 “我沒關係啊,再說不是還有你在嘛~” “真乖,不愧是我的女人!”
29.6萬字8 5229 -
完結1939 章

替嫁后我被大佬纏上了
所有人都說,戰家大少爺是個死過三個老婆、還慘遭毀容的無能變態……喬希希看了一眼身旁長相極其俊美、馬甲一大籮筐的腹黑男人,“戰梟寒,你到底還有多少事瞞著我?”某男聞言,撲通一聲就跪在了搓衣板上,小聲嚶嚶,“老婆,跪到晚上可不可以進房?”
290萬字8.18 188936 -
完結1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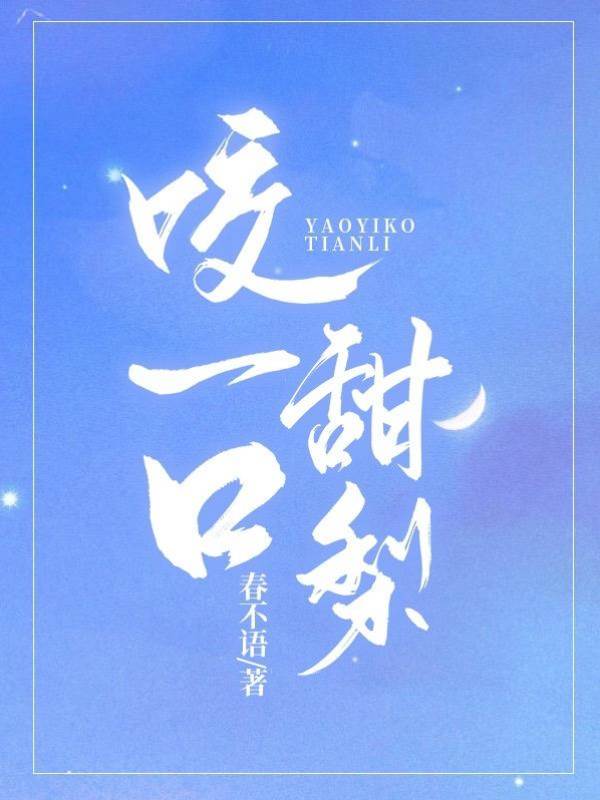
咬一口甜梨
白切黑清冷醫生vs小心機甜妹,很甜無虐。楚淵第一次見寄養在他家的阮梨是在醫院,弱柳扶風的病美人,豔若桃李,驚為天人。她眸裏水光盈盈,蔥蔥玉指拽著他的衣服,“楚醫生,我怕痛,你輕點。”第二次是在楚家桃園裏,桃花樹下,他被一隻貓抓傷了脖子。阮梨一身旗袍,黛眉朱唇,身段玲瓏,她手輕碰他的脖子,“哥哥,你疼不疼?”楚淵眉目深深沉,不見情緒,對她的接近毫無反應,近乎冷漠。-人人皆知,楚淵這位醫學界天才素有天仙之稱,他溫潤如玉,君子如蘭,多少女人愛慕,卻從不敢靠近,在他眼裏亦隻有病人,沒有女人。阮梨煞費苦心抱上大佬大腿,成為他的寶貝‘妹妹’。不料,男人溫潤如玉的皮囊下是一頭腹黑狡猾的狼。楚淵抱住她,薄唇碰到她的耳垂,似是撩撥:“想要談戀愛可以,但隻能跟我談。”-梨,多汁,清甜,嚐一口,食髓知味。既許一人以偏愛,願盡餘生之慷慨。
20.2萬字8 7738 -
連載256 章

全球通緝令,抓捕孕期逃跑小夫人
曾經顏琪以爲自己的幸福是從小一起長大的青梅竹馬。 後來才知道所有承諾都虛無縹緲。 放棄青梅竹馬,準備帶着孩子相依爲命的顏鹿被孩子親生父親找上門。 本想帶球逃跑,誰知飛機不能坐,高鐵站不能進? 本以爲的協議結婚,竟成了嬌寵一生。
45.2萬字8 458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