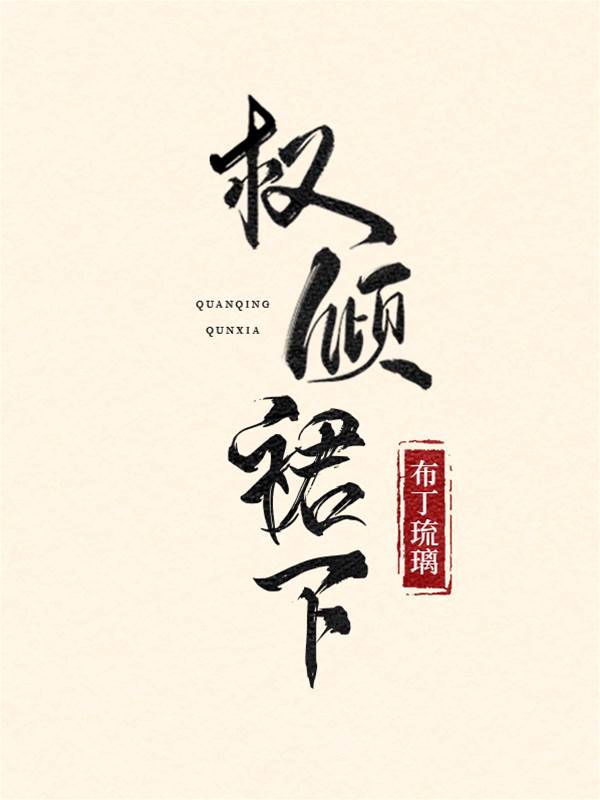《嬌靨》 第 112 章 112章的太子殿下
熊熊烈火照亮夜空,像巨蟒張著盆大口,濃煙和火苗徹底吞噬第一闕。
無數寺人與奴隨來來往往,慌地將一桶桶河水往前潑,家令心急如麻,一邊跺腳嘆氣一邊指揮侍衛們救火。
“一定要火勢蔓延前將火撲滅!絕不能讓火燒到別去!”家令嗓子都喊啞。
他又驚又怕,生怕這火停不下來,搶過旁邊寺人手里的水桶,加撲火的隊伍中。
第一闕燒沒了不要,就是再燒上十個第一闕,他也不會心疼,要的是趕將火勢止住,避免這火燒了別的宮殿。家令想起更要的事,他憤憤地瞪向角落里的四個狼狽影。
好端端地,第一闕怎會走水!
龐桃赤著腳披頭散發,臉上滿是煙污,佝僂著背,學越一般,做出驚慌失措瑟瑟發抖的模樣。在的左側不遠,兩個人抱在一起,哭得淚流滿面,和不同,們臉上的恐懼是真實的。
們與死亡肩而過。若是被人喚起來的時間晚那麼一點點,們就將葬火海。
“沒事了,沒事了。”孫氏抖地拍著翡姬的背。逃出來時為替翡姬擋火,的頭發被燒焦,脖子上也被燒出傷痕來,痛得已經沒有知覺,此時此刻兩眼空,被嚇得六神無主,卻還是下意識將翡姬護在懷里。
翡姬抓著的角哭得泣不聲:“姐姐,我好害怕。”
孫氏呆傻地重復拍背的作:“不怕,有姐姐在,姐姐不會讓你有事。”
龐桃心中涌起奇怪的覺,這一刻,忽然不再嫌棄孫氏和翡姬,可依然不后悔放火時沒有喚醒們的事。
風一吹,有些冷,想往越秀邊靠,卻又不敢。
越秀讓放火后將孫氏和翡姬醒來,沒有照做。等大火燒起來,才發現,原來越秀早就料到不會去喚人,所以越秀自己去了。
Advertisement
龐桃手臂被猛地一掐,回過神,越秀的手已上的臉。
龐桃做賊心虛,聲音抖:“公主……”
越秀悄聲:“知道我怎麼對付不聽話的人嗎?”用兩個人才能聽到的聲音,笑聲嘶嘶著寒意,一字一字:“我會將他們剖腹挖心,碎尸萬段。”
龐桃打個寒:“我不是故意的,公主,我真的不是故意的,饒過我這一回。”
越秀指腹緩緩挲龐桃側頰,龐桃高出一截,此刻卻彎著腰低著腦袋,順從地低到掌心。
這樣的臣服對于越秀而言,早已是司空見慣,的臉上沒有一一毫的,眉眼滿是冷漠:“你怎麼這麼蠢,連撒謊都不會?”
龐桃后背發寒,不敢再狡辯:“因為我不想救們,公主為何要救們,又為何在意們?”
越秀一掌扇過去,人群皆被大火吸引目,無人注意到這一掌。
越秀自己的手心,語氣輕描淡寫:“誰告訴你我在乎們的命?我只是不想做個壞人。”
龐桃捂著臉,眼淚簌簌。
越秀嘖一聲,重新捧過龐桃的臉,替淚:“桃兒,你也要做個好人才行。”
龐桃委屈至極:“什麼是好人?”
越秀指尖點點龐桃的淚,將淚沾到自己齒間:“不隨便殺人的人,就是好人。”
夜蒼涼,火舌竄竄,一團的人群忽然靜下來。前方不遠,一輛青銅大蓋軺車停下,車上的人如天神般降落,眾人看到他的那瞬間,混焦急的心瞬時安定下來。
“殿下。”眾人齊齊跪下去。
越秀出得償所愿的笑容,側頭對龐桃用語道:“瞧,他來了。”
寂靜奢華的大室。
姬稷坐于幾案后,他俊秀的眉眼此刻冷得像冰,目凜然,緩緩掃過對面人的臉龐。
Advertisement
人并不安分,東張西,面上做出虛偽的天真,里道:“原來這就是殿下的建章宮,真是華麗大氣。”
姬稷:“是嗎?既然公主喜歡,那就多瞧幾眼,以后可沒機會瞧了。”
越秀嗔笑:“殿下是在告訴我,這是我第一次進建章宮,也是最后第一次進建章宮嗎?”
姬稷聲音淡漠:“不然呢?公主來一次就夠,何必再來第二次。”
越秀故作態,委屈,以袖遮面小聲啜泣:“我來帝臺三年半,無時無刻不盼著與殿下見面,無奈殿下早已忘阿秀,阿秀日日苦等,終于等來了殿下,雖然今日險些喪命,但能夠與殿下相見,殿下的建章宮,和殿下獨相談,阿秀死而無憾。”
姬稷面容波瀾不驚,深沉的眼眸無無緒:“公主無需做戲,你裝得累,孤也看得累。”
越秀從袖子后抬起臉,臉上仍掛著兩行淚痕,眼睛卻笑起來:“殿下真是無,連這點耐心都不肯給阿秀,殿下對趙姬,也是這般不解風嗎?”
姬稷眼神變得更為銳利寒戾:“收起你的那套,這里不是楚王宮,更不是齊王宮。”
越秀捂笑兩聲:“殿下果真直爽。”
姬稷打量面前的人。
越秀這個名字,從他搬回云澤臺時,便記下了。越秀一個人,即可抵過第一闕所有人。對于這種名聲在外的人,他向來是不吝于給舞臺施展本事的,可這個舞臺不該是云澤臺,而上的銳氣也該挫一挫。
一把好劍,得有主人,方能殺敵無數。
倘若不懂得聽從二字,他不介意再用另一個三年半的時間打磨,如果仍是不肯降,那他也不介意將就地掩埋。一把不識好歹的劍,再如何銳利無比,派不上用場,與廢鐵無異。
Advertisement
姬稷審視的目落在越秀臉上,越秀假裝看不懂他眼中的衡量與算計,伏下-,嗓音響亮,道:“我有良策,愿獻于殿下。”
姬稷:“哦?是何良策?”
越秀:“殿下加冠在即,屆時定有人爭先恐后為殿下送上太子妃,與其選別人,不如選我,我自請為殿下的太子妃,殿下恩準。”
姬稷:“公主真是幽默。”
越秀伏在地上,腦袋微微仰起,笑著看他,眨眨眼:“殿下難道不想找人做趙姬的擋箭牌嗎?趙姬恩寵太盛,遲早有人對下手,殿下護得了一時,但能護一世嗎?但凡一個不小心,趙姬便死無葬之地。”
言辭懇切,語氣真誠:“讓我代替趙姬做那顆眼中釘吧!趙姬討人喜歡,殿下喜,我也喜,我若做了太子妃,殿下大可放心寵趙姬,再無后顧之憂。”
“公主義舉,孤甚是。”姬稷嘆口氣,“照公主所說,孤娶了公主以后,是不是應該在人前冷落趙姬,假裝寵公主?”
“殿下若是愿意,再好不過。趙姬風頭太盛,并非好事,我愿意替趙姬這份罪。”越秀聲音清脆。
“公主既然明白樹大招風這個道理,為何在諸侯國時不曾藏鋒斂銳,反而出盡風頭橫行霸道?難道那些諸侯國的太子國君,也有許多心的寵姬要護,公主為護別人的寵姬,不得不囂張跋扈?”
越秀睜眼說瞎話:“殿下聰慧,確實如此。”
“那公主可真是命大,做了那麼多次擋箭牌,竟能安然無恙全而退。”
“阿秀心誠,日日拜神,神明庇佑,阿秀方能屢次險。”
姬稷沒耐心陪演下去,他語氣陡然一轉,冷冷穿:“一個權者,寵另一個人以此保護他心的人,那他不是生來癡傻就是傀儡懦夫。孤不是傻子也不是懦夫,孤是大殷的帝太子,孤的寵,就象征著權力,趙姬越是風,手里握著的權力就越多,一個高高在上手握大權的子和一個不寵被人冷落的子,公主覺得,誰能活得更長久些?”
Advertisement
越秀沒有回答,道:“可趙姬自己未必立得起來。”
“這個不勞公主心,孤會替趙姬立起來。”姬稷冷笑一聲,忽然有些生氣。
這個越秀竟敢小瞧他,竟敢懷疑他護不住他的枝枝。他殺過的人不算,不是每個人他都能記住,但沖枝枝下手的人,他記得清清楚楚。越秀該慶幸,沒有起過暗害枝枝的心,不然就沖做過的那些事,死一百次都不夠。
姬稷收回視線,略為失:“還以為公主大費周章與孤見面是為何事,原來是為這等無關要的小事,公主回去吧,孤不需要你做孤的太子妃。”
越秀直起腰,目放肆大膽地盯住姬稷,不再做戲,不再偽裝,冷聲冷氣道:“殿下難道不問問,我為何要縱火燒了第一闕嗎?”
姬稷興致缺缺。聽到第一闕起火時,他便猜到火是誰放的。除了越秀,再無別人。
越秀熬不住了。若不是孤注一擲,他不會去第一闕見,更不會讓進建章宮。
姬稷敷衍:“哦。”
越秀對他的不以為然甚是惱怒,可這惱怒僅僅只是存在一瞬便消失不見。從始至終,都清楚自己被他玩弄鼓掌指間不是嗎?他將困在第一闕,不放出去,又不理會,任由一個人折騰,只要的那些小把戲與他心的趙姬無關,哪怕鬧出人命來,他亦不曾搭理。
過去的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在這個年輕的帝太子面前,一風都刮不起一滴雨都下不了,他遠遠掛在天上,連一個眼神都不給,就連要與他單獨見上一面,都要用縱火的方式才能博得他的注意。
想過利用趙姬,可不敢冒險。從楚國帶來的宮人都死了。每往井外跳一次,邊的死尸變多一。他知道,什麼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當然了,是不會求死的,只會向生。
越秀挪著雙膝往前,每往前一步,上的外便一件:“我不想再被殿下關在云澤臺,所以才要燒了第一闕。”
姬稷皺眉:“穿好你的裳,孤對你的沒有興趣。”
越秀停下作:“殿下不就是想我投降嗎?我降了便是。”再次伏下去:“殿下說吧,要怎樣才肯放過我?”
姬稷終于聽到想聽的話,半刻沉默,他慢條斯理道:“既然公主已經說破,那孤就直言不諱了。”
越秀:“但憑殿下吩咐。”
姬稷:“以你的本領,留在云澤臺,大材小用,實在可惜。過去你做過的事,再做一次吧。這一次,結局會不一樣。”
越秀:“哪里不一樣?”
姬稷出案上的劍,他執劍起,燈下的影如山一般,氣勢沉沉,冷肅威嚴。
冰冷的劍抵住越秀下,被迫仰起脖子,姬稷第一次瞧清的臉,他挑眉笑了笑。
越秀下意識后。
很久沒害怕過了,這是十年里的頭一回。
越秀垂了視線,姬稷沒再看。他手里作一變,劍從的下移開,轉而到手里。
他以高位者不容置疑的語氣告訴:“這一次,你會得到你想要的,殷王室會替你的母國報仇雪恨。”
猜你喜歡
-
完結307 章

妃揚跋扈:重生嫡女好妖嬈
上一世鳳命加身,本是榮華一生,不料心愛之人登基之日,卻是自己命喪之時,終是癡心錯付。 重活一世,不再心慈手軟,大權在握,與太子殿下長命百歲,歲歲長相見。 某男:你等我他日半壁江山作聘禮,十裡紅妝,念念……給我生個兒子可好?
56.5萬字8 7103 -
完結201 章

逆天嬌妃:皇上把持不住
宋微景來自二十一世紀,一個偶然的機會,她來到一個在歷史上完全不存在的時代。穿越到丞相府的嫡女身上,可是司徒景的一縷余魂猶在。
52.1萬字8 27669 -
完結148 章

丞相重生后只想擺爛
柳枕清是大周朝歷史上臭名昭著的權臣。傳聞他心狠手辣,禍亂朝綱,拿小皇帝當傀儡,有不臣之心。然老天有眼,最終柳枕清被一箭穿心,慘死龍庭之上。沒人算得清他到底做了多少孽,只知道哪怕死后也有苦主夜半挖開他的墳墓,將其挫骨揚灰。死后,柳枕清反思自己…
57.7萬字8 9535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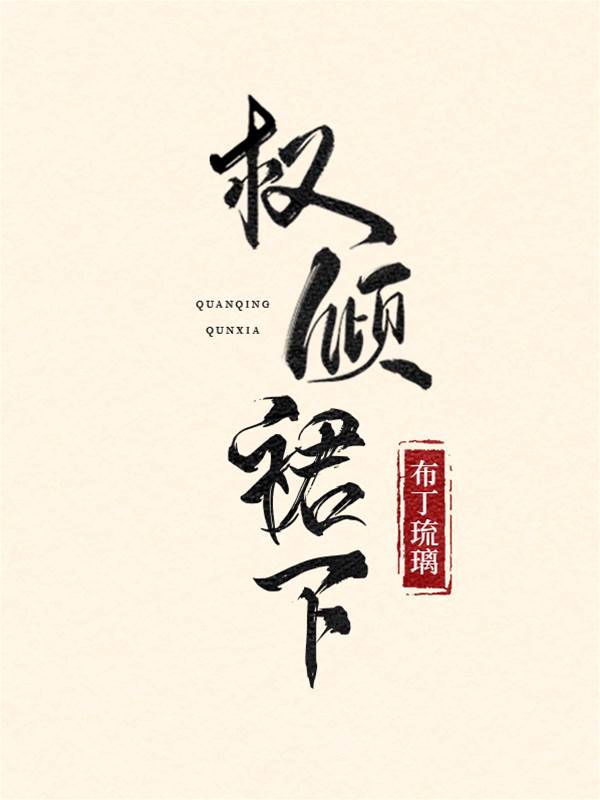
權傾裙下
太子死了,大玄朝絕了後。叛軍兵臨城下。為了穩住局勢,查清孿生兄長的死因,長風公主趙嫣不得不換上男裝,扮起了迎風咯血的東宮太子。入東宮的那夜,皇后萬般叮囑:“肅王身為本朝唯一一位異姓王,把控朝野多年、擁兵自重,其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聽得趙嫣將馬甲捂了又捂,日日如履薄冰。直到某日,趙嫣遭人暗算。醒來後一片荒唐,而那位權傾天下的肅王殿下,正披髮散衣在側,俊美微挑的眼睛慵懶而又危險。完了!趙嫣腦子一片空白,轉身就跑。下一刻,衣帶被勾住。肅王嗤了聲,嗓音染上不悅:“這就跑,不好吧?”“小太子”墨髮披散,白著臉磕巴道:“我……我去閱奏摺。”“好啊。”男人不急不緩地勾著她的髮絲,低啞道,“殿下閱奏摺,臣閱殿下。” 世人皆道天生反骨、桀驁不馴的肅王殿下轉了性,不搞事不造反,卻迷上了輔佐太子。日日留宿東宮不說,還與太子同榻抵足而眠。誰料一朝事發,東宮太子竟然是女兒身,女扮男裝為禍朝綱。滿朝嘩然,眾人皆猜想肅王會抓住這個機會,推翻帝權取而代之。卻不料朝堂問審,一身玄黑大氅的肅王當著文武百官的面俯身垂首,伸臂搭住少女纖細的指尖。“別怕,朝前走。”他嗓音肅殺而又可靠,淡淡道,“人若妄議,臣便殺了那人;天若阻攔,臣便反了這天。”
52.5萬字8 2219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