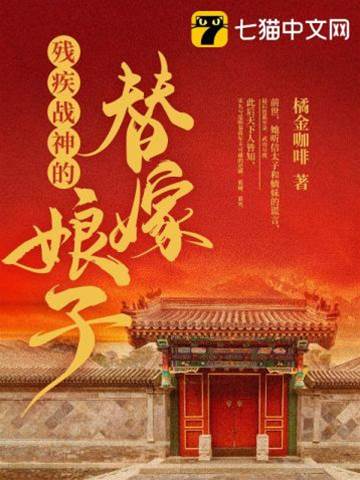《嬌靨》 第 71 章 雙更合并
這一夜,趙枝枝沒有睡覺。
盯著太子看了一夜,太子睡得很沉,他累了,親他好幾下,他都沒有醒來。
趙枝枝雖然徹夜未眠,但是第二天興得就像一頭牛,渾上下全是勁。
小牛一般的趙枝枝喊起人中氣十足,一聲聲“殿下”喊出口,震得姬稷耳朵疼。
屋外白霧籠著窗戶,蝦青的天空尚未見晨暉。趙枝枝自告勇為姬稷梳發。這是第一次睡得比姬稷晚,起得比姬稷早——因為沒睡。打算以后都這樣,做一個早起的趙姬,送殿下出門辦公。
趙枝枝盯著姬稷的后腦勺,象牙梳一下下梳著他的頭發,在心里想,殿下的頭發真是又黑又,但不會嫌棄的,就算他的頭發很難理順,也會天天為他梳發,因為擁有一頭黑長發的殿下,是的殿下,是的男人。
他不再是的主人了,總算明白他之前對說過的那句“趙姬不必有主人”是什麼意思。
趙枝枝梳著梳著親了親姬稷的頭發,姬稷怪:“作甚。”
趙枝枝寶貝地捧起他的頭發,往下梳了梳:“趙姬喜歡殿下的頭發。”
姬稷頂著被梳痛的頭皮,掩住角因為被梳子扯疼的猙獰:“喜歡也不能親,知道孤幾天沒洗頭了嗎?臟不死你。”
趙枝枝嗅了嗅:“好像是有一點臭。”
姬稷立馬甩過自己的長發捧起一聞:“臭嗎?三天沒洗而已,真的發臭了嗎?”
趙枝枝趴到他背上抱住他:“趙姬騙殿下的,殿下的頭發和趙姬的一樣香。”
“小騙子。”姬稷抖了抖雙肩,將抖下去。他仍是在意他的頭發,讓人去取香。香覆在腦袋上,奴隨們小心翼翼地吹,白白細細的末從頭發上吹開,轉瞬消失不見。
Advertisement
姬稷想讓奴隨們替他梳發,奴隨們一人一把梳子,一小撮一小撮地梳,比趙姬梳得舒服多了。可是不等他吩咐,趙姬已經撲上來,里嘀咕:“好不容易理順,這下又得重新梳了。”
姬稷到邊的話咽回去。
算了,讓梳吧梳吧。
這點痛算什麼,殷人男兒,怎能連梳發之痛都忍不了。
他覺得趙姬今天有點不一樣。早上起來,他一睜開眼,就看著他了。趙姬的眼睛本來就大,早上一眨不眨地凝視他,那雙眼睛比平時更大更圓,像一對牛眼睛。
有著牛眼睛的趙姬,今天喊起人來,也像是牛哞哞,到他懷里,用腦袋不停頂他的時候,也像是牛。
姬稷想著牛,口而出:“晚上吃炙牛吧。”
趙枝枝也想吃牛了:“漬牛更好吃。”
“為何漬牛更好吃?孤覺得炙牛更好吃。”
趙枝枝為自己心的漬牛爭奪一席之地:“炙牛用火烤容易烤糊,漬牛就不一樣了,新鮮的薄片牛去筋剔用酒浸泡,蘸上豆醬吃,吃進里,又又,嚼勁十足。”
姬稷:“吃炙牛。”
趙枝枝:“吃漬牛。”
姬稷回頭,目掃視趙枝枝:“你敢和孤爭?”
趙枝枝愣了愣。也不知道自己怎麼回事,得了那管羊皮卷,就像是多得了一條命,整個人都輕松了。他的承諾令不再為自己的命前途擔憂,的命握回自己手里,可是這才第一天,就開始逾越了。
趙枝枝有些張,下意識要將腦袋垂下去低頭認錯。擅長認錯,做起這件事如魚得水。
不等低下頭,太子捧住下往上抬,他不許低頭。
他狠狠親了親沒有漱口的:“怕什麼,又沒說你爭得不好。晚上孤吃炙牛,你吃漬牛,咱們一起吃。”
Advertisement
趙枝枝意猶未盡,笑著點頭:“嗯。”
早上姬稷去朝會,整個人神清氣爽,神采飛揚。
他總是忍不住他的頭發。
趙姬梳頭發雖然梳得力道大了些,但是將他的頭發梳得又直又順。等明年,他戴上冠,或許趙姬還能為他盤歇髻。
姬重軻坐在王座上,看姬稷第八遍頭發,他看著看著憋笑,趁眾人爭吵趙國一事時,悄悄命寺人備洗頭用的皂葉和熱水。
季衡昨天得了羊皮卷后,今天一直沒敢看姬稷。他怕他看太子一眼,就會忍不住發出笑聲。
誤以為姬稷沒洗頭所以頭發的姬重軻在吩咐完寺人后,也不再看姬稷。他怕他再多看啾啾幾眼,別人也會注意到啾啾頭未洗的尷尬。
姬重軻和季衡同時咳了咳,君臣倆默契地談起趙國的事。
昨日季玉在啟明堂的話已經被人拿到朝會上說事,很久沒有打戰的將軍們非常喜歡季玉的說法,平時寡言語的他們今天一改沉默作風,當殿和那些牙尖利的大夫們吵起來。
“我們又不是沒打過齊國,幫一個趙國打齊國有什麼要的!”
“當年齊國與我們殷國三戰三敗,他齊國的六座城池現如今都沒能拿回去,真打起來,齊國未必抵得住半月,只怕十天就要投降,有什麼好怕的?”
“借趙削齊,天賜良機,此戰若是不打,便是錯失良機!”
武將軍們壯志凌云,一個個吼得響亮,生怕聲音弱一點,就會被這幫子嗓門大的大夫們給比下去。
有人想要讓季玉站出來說話:“小季大夫呢?讓他出來,好好給這群弱腳說說。”
大夫們甩袖:“你們說誰弱腳?”
眼看就要打起來,姬重軻見怪不怪捂住耳朵,嫌棄地皺起眉。姬稷一言不發,他今天不打算說話。
Advertisement
季衡掃掃了他的天子和太子,他嘆口氣,揮揮袖子站出來:“諸君莫躁,吾有一言,不知當講不當講。”
武將軍們看了看季衡,洪亮的嗓音有所收斂,牽頭說話的左將軍蒙銳雙手抱拳一揖禮,因此表示對季衡的敬重:“季公但說無妨。”
季衡捋捋胡子:“將軍們為殷王室揚威的心雖好,但眼下并未有戰事,趙國尚未廢后,趙國和齊國之間并未有戰事,尚未發生的事,為它爭論,是否不值當?除非——”
季衡不聲朝姬稷所在的方向看了眼,繼續對武將軍們道:“除非將軍們未卜先知,早就知曉趙齊兩國戰事不可避免,所以才急著現在定下出戰之事。若果真如此,他日傳出去,天下人豈不說殷王室乃狼子野心之輩,有意攪諸侯國的安寧?”
蒙銳目掃了掃姬稷,及時收回,面平淡:“季公謬贊,吾等怎知未卜先知之,不過是看趙國遞了上奏書,由此多想些事罷了。”
季衡笑道:“既如此,那就不必再議,等趙齊兩國真正起戰事再說罷。”
蒙銳擰眉,沒再往下說。
他不說話,其他武將軍也不說話了。
姬阿黃笑了句:“欸,還是說說殿下的安城吧,聽說殷人都遷進去了?”
說到安城,殿上氣氛緩和,無人再提趙國的事,紛紛說起安城的事。
朝會結束后,姬重軻派人告訴姬稷洗頭之事,讓他不要急著出宮,洗完頭再走。姬稷窘迫之余,沒有拒絕。
反正回去也是洗,在王宮洗也一樣。
季衡正和人說話,轉頭一看,太子不見了。他急忙跟上去,五短材跑起來,氣吁吁,這才追上太子矯健的長。
姬稷見側是他,沒有慢下腳步:“季大夫不出宮,跟著孤作甚?”
Advertisement
季衡臉上笑瞇瞇:“吾最近頗年老邁之倦,想沾沾殿下年輕蓬的朝氣。”
“有話不妨直言。”
“猛虎下山固然是好,但韜養晦更為穩妥。”
姬稷明白季衡是說趙國的事,但他不打算聽明白:“都好,都好。”
季衡笑了笑,對姬稷揖禮:“殿下慎重。”
姬稷回禮:“多謝季大夫關心,孤自當慎之又慎。”
季衡看著姬稷遠走的影,深深地嘆一口氣。
姬稷拐到狹窄的宮道,一招手,昭明出現。
姬稷:“傳孤的口令,讓龐備調趙國的間人,盡快起事。”
昭明應下:“喏。”
十日后,趙國都城邯鄲。
夜深人靜的趙王宮忽然響起一記慘痛的悲鳴,趙王抱著他的姬仰天痛哭,大殿狼藉不堪,宮人驚恐跪伏。
趙王哭得眼淚鼻涕流一臉,發冠歪倒,頭發披散,年過四十的人此刻捶著坐在地上,像一個發瘋的稚:“是誰!是誰殺了寡人的花姬?”
他手里沾滿鮮,是從花姬上流出來的,花姬肚子上開了個大。趙王捂著那個,怎麼捂都捂不住,花姬瞪著眼已經痛苦死去,可的還在汩汩往外流。
大殿無人敢答話,宮人伏低頭,誰都不敢告知趙王兇手是誰。
趙王的嚎哭聲響徹宮殿,他抱著花姬的尸親了又親,手上臉上全沾了,許久,他放下花姬,站起來,拿過蘭錡上的鐵劍,瞋目怒視往外沖。
王后大殿。
趙王后躲在簾后瑟瑟發抖,手里握著一把沾的匕首,里念念有詞:“是先招惹我的,一個賤妾,竟敢三番兩次沖撞一國之后!該死,死有余辜!太便宜了,死得太輕巧了!我應該多捅幾刀,應該多捅幾刀……”
趙王后從齊國帶來的宮人想要上前攙扶王后,被趙王后邊新近得寵的巫阻攔。
巫月奴吩咐們準備沐浴用的熱水:“王后就要重生,需洗凈上的污穢之,方能完神圣的水凈之典,得到共工大人的神力。”
趙王后:“快,聽月奴的,快去準備熱水!”
宮人只好離開,去準備熱水。
宮人離開后,月奴握住趙王后的手,聲藉:“您做得很好,共工大人在上,您才是真正有資格得到幸福的人。”
趙王后渾發抖,抱住月奴:“對,只要我才有資格得到幸福,們都不配,都不配,月奴,共工大人會庇佑我的對不對?我是他的子民,他一定會庇佑我!”
月奴著的后背,輕聲說:“您是齊國公主,共工大人為齊國的守護神,他自然會庇佑你。”
趙王后哭起來:“月奴,我好想齊國,我想回去,我想回去,你快施法,讓共工顯靈,讓他托夢王父,讓王父接我回去。”
月奴拍拍的背:“月奴也想齊國,月奴想和公主一起回齊國。”
趙王后哭得更大聲,哭著哭著,忽然兩只手扼住月奴的脖子:“要是我回不去,你就去死吧。”
月奴被掐得不過氣,心里將趙王后祖宗十八代罵了個遍,面上鎮定從容:“怎會回不去?待王后完水凈之典,王后就是神了,神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無人能擋。”
趙王后怔怔出神,手上力道一松,放開樂奴:“對,神,我即將為神。只要我為了神,王父就會接我回去。”
趙王后小時候聽過神的故事,齊國有神,神是共工的神,為共工他的子民。齊國信奉共工,自認共工后人,以水為圖騰,所有的神話都與水有關。
神的故事,就是齊王給趙王后講過的睡前故事之一,對此深信不疑。當說著齊語穿著齊服的月奴出現在面前,以共工的名義,說可以為排憂解難時,很快就相信了。
在月奴的“詛咒”下,花姬病了,在月奴的“詛咒”下,花姬和王上吵架了,在月奴的“詛咒”下,王上也病了。事實證明,月奴真的可以幫鏟除花姬,甚至助回齊國。
不想做王后了,要回去繼續做的齊國公主,只做齊國公主。
趙王后:“我的信呢,我寫給王父的信呢!”
月奴:“早就送出去了。”
猜你喜歡
-
完結52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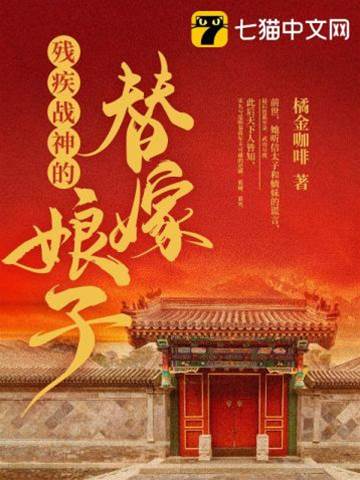
殘疾戰神的替嫁娘子
【重生+男強女強+瘋批+打臉】前世,她聽信太子和嫡妹的謊言,連累至親慘死,最后自己武功盡廢,被一杯毒酒送走。重生后她答應替嫁給命不久矣的戰神,對所謂的侯府沒有絲毫親情。嘲笑她、欺辱她的人,她照打不誤,絕不手軟。傳言戰神將軍殺孽太重,活不過一…
97.6萬字8 30851 -
完結668 章
毒妃傾城:王爺掌中寵
夏吟墨手欠,摸了下師父的古燈結果穿越了,穿到同名同姓的受氣包相府嫡女身上。 她勵志要為原主復仇,虐渣女,除渣男,一手解毒救人,一手下毒懲治惡人,一路扶搖直上,沒想到竟與衡王戰鬥情誼越結越深,成為了人人艷羨的神仙眷侶。 不可思議,當真是不可思議啊!
120萬字8 16741 -
完結245 章

穿成農女后我帶落魄皇子登基了
現代中醫大家一朝穿越,就面臨地獄開局?惡毒渣男?留著過年嗎?當然馬上退婚!極品親戚,要回父母遺產,立刻斷絕關系!救命恩人呃,那就以身相許吧!盛清苑快刀斬亂麻,一邊發家致富,一邊治病救人。呃,什麼?她隨便嫁的小秀才竟然是當朝皇子?“娘子,雖然我身份高貴,但是我對你絕無二心,求你不要離開我”小秀才緊緊拉住她的手,就差眼淚汪汪了。盛清苑輕笑一聲,道:“你想什麼呢!我這大周首富難道還配不上你這個落魄的皇子嗎?你趕緊將皇位拿下,給我弄個皇后當當!”
71.1萬字8.18 1417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