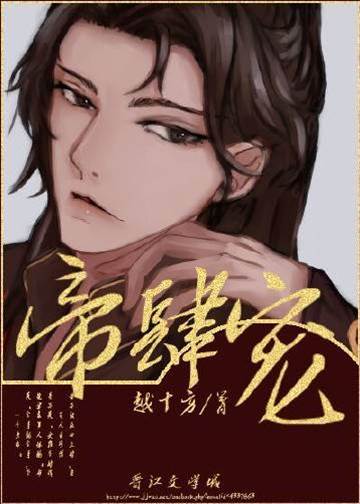《花開春暖》 第266章 各自的悲傷
到了離花廳不遠,孫嬤嬤引著鄒氏,往花廳左邊的一高大假山上走去,走了十來步,在一座垂滿綠蘿的嶙峋怪石後頓住腳步,招手示意鄒氏上前,撥開綠蘿,指著側下方的花廳,轉看著鄒氏吩咐道:
“鄒姨娘,你就坐在這一吧,只別弄出聲響就行,我們主子說了,你們爺過來了,這要商量的事,只怕關著你,還是讓你聽聽的好。”
怪石很高,巨般蹲伏著,腹部有一個小小的門,修著臺階,不知通往何,上面往前探出檐來,檐下已經放好了張扶手椅,孫嬤嬤示意婆子扶著鄒氏坐下,往後退了兩步站住,微笑著說道:
“我就在這裡,姨娘只管放心。”
鄒氏膽怯中帶著莫名其妙,不敢違了孫嬤嬤的話,扶著婆子的手,小心的坐到扶手椅上,手撥開面前懸垂著的綠蘿,微微著脖子,往下面花廳裡探過去,花廳離七八步遠,過雪白的綃紗簾,裡面的形清晰可見。
金志揚收了摺扇,昂然進了花廳,古云姍端坐在花廳上首,見他進來,面容冷淡的指了指左邊的扶手椅,
“請坐吧。”
金志揚頓住腳步,看了看古云姍,又轉頭看著古云姍手指指向的扶手椅,暗暗咬著牙,臉上帶著笑,彷彿很隨意的順著古云姍的意思坐了下來,接過小丫頭奉上的茶,喝了兩口,滿臉笑容的問道:
“墨兒他們還好吧?半年沒見他們了,真是想得不行!”
古云姍垂著眼簾,沒答他的話,冷淡的問道:
“你來有什麼事?”
金志揚眉頭擰一,又飛快的舒展開,上微微往前探著,陪著滿臉笑容,親熱的說道:
Advertisement
“雲姍,咱們這麼些年的老夫老妻了,從沒紅過臉,我對你如何,這些年……你還能不明白?有什麼話,只要你說了,我哪有不答應的?你看看你,何苦用這點子小事,驚了長輩去?”
古云姍眉頭皺了起來,轉頭看著金志揚,
“你要是沒什麼事,我就不陪你說話了,家裡事多著呢。”
古云姍作勢要走,金志揚忙站起來,手就要去拉古云姍,古云姍臉上浮出怒氣來,甩開金志揚的手,
“你也自重些!來人!”
外頭的丫頭婆子應聲而,金志揚臉紅漲,尷尬的往後退了兩步,擺著手說道:
“好好好!我不你,你先別走。”
古云姍冷著臉坐回到椅子上,丫頭婆子眼風掃過兩人,輕手輕腳的又退了出去,金志揚端起幾上的杯子,將杯子裡半涼的茶水一飲而進,看著古云姍,下了決心般說道:
“雲姍,你聽我說,鄒氏這事,往日是我錯了,萬沒想到家裡竟然門風如此,我真是半分也想不到!母親竟是那樣的人!誰知道這賢惠,竟都是要謀事的賢惠,如今我真是恍然醒悟,徹底明白過來了,往日是我糊塗了,被這假賢惠蒙了眼。”
古云姍眼底閃過悲涼,端起杯子,低頭喝起了茶,金志揚留意著古云姍,語氣沉痛的接著說道:
“都是我糊塗,當日把做了貴妾,要不是這樣……唉,雲姍,你也看到了,如今已經懷了四個月的孕,先讓把孩子生下來,那孩子,總是金家的骨,不能流落到外頭去,等生了孩子,我想著,要麼把送回臺州老家,讓到家廟裡清修,好好修修心,積點福,也是的福份,要麼,就把打發回去,家裡只怕也容不得,那也只隨去,雲姍,這幾天,我算是看明白、也想明白了,這賢惠都是假的,竟都是想騙了我,拆散了我們夫妻,雲姍……”
Advertisement
古云姍擡手止住了金志揚的話,
“那孩子呢?”
“孩子……”
金志揚頓了頓,看著古云姍,苦笑著說道:
“雲姍,我知道,你是個極賢惠的,這孩子,總是金家的脈,是我的骨,這孩子剛生下來,不過是一團,往後你養大了,他心裡眼裡,也只有你一個母親罷了。”
金志揚仔細看著古云姍的神,見垂著頭只不說話,咬了咬牙,接著說道:
“雲姍,我也只顧著你和墨兒幾個罷了,這孩子,你若不喜……若不喜,那就……送回臺州老家,給母親們帶著就是,若是……你覺得也不好,那就……讓人寄養到外頭去,雲姍,只要咱們一家人和和,旁的,我還在乎誰去?”
古云姍長長的嘆了口氣,站起來,直直的看著金志揚,傷萬分的說道:
“你只在乎你自己,旁的,我也罷,那個鄒氏也好,孩子也好,你哪個也不在乎!你走吧,往後不要來了,孩子我會好好帶大,你我,從此就是路人。”
古云姍轉就要從側門出去,
“等等!”
金志揚急得手想去抓古云姍,古云姍轉過,往後退了兩步看著他,
“孩子是我金家的孩子!你要與我做路人,我就全你!明天就給你送了休書過來,把孩子給我!我要帶孩子走!金家的孩子,不能長在你們古家!”
金志揚再也不住從早上積到現在的滿腹怒氣,點著古云姍,吼了起來,古云姍憐憫的看著他,角閃過譏笑,
“金家的孩子?那是我的孩子!任誰也別想打們主意!你也不行。”
古云姍說完,轉從花廳側門徑直出去了,金志揚撲過去就要拉住古云姍,側門後閃出兩個手拿水火的壯婆子,狠狠的盯著金志揚,金志揚膽怯的看著婆子手裡大的水火,下意識的往後退了一步,又退了一步,恨恨的說道:
Advertisement
“我告訴你古云姍,孩子是我金家的孩子!你若與我做路人,就把孩子給我送回來!”
兩個婆子拎起了水火,金志揚又往後連退了幾步,轉過,拎著長衫,怒氣衝衝的大步往院外衝去。
鄒氏半癱在扶手椅上,臉蒼白的一點也沒有,見孫嬤嬤過來,撐著椅子扶手,搖搖墜的站起來,擡手點著孫嬤嬤,聲音暗啞的質問道:
“你們大,讓我……讓我……看……要做什麼?”
“鄒姨娘別急,先舒口氣,千萬別急,我家大沒半分惡意,趕扶好姨娘,”
孫嬤嬤吩咐著傻在一旁的婆子,示意著鄒氏,
“鄒姨娘,咱們邊走邊說,你得趕趕回去,你們爺回去若是見不到人,總不大好。”
婆子急忙上前扶住鄒氏,孫嬤嬤領先半步,往側門走去,
“鄒姨娘,我們大這析產分居,可不是要嚇唬誰的,既說了這話,開弓就沒有回頭的箭,我們大斷沒有再回頭的理兒,請鄒姨娘來,不過就是讓姨娘聽聽,往後心裡有個底就是了,旁的?姨娘想想,我們大連你們爺都不要了,還能對你怎麼樣?”
鄒氏靠著婆子,垂著頭跟在孫嬤嬤後面,上了車,木呆呆看著車簾,隨著車子來回搖晃著,往客棧回去了。
金志揚沒在客棧,不知道往哪裡去了。
婆子扶著鄒氏進了客棧,回到房間,扶著半躺到牀上,急忙吩咐小丫頭端了蓮子茶進來,鄒氏就著的手,連喝了幾口,才過口氣來,轉頭看著婆子,滿眼的悲傷,
“嬤嬤,我怎麼辦?這肚子裡的孩子,怎麼辦?”
婆子將手裡的青瓷碗遞給旁邊侍立的小丫頭,扶著鄒氏,嘆了口氣勸道:
Advertisement
“姨娘別想那麼多,走一步,算一步吧。”
鄒氏用帕子捂著臉,嚶嚶的哭了起來,
“嬤嬤,怎麼會這樣?父親當日讓我跟了爺,他……母親哪裡不好?我這賢惠,怎麼就了假賢惠了?從前他那樣對我,難不都是假的?這妾,我這妾也是有文書的,他怎麼……怎麼……”
鄒氏哭得說不下去了,父親勸著跟了金志揚,出門前也許有些怨言,可自從進了金家門,直到回到這京城前,一直都是心滿意足的,的夫婿年英俊,前途無量,待尊重有加、溫,雖說是個妾名,也滿意了,一樣是府裡的主子,和當姑娘時一樣的金尊玉貴著,沒人敢怠慢半分,可如今,進了這京城,怎麼變這樣了?
了姨娘了,了奴婢了!他還要打發了,和的孩子……鄒氏哭得倒在牀上,婆子一邊抹著眼淚,一邊空無力的勸著,
“姨娘別哭了,懷了子的人,可不能這麼哭!快別哭了。”
鄒氏支起子,看著婆子哽咽道:
“嬤嬤,讓人準備車子,我要回去找母親去!”
“姨娘。”
婆子滿臉爲難的看著鄒氏,低低的回道:
“姨娘且耐耐子,姨娘這會兒,不好回去……”
“那你讓人去接母親來,跟說,我病了,讓來!”
“姨娘!”
婆子嘆了口氣,
“就是接人來,依著規矩,也得大點了頭才行,姨娘,如今咱們不容易,可不能再失了禮數,讓人抓了把柄去。”
“都析產分居了,要點頭?怎麼要點頭去?”
鄒氏聲音高了起來,婆子垂下了眼皮,鄒氏連聲泣著,又伏在牀上大哭起來。
嗯,第二更,晚上八點前,如果來得及就更,來不及....咳,那個,扔空心磚吧,閒收起來省點力。
非常謝大家的支持和,大家喜歡這個文,對閒來說,沒有比這個更好的了,至於其它,那都素浮雲。
你喜歡,覺得那應該給閒,閒開心,覺得應該打賞鼓勵下閒,閒開心,如此就夠了。
()
猜你喜歡
-
連載3575 章

錦鯉棄婦:隨身空間養萌娃
一覺醒來,安玖月穿成了帶著兩個拖油瓶的山野棄婦,頭上摔出個血窟窿。米袋裡只剩一把米;每天靠挖野菜裹腹;孩子餓得皮包骨頭;這還不算,竟還有極品惡婦騙她賣兒子,不賣就要上手搶!安玖月深吸一口氣,伸出魔爪,暴揍一頓丟出門,再來砍刀侍候!沒米沒菜也不怕,咱有空間在手,糧食還不只需勾勾手?且看她一手空間學識無限,一手醫毒功夫不減,掙錢養娃兩不誤!至於那個某某前夫……某王爺邪痞一笑:愛妃且息怒,咱可不是前夫,是『錢』夫。
322.4萬字8.08 312447 -
完結8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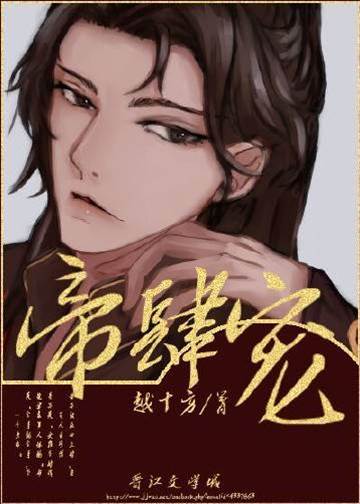
帝肆寵(臣妻)
從軍六年渺無音訊的夫君霍岐突然回來了,還從無名小卒一躍成為戰功赫赫的開國將軍。姜肆以為自己終于苦盡甘來,帶著孩子隨他入京。到了京城才知道,將軍府上已有一位將軍夫人。將軍夫人溫良淑婉,戰場上救了霍岐一命,還是當今尚書府的千金,與現在的霍岐正當…
28.8萬字8 26467 -
完結451 章

歡恬喜嫁
前麵七世,徐玉見都走了同一條路。這一次,她想試試另一條路。活了七世,成了七次親,卻從來沒洞過房的徐玉見又重生了!後來,她怎麼都沒想明白,難道她這八世為人,就是為了遇到這麼一個二痞子?這是一個嫁不到對的人,一言不合就重生的故事。
81.3萬字8 15673 -
完結532 章
醫庶無雙
原主唐夢是相爺府中最不受待見的庶女,即便是嫁了個王爺也難逃守活寡的生活,這一輩子唐夢註定是個被隨意捨棄的棋子,哪有人會在意她的生死冷暖。 可這幅身體里忽然注入了一個新的靈魂……一切怎麼大變樣了?相爺求女? 王爺追妻?就連陰狠的大娘都......乖乖跪了?這事兒有貓膩!
103.5萬字8 19339 -
完結206 章

賠罪
施綿九歲那年,小疊池來了個桀驁不馴的少年,第一次碰面就把她的救命藥打翻了。 爲了賠罪,少年成了施綿的跟班,做牛做馬。 一賠六年,兩人成了親。 施綿在小疊池養病到十六歲,時值宮中皇子選妃,被接回了家。 中秋宮宴,施綿跟在最後面,低着頭努力做個最不起眼的姑娘,可偏偏有人朝她撞了過來,扯掉了她腰間的白玉銀環禁步。 祖母面色大變,推着她跪下賠禮。 施綿踉蹌了一下,被人扶住,頭頂有人道:“你這小姑娘,怎麼弱不禁風的?” 施綿愕然,這聲音,怎麼這樣像那個與她拜堂第二日就不見蹤影的夫婿?
33.9萬字8.18 406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