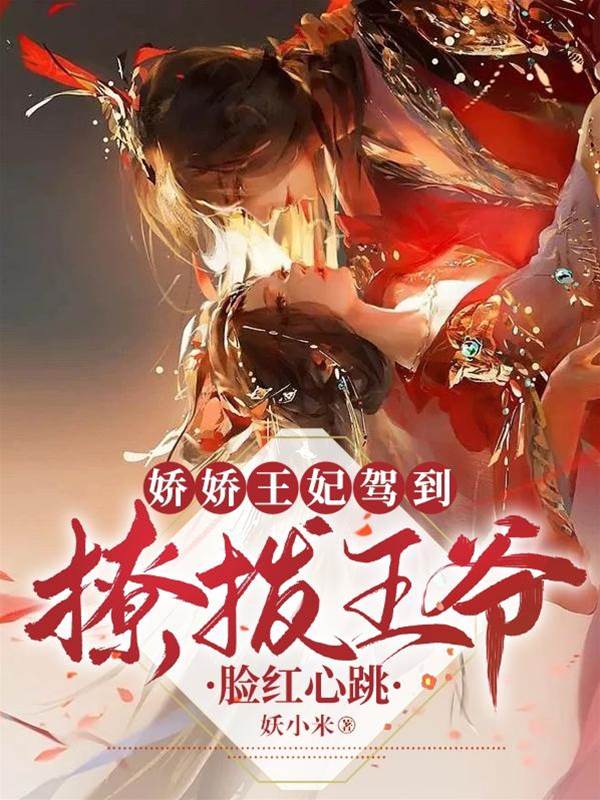《繼室難為》 第26章 第 26 章
「老夫人莫要生氣了,夫人這次雖是行事沒了分寸,但也主來認錯了不是?」花嬤嬤安道。
祝老夫人擺擺手,「氣什麼?這事雖是與名聲不好,但護著自家姊妹,說到底也算不得錯。在家裏雖是了些,但是出門在外,還是強勢些的好,能護著家裏人。」
說罷,哼了一聲,疲老的眼睛裏閃過些好笑,「你以為是乖順,自己來認錯?那是聰慧。」
沈蘭溪毫不知老夫人對的把戲瞧得分明,得前後背,腳步飛快,擺隨著的作打旋。
「娘子,這彩還要養著嗎?」元寶跟著,小聲問。
沈蘭溪看了眼抱著的綠豆眼小菜,隨口道:「養著吧,再長些才好吃。」
「咕咕!」
小菜似是聽懂了的話一般,撲棱著翅膀就從元寶懷裏跳了下去,剛跑兩步,又被元寶揪著翅膀抓了回來。
「跑什麼,娘子說了,現在還不吃你呢!」元寶教訓似的拍拍它的腦袋,又嘿嘿一笑,「養再吃~」
「咕咕咕!」
沈蘭溪不忍再瞧那傻姑娘,大步進了院子。
既是在老夫人面前扯了慌,總要圓好才是,哪裏能隨便烤了吃?也就這傻姑娘會信這話。
阿芙一早得了信兒,金炭火把屋子烘得甚是暖和。沈蘭溪一進屋便了上沉甸甸的披風,吩咐人擺膳。
鴿湯,地三鮮,麻辣魚和一碟子糯糯的紅燒豬腳,都是沈蘭溪尋常吃的。
「還有一碟子糯米丸子需得等會兒,婢子一會兒給您端來。」
沈蘭溪笑盈盈的瞧著滿是喜氣的小臉兒,誇讚道:「幾日不見,阿芙愈發伶俐了。」
阿芙有些害的笑了下,屈膝行禮退了出去,正巧撞上回來的祝煊。
Advertisement
「郎君。」
「嗯,再拿副碗筷來。」祝煊說著進了屋。
沈蘭溪剛要筷子,視線落在那進來的人上,又放下。
沒起行禮,沒規矩的托腮瞧著他去上的大氅。
「今日的戲,郎君看得可還盡興?」沈蘭溪語氣輕懶,帶著些秋後問責的意思。
祝煊凈了手,轉過來瞧,眼裏還殘留著些笑意,「以退為進,倒是不知你還會這個。」
沈蘭溪一臉驕傲的哼了聲,「我會的多著呢。」
說罷,夾了個糯油亮的豬腳開始啃,滿香。
聞言,祝煊眉梢微揚,眼前閃過坐在廊下盛氣凌人又霸道至極的模樣,輕笑了聲,「嗯。」
瞧了眼桌上的菜,他沒忍住道:「食葷易上火。」
沈蘭溪:「吃飯先閉。」
祝煊:「……」
脾氣倒是顯出來了。
用過午飯,祝煊便起往前院書房去了。
沈蘭溪上午在馬車上睡過,便沒歇晌,讓元寶拿了話本子來。
不覺日暮西斜,阿芙進來稟報,「稟夫人,郎君派阿年來傳話,請您去前院書房走一趟。」
沈蘭溪從話本子上收回視線,詫異道:「前院書房?」
往常從未有過這般,沈蘭溪也不敢耽擱,讓元寶伺候著重新梳了髮髻,穿好披風,匆匆往前院去。
府里上下都準備著過年,一路走來張燈結綵的好不熱鬧,唯獨前院書房寂靜的很。
「小的給夫人請安,郎君囑咐說,您來了直接進去便好。」阿年上前行禮道。
沈蘭溪與他頷首示意,幾步上臺階推門而。
寬大的檀香木書桌后,男人一青袍端坐著,聽見靜時掀起眼皮瞧來。
沈蘭溪左右看了看,沒瞧見什麼,這
才上前淺淺屈膝行了一禮,納罕的問:「郎君喚我來,可是有要事?」
Advertisement
祝煊示意上前,指了下自己左手邊的一摞冊子,「我先前應過你,休沐時教你看賬冊,幾日得閑,便細細教你一點。」
沈蘭溪險些兩眼一抹黑的暈過去,有些奔潰道:「這麼多?」
說罷,又小聲嘟囔,「郎君倒也不必如此言而有信……」
祝煊掩下笑意,只當作沒聽見後面那句,語氣清淡依舊,神也是一本正經的,「你先前說得不錯,笨鳥先飛,這是賬冊都是與你學習的,若是不夠,我再去問母親要一些來,往年的賬冊母親也應是收著的。」
沈蘭溪慌忙搖頭,哭無淚道:「不必去勞煩母親了,我也沒有那般愚笨不堪!」
祝煊對這話不置可否,「過來坐,還是你想站著聽?」
沈蘭溪幾步過去,在他旁邊的圓凳上坐下,雙手置於膝上,一副乖巧認真的模樣,「勞煩郎君了。」
「既是知勞煩,便認真些。」祝煊眼神意味深長的瞥一眼,翻開了最上面的那本賬冊。
沈蘭溪沒聽出其中意思,垂頭耷腦的瞧向桌面的賬冊。
這麼一摞,看來今日得聰明些了。
他的聲音清淡,仿若一杯清茶,沈蘭溪聽著那些悉的東西,迷迷瞪瞪的只想打瞌睡。
太催眠了!
祝煊側眼,瞧見漸漸闔上的眸子,抬手在桌面上輕叩了兩下,「既是犯困,便站起來聽吧。」
沈蘭溪:「?」
在一瞬間腦子清明,一難言的恥涌了上來。
「祝正卿!我,我是你娘子,你不能這樣……」沈蘭溪面紅耳赤的哼哧出一句,卻是越說越小聲。
狗男人抬起的眼睛裏的揶揄藏都不藏,煞人啦!
祝煊被喊得眉梢一揚,手從書案的屜里翻了戒尺出來,比西院兒的小書房裏的那個略薄一些,但足以威懾人了。
Advertisement
「今日既是當你先生,有些規矩還是要講的」,祝煊說著稍頓,戒尺在掌心輕拍了下,「方才的話,要我再說一遍嗎?」
明晃晃的在威脅人,沈蘭溪最是識時務,不不願的站了起來,立在他右手邊。
「還有一點講完,一會兒便要教考了,仔細聽。」祝煊叮囑一句。
「哦。」沈蘭溪隨意應道。
「若是還不會,那便要罰戒尺了。」祝煊漫不經心的道。
沈蘭溪:「……」
混蛋!就會這一招!
祝煊眼角的餘掃過不平的神,垂眸斂起眼裏的笑。
爛於心的東西,被他細細講來,沈蘭溪甚無聊,哪裏有還沒看完的話本子有趣?
祝煊講得簡單,教考也甚是容易。
哪怕沈蘭溪有心藏著,也不覺答對了大半,雖也是害怕他置於左手邊的戒尺。
他問,答。
直至……
「這法子你倒是記得清楚。」祝煊盯著的一雙眼睛道。
沈蘭溪點頭賣乖,「都是郎君講得好~」
聞言,祝煊輕呵一聲,「七八個步驟轉換為三步,這法子雖是輕巧,但不適於娘子這般——」
在漸漸反應過來的眼神中,他慢悠悠的說完那句話,「沒有學過管理賬冊的學生,是以,今日我可沒有教過你這法子。」
沈蘭溪如同被人當頭一棒,連忙辯解道:「我都說了我聰明,你怎麼不信呢?」
祝煊端起案桌上的茶水潤了潤嗓子,作勢翻開另一本賬冊,「既是如此,那我便考考你同樣沒講過的——」
沈蘭溪便是再傻,也瞧出了端倪,手按住他要翻賬冊的手,負氣的一屁坐在圓凳
上,「你戲弄我!」
這話帶了幾分指控的意思,祝煊不接,反問,「不裝了?」
沈蘭溪回他一記白眼,有些氣道:「祝正卿,你好生能裝啊。」
Advertisement
「比不得你沈二娘。」祝煊涼嗖嗖的道,又飲了口茶。
「哼!你是如何知曉的?」沈蘭溪語氣蠻,有些兇的問。
祝煊不與解,放下茶盞,把那幾本賬冊合上,「自己想。」
「那日在莊子上,你瞧見了?」沈蘭溪反問,語氣卻是篤定。
懂賬簿之事,也就林氏知曉,便是沈蘭茹也不甚清楚,以為與一般是個一知半解的學渣渣。
「若是不想為人知,便要守好,不要外。」祝煊瞧是小輩一般,教導道。
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越想越氣,沈蘭溪被他耍了的惱一個勁兒的往腦袋裏沖,「哼!祝正卿,你欺負我!」
說著,起到了他上,雙手抓著他的領,惱怒得明顯。
祝煊被的作一驚,生怕摔了,手攬住的腰背,訓斥道:「不許胡鬧。」
男人上的清冷很重,沈蘭溪使著壞的想他與一般,原本抓著他領的手開始剝洋蔥,帶著些明晃晃的,「胡鬧什麼,郎君仔細說說?」
勾人的狐貍,勢要把這清冷如月的謫仙拉到自己的狐貍。
祝煊的耳不免染上了紅,在的手上輕拍了一下,「君子正冠,不許在書房鬧。」
沈蘭溪斜他一眼,語氣輕又綿長,「君子正冠,得以赴卿約,郎君是要去赴哪位佳人的約?」
謫仙終是不敵狐貍,被剝去了外面的青衫,出青白的裏。
眼瞧著裏不保,祝煊咽了咽嚨,一把抓住搗的手在腰后,惱道:「前夜沒要夠?」
沈蘭溪眼前閃過那夜熱湯池裏的,面頰也有些發燙,但還是故作鎮定道:「郎君沒有了?」
誰讓他先戲弄的,定得還回去!
沈二娘錚錚鐵骨,絕不認輸!
轟的一下,祝煊麵皮霎時通紅一遍,脖頸上的青筋都凸顯了出來,怒吼道:「沈蘭溪!」
小郎君被戲弄得衫半褪,很是狼狽,沈蘭溪滿意極了,聲音歡快的應:「誒,在呢?」
這一聲,仿若調皮的貓,在他心口上踩了下又跑開,無奈的。
祝煊一把擒住那起的人,眼裏著了狼。
兩人四目相對,沈蘭溪瞬間頭皮發麻。
糟糕!逗過頭了!
剛要開口,門忽的被敲了兩下。
「郎君,攬香樓出事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709 章

攝政冷王悄醫妃
特工軍醫穿越為相府嫡女,受父親與庶母迫害,嫁與攝政王,憑著一身的醫術,她在鬥爭中遊刃有餘,誅太子,救梁王,除瘟疫,從一個畏畏縮縮的相府小姐蛻變成可以與他並肩 ...
255.2萬字8.18 63160 -
完結449 章

郡主囂張:誤惹腹黑世子
一場精心謀劃的空難,顧曦穿越成了安平公主府里人人欺賤的癡傻嫡女。親娘早死,渣爹色迷心竅,與妾室母女狼狽為奸,企圖謀奪公主府的一切。前世的顧清惜,以為裝瘋賣傻,隱忍退讓便能茍活,卻仍被姨娘,庶妹奸計毒害。今生,顧曦決心將忍字訣丟一邊!專注斗姨…
120.8萬字8.09 87940 -
完結691 章

公府貴媳
晏長風嫁給病秧子裴二少,是奔著滅他全家去的。后來,她眼睜睜看著這病秧子幫她滅了全家,又一手將她捧成了天下第一皇商。……晏長風的大姐莫名其妙的瘋了,瘋言瘋語地說著一些匪夷所思的事。她說爹爹將死,母親殉情,家產被姨娘霸占,而她們姐妹倆會被趕出家門。她說她未來的世子夫君是個渣,搶奪嫁妝,寵妾殺妻,連親骨肉也不放過。晏長風難以置信,卻也做足了準備。后來證明,爹爹確實身處險境,姨娘確實狼子野心,她為了不讓后面的悲劇發生,代替姐姐嫁入國公府。然后,她嫁給了國公府最不起眼的一個病秧子。當她要大開殺戒時,那病...
110.4萬字8 25343 -
完結10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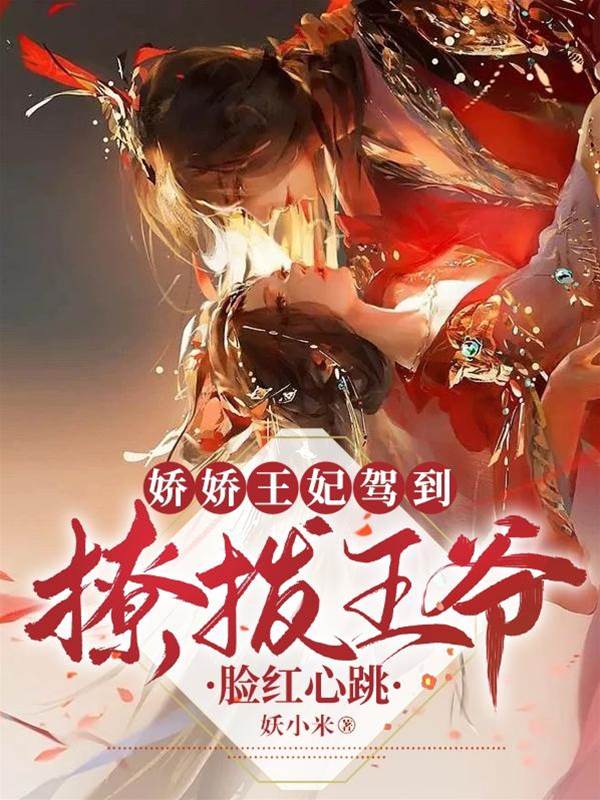
嬌嬌王妃駕到,撩撥王爺臉紅心跳
水洛藍,開局被迫嫁給廢柴王爺! 王爺生活不能自理? 不怕,洛藍為他端屎端尿。 王爺癱瘓在床? 不怕,洛藍帶著手術室穿越,可以為他醫治。 在廢柴王爺臉恢復容貌的那一刻,洛藍被他那張舉世無雙,俊朗冷俏的臉徹底吸引,從此後她開始過上了整日親親/摸摸/抱抱,沒羞沒臊的寵夫生活。 畫面一轉 男人站起來那一刻,直接將她按倒在床,唇齒相遇的瞬間,附在她耳邊輕聲細語:小丫頭,你撩撥本王半年了,該換本王寵你了。 看著他那張完美無瑕,讓她百看不厭的臉,洛藍微閉雙眼,靜等著那動人心魄時刻的到來……
183.7萬字8.18 106609 -
完結236 章
選秀當天被爆孕吐,冤種王爺喜當爹
【女強+萌寶+醫妃+偽綠帽】 一朝穿越,神醫沈木綰穿成丞相府不受寵的四小姐,第一天就被人「吃干抹凈! 被狗咬了一口就罷了,竟然在選妃當場害喜! 還沒進宮就給皇帝戴綠帽?! 沈木綰:完了! 芭比Q了! 瑾北王表示莫慌:我,大冤種。 人在家中坐,綠帽天上來。 御賜綠帽,眾人皆諷。 催眠術,神醫術,沈木綰生了娃打腫他們的碧蓮! 不要臉的瑾北王每天拿著鋪蓋送上門:「媳婦兒,孩子生下來吧,我跟他姓」
42.6萬字7.93 1386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