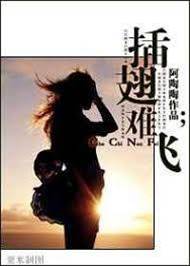《婚情告急:總裁請別撩》 第56章 夢鑰小姐!
「大爺呀,不就是帶夢月小姐參加個老爺子的大壽麼,你就當為我積點德吧,否則我真會挨荊條了。」我從被裡看到陳世章哭喪著臉,妖孽的臉皺了一團。
「再羅嗦,我讓你吃暴粟子。」許越把妮妮放到我邊的床鋪上,轉過去,抬起了手來。
「哎喲,饒命。」陳世章立即用手護頭,連聲哀,一會兒后,並沒有看到許越的手落下來,知道被他誑了,著蘭花指一甩手,跺腳,屁一扭,「呀,真討厭。」
他那作委實稽可笑,妮妮在一旁看得咯咯笑了起來。
「陳世章,你不要這麼娘行不行?」許越踢了他一腳,角也是忍俊不的笑意。
我躲在被子里都覺得好笑。
「許越,你這臭小子,老爺子大壽那天,你要不帶著夢鑰小姐參加,我,我……我上吊自殺。」陳世章跺著腳,滿臉脹得通紅地威脅著。
Advertisement
夢鑰是誰?是那天晚上接電話的那個人嗎?聲音溫溫的,一口一聲『許越哥哥』,我躲在被子里這樣想著,心裡竟會湧起酸酸的味道來。「陳世章,想死趁早,要不要我送你一程?」許越雙手進兜,嘲諷地看著他,「告訴你,今天上午恆盛地產那個合約給我好好籤,若出了差錯,我真要送你去曹地府了
。」
「,這個我可以代。」陳世章不假思索地點頭,「可是,夢鑰小姐的事,我是無法代的,這個可要說明,你不能給我難堪!」許越角浮起抹笑意,抬手捊了下陳世章那油放亮的頭髮,淡淡說道:「小子,給我好好工作,放心,老爺子大壽那天我會帶一個人回去的,不會讓你為難,這總行了
吧!」「哎呀,我的頭髮呀。」陳世章像被要了命般,一手捂著散了的髮,殺豬般嚎著,朝衛生間里跑去,直到在鏡子前把滿頭髮整理得油發亮,一不后這才跑了
Advertisement
出來,朝著許越一臉的哭相:「許越,你個混小子,若再敢弄我的頭髮,我一定要跟你拚命。」
許越昂然站著,子朝他近:「好,好,來,我倒要看看你如何來跟我拚命。」說完手過去又要弄他的頭髮,陳世章面容失,怪一聲,朝著門口跑去。
妮妮咯咯笑個不停。
「許總,別忘了我說的呀,我等著你的好消息。」陳世章走到病房門口后又探出個頭來,朝著許越做了個鬼臉,尖細著聲音提醒道。
許越朝前走二步,陳世章嚇得把臉一,一溜煙地跑了。
這陳世章一走,許越就在妮妮邊坐了下來,他只以為我睡著了,也沒來打擾我。
我從被裡看到他俊容上有疲,顯然這幾天照顧我和妮妮辛苦了。
這樣想著我心裡一暖,充滿了淡淡的。一會兒有護士進來替妮妮吊瓶,許越就坐在一邊鼓勵著妮妮一邊跟說話,果然妮妮自始至終也沒有哭一聲,針尖扎進小手背時,我看到小臉上的眉頭只是皺了下就
Advertisement
舒展開了。這間VIP病房朝南向,日正從窗簾上照進來,我躺在病床上,逆看著床邊形高大偉岸的男人,還有我的心肝寶貝妮妮,莫名的,那種淡淡的幸福是麼的真實,仿
佛我從沒有擁有過。
我癡迷地著那個俊容,不知怎麼回事,竟從許越的側臉上看到了些許妮妮五的影子。我知道我魔怔了,妮妮長得像我,是我和沈夢辰的孩子,而我竟然會有這種不切實際的想法,想想都是荒誕。
猜你喜歡
-
完結7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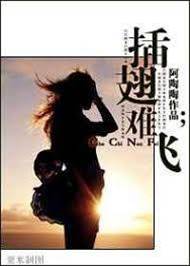
插翅難飛
美麗少女爲了逃脫人販的手心,不得不跟陰狠毒辣的陌生少年定下終生不離開他的魔鬼契約。 陰狠少年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女孩,卻不知道怎樣才能讓女孩全心全意的隻陪著他。 原本他只是一個瘋子,後來爲了她,他還成了一個傻子。
23.5萬字8 17235 -
完結658 章

名門寵婚之老公太放肆
他和她的關係可以這樣來形容,她之於他,是他最愛做的事。 而他之於她,是她最不愛做的事。 ……安城有兩樣鎮城之寶,御家的勢,連家的富。 名門權貴聯姻,艷羨多少世人。 連憶晨從沒想過,有天她會跟安城第一美男攀上關係。 「為什麼是我?」 她知道,他可以選擇的對象很多。 男人想了想,瀲灧唇角勾起的笑迷人,「第一眼看到你就想睡,第二眼就想一起生兒子」 她誤以為,他總會有一句真話。 ……一夕巨變,她痛失所有。 曾經許諾天長地久的男人,留給她的,只有轟動全城的滅頂醜聞。 她身上藏匿的那個秘密,牽連到幾大家族。 當她在另一個男人手心裏綻放,完美逆襲贏回傲視所有的資本。 ……如果所有的相遇都是別後重逢,那麼他能對她做的,只有不還手,不放手! 他說:「她就是我心尖上那塊肉,若是有人動了她,那我也活不了」 什麼是愛?他能給她的愛,有好的也有壞的,卻都是全部完整的他。
106.3萬字8 71276 -
完結235 章

追妻漫漫行長的心尖寵
【京城大佬 美女畫家】【雙潔】【追妻火葬場】 陸洛晚如凝脂般的肌膚,五官精致絕倫,眉如彎月,細長而濃密,微微上挑的眼角帶著幾分嫵媚,一雙眼眸猶如清澈的秋水,深邃而靈動。 但這樣的美人卻是陸家不為人知的養女,在她的大學畢業後,陸父經常帶著她參加各種商業聚會。 …… 在一年後的一次生日派對上,原本沒有交集的兩人,被硬生生地捆綁在了一起,三年漫長的婚姻生活中一點一點地消磨點了陸洛晚滿腔的熱情,深知他不愛她,甚至厭惡她,逐漸心灰意冷。 一係列的變故中,隨著陸父的去世,陸洛晚毫不猶豫地拿出離婚協議,離了婚……從此遠離了京城,遠離沈以謙。 後來,命運的齒輪讓他們再次相遇,隻不過陸洛晚早已心如止水。 而沈以謙看著她身邊層出不窮的追求者,則不淡定了,瞬間紅了眼。 在某日喝的酩酊爛醉的沈以謙,將她按在懷中,祈求著說:“晚晚,我們重新開始好不好?” —— 都說沈以謙風光霽月,聖潔不可高攀。 在兩人獨處時陸洛晚才發現,他要多壞有多壞,要多瘋就有多瘋。 他道德高尚,也斯文敗類。他是沈以謙,更是裙下臣
46萬字8 1579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