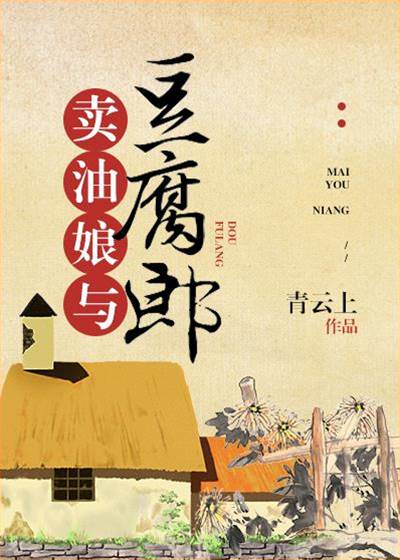《全宗門都是戀愛腦,唯我是真瘋批》 第100章 得離這玩意遠點
“小師叔,你……”夏天無看著林渡手中的銀鏡言又止。
方才屋里看了一圈兒,也就桌上的那燈盞不是著村子的東西,大約就是林渡所說的”監控“。
現在這位又是監視誰?
偏偏回來之后也不怎麼說話,就那麼看著手中的鏡子,那鏡子里也沒說話的聲音。
“遇上個人,他在破陣。”
“還有小師叔你破不了的陣?”夏天無下意識口而出,但很快反應過來,林渡才門一年,破不了才正常。
瑾萱和元燁天天在宗門里說小師叔的破陣多厲害,聽著聽著總忘了林渡還是個孩子。
陶顯聞言開口,“這陣道難門,更難通,小道長今年才多大……”
林渡的聲音已經響起,“我手這村子就沒了,還是讓他來吧。”
陶顯:?他就多余張。
陣道法門繁雜,刻陣布陣是一門手藝,破陣也是一門手藝。
林渡這人之所以比尋常人學得快,不過是因為接過現代數理化的熏陶,讓小時候學奧數,長大了學高數算理化學的人來研究陣法,對能量場的原理就接良好。
但其他很多細的破陣之法還沒學,現在的破陣辦法就兩個,一逆轉抵消,二暴力破壞能量場,讓能量失衡,后果不可預料。
大約就是破陣起來有種不顧他人死活的。
林渡低著頭,忽然聽到了陶顯小聲開口,“小道長,你這年紀輕輕的就白頭啊,是不是太用功了?我記得他們這地方,好像老人家都不長白頭發,要不你去要點方?”
接著他就看到那邊的小孩兒轉過臉,冷冷地看著他,一雙眼睛霧靄沉沉。
陶顯莫名有點張,“也不是那個意思。”
Advertisement
“我故意的,我取了個名字,挑染,怎麼樣,夠冷酷嗎?”林渡抬著下,一副臭屁小孩兒的態度。
陶顯只能點頭,“冷酷冷酷冷酷……”
再冷酷也是個都沒長齊的小屁孩。
唯有夏天無擰了眉,走過去搭了林渡的脈。
林渡本源不足,于壽數有礙,自進宗門后就一直在補,按理來說不該老得這麼快。
而如今那一縷白發卻生機全無,夏天無一探脈象,就知道是為什麼了。
那已經不只是憂思了,是殫竭慮,用腦過度,本能取了頭發的生機。
開口想罵,卻見小師叔忽然臉一變。
林渡看著手中的銀鏡,那上頭出現了危止那張含笑的俊臉,一雙眼睛仿佛在過琉璃燈直直看向,那燈照得人眼若琥珀琉璃,連那細下垂的羽睫都顯出一點靈巧的戲謔。
……
就知道危止遲早會發現。
耳邊傳來懶散含笑的一句,“看夠了?出來幫我個忙。”
很好,看來是一直都知道。
林渡垮個著臉,心不知道多糟糕,沖夏天無出個笑容,“二師侄,要罵改日,我先出去破個陣,那人不太行,還得我出馬。”
”二師侄,你去,守著大師侄吧。“上這樣說著。
夏天無下意識撒了手,也就那麼一瞬間,那人就沒了。
門框空的,竄出去的時候毫無阻礙,很快就沒影了。
夏天無默然了一會兒,小師叔這東西可以起個別名了,該撒手沒。
”我回去看看師兄。“面上不變,起出了屋子。
月愈發濛濛,林渡到井跟前的時候危止正拎著那琉璃燈,細細查看那補天石上鐫刻的咒文。
“喊我做什麼?”
Advertisement
“畢竟我不太行,還得你出馬。”危止笑著看了一眼。
他甚至聽到了之前出來時候說的話!
林渡頭皮都在發麻,已經想要把自己打包一團就地埋了,但面上還是穩住了,強行轉移了話題,看了一眼那地上明明白白出的,“還沒有拔除嗎?”
危止搖了搖頭,“還差最后一點,我鎮住了整個村子的上層,但這東西還有一部分和地下水扎在一起,你要保這村子,就要填點東西,這對我來說不難。”
林渡一面敷衍地點頭,一面明明白白瞧著他,眼中意味鮮明:對你來說不難,那喊我做什麼。
“我要你幫我提個燈。”
林渡臉上那漫不經心的笑就僵住了。
要不是危止他是重霄榜第三,林渡現在已經想把他按到井里去洗洗腦子了。
師父是死宅久了腦子鬼畜了,危止是消化龍消化傻了吧。
雖然確實窺缺德,但危止分明一開始就看出來了那是什麼東西。
這就是明晃晃的報復,又不是那高僧跟前提燈的小沙彌!
“井水可能會溢出來,你擋一擋,別淹了村子。”
危止倒也不是不能在一瞬間辦到,但……
他垂下眼睫,“你是冰靈,應當比我做得好。”
林渡忽然就收了聲,手接了燈,“也行吧。”
不愧是高僧,那就是比家里那老頭兒會說話。
危止祭出一個東西,和先前林渡在水鏡中所見的金剛橛有些類似,卻又不太一樣。
林渡之前看書的時候看文字描述總有些分不清金剛橛和金剛降魔杵,如今看了實就更愣了,兩個都是三棱尖,另一頭又都是繁復的紋路。
那人分明已經在施法,目堅定地看著眼前的靈寶,卻依舊開了口,“是降魔杵。”
Advertisement
林渡悚然一驚,他怎麼知道在想什麼……
危止勾了勾,“你盯著那東西,眼睛沒聚焦,顯然是在想東西,但你不是在腦中思量算計,而是在回想什麼,我猜是回想書中的東西,判斷我在干什麼。”
林渡后退了一步,很討厭這種被人向下兼容的覺。
當你和一個人相很舒服,不管說什麼都能接上,而那人不管什麼時候都能順應你的想法,那你多半是被向下兼容了。
不喜歡棋逢對手,只喜歡單方面掌控局勢。
得離這玩意遠點。
總歸這次合作完,估計此后也不會再見面了。
危止已經正了神,周可見金,那懸在他面前的降魔杵也已經慢慢旋轉起來,金大綻,分明是個不過掌長的東西,此刻已經三棱尖朝下,帶著沉沉的迫。
那妖僧卻已經闔上了眼睛,口中念念有詞,手中咒印不斷,眉宇間不見毫氣,一派清正。
是林渡從未見過的模樣。
危止倏然睜開眼睛,喝了一聲,金剛降魔杵已經應聲而下,直直扎那藤的系。
繼而那人雙手合十,結了個法印,周忽然起了一陣風,將那僧袍角吹得獵獵作響。
四下靈力迅速暴,底下可覺那涌的藤,遠清晰可見那底下有空乏崩塌之勢,繼而青山震。
盤虬在青瀘村下數百年之久,早就占據了極大空間的月藤被那降魔杵一路穿追逐,繼而分崩離析,四面金剛橛鎮之際亦同時發力,將那藤退拔除。
“起。”危止倏然抬手,那幾乎如人大一般的藤蔓破土而出,如同破布麻繩一般被拋至口中,繼而一道黑旋風兜頭而下,盡數倒灌其中。
Advertisement
不遠青山如同被了一層服,飛沙走石,一切不過瞬息之間。
那無辜的蟲蟻和棲息的野只覺得好像起了一陣風,毫不曾察覺有任何意外。
就在那靈藤被拔除的一瞬間,林渡忽然收了琉璃燈,右手一張,浮生扇就已經出現在了手心,繼而收手握,扇面利落張開,靈力盡數灌井水之中。
那恍若承不住被激發出來的井水就這麼被凍在了井口,甚至已經躍出了那井水約莫半人高的距離,卻都在一瞬間結了結結實實的冰塊。
寒氣森森。
“不愧是至寒的天品冰靈。”危止輕輕贊嘆了一句,繼而不聲地眨掉了眼睫上的霜雪。
林渡甚至皮得不行地,手敲了敲那凍了結實冰塊的井水。
忽然注意到了什麼,將手撤回來,漫不經心地轉過了頭,背著手不去看旁的人。
危止那出的半截脖頸之上,在月下有一泛著淺淡的銀。
是龍鱗。
危止方才趕走,大約是不想被看出自己一手就不住那妖氣。
猜你喜歡
-
完結491 章

鳳花錦
仵作女兒花蕎,身世成謎,為何屢屢付出人命代價? 養父穿越而來,因知歷史,如何逃過重重追捕回歸? 生父尊貴無比,一朝暴斃,緣何長兄堂兄皆有嫌疑? 從共同斷案到謀逆造反,因身份反目; 從親如朋友到互撕敵人,為立場成仇。 富貴既如草芥, 何不快意江湖?
90萬字8 10797 -
完結536 章

傾城醫妃不好惹
一朝穿越,成了不受寵的秦王妃,人人可以欺辱,以為本王妃是吃素的嗎?“竟敢對本王下藥,休想讓本王碰你....”“不是,這一切都是陰謀....”
97.2萬字8 114911 -
完結492 章
穿越醫妃不好惹
穿越前,她是又颯又爽的女軍醫,穿越后,她竟成了沒人疼的小白菜,從棺材里爬出來,斗后媽,氣渣爹。夫婿要悔婚?太好了!說她是妖孽?你再說一個試試?說她不配為后?那我做妃總可以了吧。只是到了晚上,某皇帝眨巴著眼睛跪在搓衣板上,一字一頓地說天下無后是怎麼回事?
88.1萬字8 19921 -
完結14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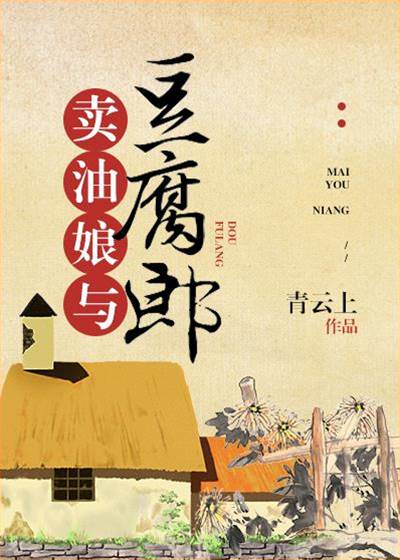
賣油娘與豆腐郎
每天早上6點準時更新,風雨無阻~ 失父之後,梅香不再整日龜縮在家做飯繡花,開始下田地、管油坊,打退了許多想來占便宜的豺狼。 威名大盛的梅香,從此活得痛快敞亮,也因此被長舌婦們說三道四,最終和未婚夫大路朝天、各走一邊。 豆腐郎黃茂林搓搓手,梅香,嫁給我好不好,我就缺個你這樣潑辣能幹的婆娘,跟我一起防備我那一肚子心眼的後娘。 梅香:我才不要天天跟你吃豆腐渣! 茂林:不不不
77.7萬字8 12157 -
完結257 章

春水搖
赫崢厭惡雲映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她是雲家失而復得的唯一嫡女,是這顯赫世家裏說一不二的掌上明珠。 她一回來便處處纏着他,後來又因爲一場精心設計的“意外”,雲赫兩家就這樣草率的結了親。 她貌美,溫柔,配合他的所有的惡趣味,不管他說出怎樣的羞辱之言,她都會溫和應下,然後仰頭吻他,輕聲道:“小玉哥哥,別生氣。” 赫崢表字祈玉,她未經允許,從一開始就這樣叫他,讓赫崢不滿了很久。 他以爲他跟雲映會互相折磨到底。 直到一日宮宴,不久前一舉成名的新科進士立於臺下,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包括雲映,她脊背挺直,定定的看他,連赫崢叫她她都沒聽見。 赫崢看向那位新晉榜首。 與他七分相似。 聽說他姓寧,單名一個遇。
38.5萬字8.18 469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