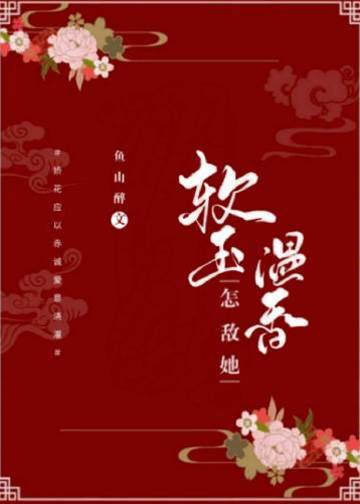《侯夫人與殺豬刀》 第61章 第 61 章
樊長玉睡得并不安穩,夜里又燒了一次。
渾渾噩噩陷在了夢魘里,眼前是白茫茫的雪原,飛雪大片大片落下。
穿著單薄的衫赤足在雪地里奔跑,腳都快凍得失去知覺了,卻不敢停下。
樊長玉一開始不知道自己在追趕什麼,直到看到遠的雪地里一對攜手往前走的夫妻時,終于知道自己為何這般著急了。
是爹和娘啊!
更用力地往前跑,心口酸漲得疼,眼眶也瞬間涌上熱意:“爹,娘!”
前方那兩道影明明走得不快,可就是無論如何也追不上,急得不行,幾乎快落下淚來。
雪地里的人終于回過頭來,臉上依舊是記憶中溫的神,對道:“長玉乖,回去。”
樊長玉不知自己為什麼難過這樣,眼淚流出來的時候,心口一一地疼,無措地問:“你們去哪兒?”
人沒有回答,只轉過頭和男人一起繼續往前走了。
樊長玉怔在原地,覺自己像是忘了什麼,腔里窒疼得厲害,口鼻呼吸也格外艱難,仿佛是溺在了水中。
謝征打了盆溫水準備給降熱時,就發現似魘著了,渾痙攣不止,汗如出水,將鬢發和里了個,原本蒼白的臉上也因高燒泛起了不正常薄紅,口齒不清地夢囈著些什麼,眼角都慢慢被淚水給泅了。
“魘著了?”
謝征還是頭一回瞧見這般狼狽又這般脆弱的模樣,心口像是被堵了一團棉花,下來又悶得發慌,他推了推樊長玉:“醒醒。”
但樊長玉被魘得太沉,毫沒有醒來的跡象。
他見樊長玉無意識掙扎時險些到了左臂,只得用一只手避開胳膊上的傷,按在了肩頭,制住,再冷聲吩咐守在屋外的親衛:“去尋大夫!”
Advertisement
白日里大夫給樊長玉看完病后,謝征瞧著況似乎穩定了,就讓親兵把大夫送了回去,畢竟把人留在這里,老嫗家中也沒多余的房間給那大夫歇息。
哪想到樊長玉夜里會突然驚厥。
到底是做了什麼噩夢?
謝征不自覺擰起眉心,發現因為齒咬得太,沁出了跡時,抬手去開下顎,卻不慎被咬住了指節。
他掙了一下,樊長玉齒關卻咬得更,幾乎是瞬間就破開皮,留下了一圈帶的齒印。
謝征只微微皺了皺眉,便索讓一直咬著自己食指了。
覺到懷里的人渾都在發抖,那蜷做一團的瘦弱背脊喚醒了他一些塵封的記憶,他這輩子都沒安過人,卻在此時遲疑了片刻,放緩了語氣道:“夢魘罷了,沒什麼好怕的。”
年時,那人在橫梁下方的擺也曾是他揮之不去的噩夢,每每驚厥著醒來,要麼是獨自一人在無邊的黑暗里,要麼是燈火通明,魏嚴立在床頭,看死狗一樣冷眼瞧著他。
魏宣則會帶著魏氏宗族的兒一起嘲諷他,學著他夢魘驚厥的樣子取笑作樂。
后來,他就再也不怕做噩夢了。
從尸山海里爬打滾殺出一條命,他刀口沾過的,比夢里的厲鬼還多。
這一刻,樊長玉抖的形似乎和記憶中那個自己重疊起來。
謝征眸深了幾許,等大夫來的時間里,他任樊長玉咬著他指節,半抱著,有些僵地一下一下輕拍著背脊。
說的最多的一句話便是:“別怕。”
別怕,噩夢都會醒的。
親衛把大夫從被窩里提起,放馬背上一路狂奔帶回來時,樊長玉已平復了下來,只是力竭又沉沉睡了過去。
Advertisement
謝征坐在屋一張木椅上,姿態隨意,左手食指上絞著一排牙印,模糊,他目放空,半垂著眸子,碎發散落在眼前,不知在想些什麼。
大夫哆哆嗦嗦被扛進門后,他散漫卻迫十足的目才淡淡瞥了過去:“魘著了。”
大夫大半夜的,夢游似的被人從被窩里拎到這里來,結果竟然只是做噩夢魘著了!
他一口氣堵在心頭,偏偏還半點不敢發出來,屋這男子眼風一掃,后背就已出了一層冷汗,只得認命戰戰兢兢去給那床上的子號脈。
脈一號上,大夫就意外地發現下午還虛弱的人,這會兒脈象竟然已平穩了許多。
他覷了一眼邊上那俊又沉的男人,到底沒敢說床上這子況好的,琢磨了半天,開了個安神的方子,道:“尊夫人應當是了驚嚇,這副安神藥喝下去,就能睡得安穩些了。”
親兵看向謝征,見他點了頭,才帶著大夫去廚房煎藥。
安神藥煎好拿過來,謝征照舊開樊長玉下顎,一勺一勺給喂了進去。
左手食指上那兩排模糊的牙印,此時才泛起了痛意。
他喂完藥瞥了一眼,沒做聲。
親兵倒是遞上了金創藥:“侯爺,您手上的傷口涂些藥吧?”
謝征沒把這樣的小傷放在眼里,只道:“不妨事。”
親兵拿著碗退出去時,打量了床上昏睡的樊長玉一眼,心底暗自掀起了驚濤駭浪。
這子容貌雖好,但也還稱不上絕,怎地就讓侯爺上心了這般?
不過回想起單手把一個年男子拎起來扔出去老遠的畫面,親兵又突然打了個寒。
這臂力,怕是同他們侯爺不相上下了吧?
Advertisement
-
喝下安神藥后,樊長玉后半夜的確睡得沉了許多,也沒有再發熱。
謝征枕在床邊淺眠了兩個時辰,天剛放亮時,門外便響起了極輕的敲門聲。
他來看了一眼床上,見樊長玉睡得頗沉,拿上一旁矮凳上的大氅幾乎沒弄出靜出了房門。
屋外的親兵見他出來,忙低了嗓音道:“侯爺,查到隨元青的下落了,他果真躲在清風寨!清風寨被搗時,他便帶著一部分清風寨的人趁從后山的小路逃了出去,現已被咱們的人到了巖松山上。”
謝征眸子里全是冷意:“守住下山要道,放獵犬進山,且看他能躲到幾時。”
親兵面難掩激之,抱拳道:“屬下這就去辦!”
一陣寒風拂過,謝征看著垂落至自己腳邊的一片凝著霜雪的枯葉,忽道:“今日刮的是西南風。”
親兵尚未明白他話中意思,便聽他道:“在上風口熏濃煙,順道把那山匪頭子的尸首一并帶過去,鞭尸。”
親兵一驚后,臉上喜更甚:“屬下遵命!”
在巖松山下鞭清風寨大當家的尸,躲在山上的清風寨余孽只怕膽都給嚇破了。
用濃煙熏得他們夠嗆之際,才放獵犬進去追,不愁不出躲在巖松山的山匪余孽,屆時只要守在各大下山要道,便是甕中捉鱉。
-
又是一個大雪天,巖松山上卻是濃煙布,幾大摞松柏枝燃燒升起的濃煙被風帶著往山林深飄,獵犬穿梭在林里,犬吠聲此起彼伏,仿佛是追逐獵的豺狼。
躲在山上的山匪被攆得四躥,一出現在山道上就被早早埋伏好的兵給包了餃子。
只是等山上的濃煙都散去,兵們清點落網的山匪人數時,卻并不見隨元青,也不見清風寨那名匪。
Advertisement
帶兵的小將拿刀抵著一名山匪的脖子喝問:“秦緣和閆姓匪在何?”
山匪求饒道:“小的不知,煙一放起來,大家伙兒都被熏得不了,又被狗攆著,在林子里跑散了。”
小將眼見問不出什麼,只得派人進山去找,卻只找到兩名被割后掉了甲胄的兵。
小將看到尸沉罵一聲:“壞了!快往山下追!”
一山腳下,流水潺潺,從道上駕馬狂奔了幾十里地的兩名兵打扮的人,終于一扯韁繩停下,從馬背上翻滾下來便沖到河邊,也不顧岸邊的積雪,直接趴地上牛飲了幾口沁涼的河水。
其中一人伏跪在河岸邊,竟是突然突然嗚嗚哭了起來。
嗓音尖細,明顯是名子。
邊上喝了幾口水便仰躺在雪地里氣的男子,并沒有出言安的意思,緩過勁兒后,便把上的甲胄解下來,扔進了河里,爬起來后大步朝著戰馬走去。
啼哭的子見他似乎要一個人走,驚得哭聲都卡住了,忙追上去:“秦大哥,你去哪兒!”
這二人正是殺了兩名兵換上他們從巖松山逃下來的隨元青和閆十三娘。
隨元青正要翻上馬背,卻被人死死拉住了一條胳膊。
他垂眼打量這淚眼朦朧著自己的子,形在子中也是偏高挑的,五算不得好看,臉上還有山里姑娘常年凍曬的淺紅,放長信王府里,頂多能算個使丫鬟。
他以為自己喜歡上了這類會些武藝又野難馴的子,但就目前看來,好像并非如此。
讓他心的,只有那個人。
他生著一雙瀲滟的桃花眼,笑起來的時候尤其多。
此刻挑起角,卻是把閆十三娘拽著自己臂膀的手一點點扳開了去:“天下之大,自有我的去,就此別過了。”
角的笑,明明涼薄至此,卻也是好看的。
閆十三娘呆住了,反應過來時已死死拽住了隨元青,指甲隔著服都似要陷進他皮里,近乎癲狂地質問他:“什麼意思?你要拋下我一個人走?”
隨元青淺淺一挑眉,似乎覺著問這個問題太蠢了些,笑了聲:“有何不可?”
人的指甲太尖了,抓得他手臂生疼。
他皺了皺眉,徹底失了耐心,扯開人的手直接翻上馬。
閆十三娘恨聲道:“秦緣,你沒有良心!我大哥為了讓我們,才去引開兵的,你對得起我大哥嗎?”
隨元青嗤了聲:“從府手底下逃出來,不是各憑本事麼?不然你以為巖松山上那些人是怎麼死的?”
閆十三娘嗚嗚大哭,只道:“你忘了是我把你從江邊救起來的?你不能這麼對我……”
隨元青忽而笑了笑,甚至在馬背上俯低子同閆十三娘視線平齊:“你救了我,可我不也把你從巖松山帶出來了麼?我為什麼不能這麼對你?”
話落,直接直起子,一扯韁繩揚鞭而去。
閆十三娘歇斯底里大哭起來,咒罵道:“秦緣,你必不得好死!”
隨元青對后人的哭罵聲充耳不聞,駕馬跑出一段路后,才從懷里掏出那副他后來去樊家搜尋到的畫。
畫上的似一家三口,男人俊非凡,人憨的笑上自有一朝氣,那個跟人長得極像的娃娃則滿眼古靈怪。
肩頭被樊長玉的那個窟窿還疼著,但隨元青心突然變得極好。
從拿到這幅畫時,他便猜到了當初傷自己的那鬼面男子就是謝征。
至于這畫上的人和他的關系……
莫非是他養在外面的人?
那畫上的小孩就是他們的兒?
隨元青目又在畫上脧巡了幾遭,畫上的人瞧著還只是個妙年,若有個這般大的兒,年歲至得雙十往上。
但一想到自己兄長逃跑的那個寵妾,給他兄長生了個兒子后,看著也同無異,他又慢慢相信了這個猜測。
難怪那天那人死死護著后院那口枯井,定是謝征迫于戰事離開了清平縣,知道自己帶著一個小孩逃不出去,才把小孩藏到了井里。
思及那人已經給謝征生了一個兒,隨元青臉變得不太好看,把畫重新揣懷里,一夾馬腹繼續往前走。
不管怎樣,有了這幅畫,這趟清平縣之行,也不算一無所獲了。
至知道了武安侯的肋所在。
猜你喜歡
-
完結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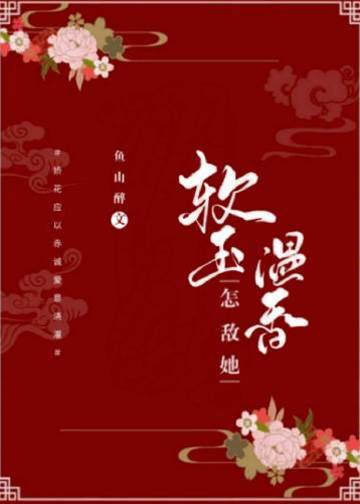
怎敵她軟玉溫香
提起喬沅,上京諸人無不羨慕她的好命。出生鐘鳴鼎食之家,才貌都是拔尖兒,嫁的男人是大霽最有權勢的侯爺,眼見一輩子都要在錦繡窩里打滾。喬沅也是這麼認為的,直到她做了個夢。夢里她被下降頭似的愛上了一個野男人,拋夫棄子,為他洗手作羹湯,結果還被拋棄…
21.9萬字8 10628 -
完結356 章

養丞
童少懸第一次見到家道中落的唐三娘唐見微,是在長公主的賞春雅聚之上。除了見識到她絕世容貌之外,更見識到她巧舌如簧表里不一。童少懸感嘆:“幸好當年唐家退了我的婚,不然的話,現在童家豈不家翻宅亂永無寧日?”沒過多久,天子將唐見微指婚給童少懸。童少懸:“……”唐見微:“知道你對我又煩又怕,咱們不過逢場作戲,各掃門前雪。”童少懸:“正有此意。”三日后,唐見微在童府后門擺攤賣油條。滿腦門問號的童少懸:“我童家
150萬字8 1875 -
完結559 章

一念桃花
八年前,常晚雲在戰亂中被一名白衣少年救下,她望著眼前的少年,俊美,有錢,當場決定我可以; 八年後,常晚雲終於知道了少年的身份。 當朝皇帝的九皇子,裴淵。 重新見面,晚雲作為醫聖唯一的女弟子,來到裴淵身旁為他療傷,阿兄長阿兄短。 裴淵日理萬機,只想將她送走,甚至當起了紅娘。 豈料趕人一時爽,追人火葬場。 晚雲冷笑。 憑本事踹的白月光,為什麼還要吃回去?
95.3萬字8 1050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