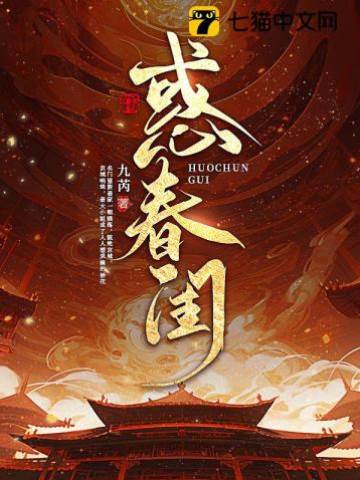《嬌鸞》 第22章 畜生
之后他半彎下腰,雙手輕輕捧住的臉頰,俯下朗星般的眸子。
“除非蘭昭儀還活著,親口所說,你不是陛下的兒。否則任何旁人說的話,你都不可輕易相信。”
姜玉目流盼,與他久久對視。
他騰出另一只手幫了眼角的淚:“莫要再哭了,好不好?”
話語溫,像是在哄。
剛剛在眾人面前,他摟住安的緒,也是的語氣。
姜玉忍不住眼眶發酸,他越是不讓,就越是眼睛潤。
看著這個樣子,姜曜忽然出一只手臂,將攬懷中。姜玉順勢埋他前,低低地泣起來。
姜曜輕拍打的肩膀,落在發梢上,向下尋的耳廓:“你藏在東宮被發現便被發現了,不用擔心。父皇如此疼你,不會過多怪罪。萬事都有我來理。”
姜玉一只手攬住他的肩膀,低低的“嗯”了一聲,聲音發,聽著一點力氣也沒有。
姜曜想起小時候和自己哭或撒,似乎也是這個樣子。
好半天,等緒穩定下來了,他才尋耳垂道:“你摟我的力氣小一點,著我背后的傷口了。”
姜玉趕退出他的懷抱,手背了眼角淚珠。
人跪坐于地,烏發婉轉,雪花貌,聲音:“那你在獵場怎麼樣,衛燕他還活著嗎?”
姜曜穿好上的衫,道:“衛燕尚且還活著,不過他的屬下已經被悉數策反,除去他只是早晚的問題。”
正說著,殿門被拍了拍,曹公公又走了進來。
殿二人齊齊扭頭看向他。
曹公公面難看之至:“殿下,未央宮傳來的話,讓你過去一趟。”
姜曜問:“是關于貞的事嗎?”
Advertisement
曹公公搖了搖頭,面發青:“是六皇子殿下的是——”
“他和趙婕妤通,被捉著了。”
姜玉目一,而他側的姜曜面容霎時冷了下去。
三更夜,更滴滴答答,未央宮里燈如游龍。
姜曜換了一袍,隨著領路的宮人穿過長長的宮道。
還沒殿,就聽到了里面叱罵聲——
“畜生行徑啊!逆子,是你半個母妃!”
姜曜垂眸聽了會,才慢慢繞過屏風走出去。
一,大就看清了殿的況。
六皇子姜灼跪坐在大殿中央,一只手艱難支撐著地,趙婕妤則衫不整,哭著伏在他上,涕淚連連求饒。
侍立在兩旁,手握木杖,鮮叢上面落滾下。
曹公公附在姜曜耳邊提醒道:“方才陛下一氣之下,把六皇子的給打斷了。”
姜曜挑眉,果然見姜灼另一只手搭在自己的左之上,瞧著面甚是痛苦。
六皇子的母妃,班人,正跪在大殿階下求:“陛下,請你看在我的面上,饒他一命吧,他年紀小,才弱冠不久,不懂事……”
“嘩啦”一聲,皇帝一袖子,帶桌上茶碗砸碎在地上。
“還不懂事呢?他三皇兄像他這麼大的時候,都帶兵上過戰場了,他呢?敢覬覦母妃!”
皇帝口上下起伏,從臺階上走下,撈起一只袖子,指著地上的一對男。
“畜生行徑,枉顧人倫!姜灼你還是人嗎?”
姜灼毫不懼,目恨:“父皇要打要殺隨便置!兒臣就是喜歡趙婕妤,這輩子都要和在一起!到底當初誰是畜生,干出強搶兒媳一事!”
趙婕妤趴到他上,泣不聲:“你別說了,夠了。”
Advertisement
皇帝氣得面漲紅:“朕的臉面都被你丟盡了,朕和你是一類人嗎?朕是皇帝,是你的父親!你放出去問問,天底下哪個兒子敢忤逆老子!”
“朕今天不打死你,朕這個皇帝就別做了。”
說罷,搶過侍手上的棒,朝姜灼上砸去。
姜灼垂靜靜地道:“父皇為何如此偏太子和十四妹,就不能偏我一回?”
不提這話還好,一聽到“十四妹”,皇帝更暴怒起來。
“要是你十四妹或是三哥干出這樣的勾當,我也得把他們的皮給了,給打斷了!”
一時間大殿哭天搶地,班人和趙婕妤撲到姜灼上,替他擋著落下的棒。
皇帝高聲呼喊:“來人,給將這對苦命鴛鴦拖到外面杖斃了!”
屏風邊上,姜曜趁著時機走了出去,行禮道:“父皇。”
瞧見姜曜,皇帝總算順了口氣,道:“曜兒,你來了。”
皇帝低聲問:“這事你說怎麼理?”
姜曜低頭看一眼六皇子,低聲道:“起來。”
六皇子撐了撐,如實道:“起不來。”
皇帝嗤笑一聲,踢了姜灼一腳:“你何時能學學你的皇兄,從來不會讓朕煩憂!”
姜灼自嘲道:“天底下有幾個能像皇兄這樣的人?”
皇帝道:“行了,這事就讓你皇兄來斷吧,你這條賤命到底是去是留。”
姜灼被人攙扶起來,聽到這話,虛弱地看向姜曜,想起此前和姜曜的談——
一旦東窗事發,便是萬人指責。
他骨子里流著天子的,或可免除一死。可趙婕妤呢?
姜灼面一變,向跪伏在地的趙婕妤。
姜曜不再看他,對皇帝道:“陛下千秋節將至,壽辰上不能見,若是此時置您的脈至親,恐怕會怒天罰。不若召欽天監的人來占卜看看?。”
Advertisement
近年大昭流年不利,西南一帶赤地千里,遭遇大旱。
這是天降的兇兆。
皇帝平日最是信奉鬼神,一聽這話,皺眉擺了擺手。
姜曜看向姜灼:“祁王即日起,被押回北方封地,此后經年沒有召見,不得朝覲見。至于趙婕妤——”
姜灼全冷住,定定地看著姜曜。
姜曜緩緩道:“便按照宮規,發配揶庭為奴。”
姜灼繃的面容有些松。
班人趁機遞眼,讓宮人上來扶著六皇子下去。
鬧劇收場,眾人漸漸退了出去。
皇帝回到寶座邊坐下,手撐著額頭,好似極其頭疼。
半晌,他才抬起頭,看向坐在旁的韋皇后。
“皇后深夜來未央宮找朕,是有何事?”
韋皇后與皇帝是強湊到一塊的夫妻,幾十年相,早就相看兩厭,甚至還比不得皇帝和姜灼的母妃班人的。
方才大殿里發生的一幕,顯然也映了韋皇后眼里。
看向下方立著的姜曜,短暫地視線接,有些擔憂,到底先將腹中的話了回去,道:“沒什麼事,就是聽說陛下近來頭疾嚴重,想來探一二。”
“那可真是多謝皇后了。”
這一對帝后,難得這樣好聲好氣地說話。
皇帝姜玄仿佛經歷了一場大仗,萬分疲憊,背靠在寶座上,道:“夜深了,皇后先回去休息吧,朕還有一些話,要和太子私下里談談。”
韋皇后行禮告退,走時瞥了姜曜一眼。
姜玄睜開惺忪的眼眸,朝姜曜招手:“曜兒,到朕的邊來。”
姜曜到他側,袍坐下,笑問:“父皇要和孩兒說什麼?”
皇帝四十多歲年紀,正值壯年,卻在貞公主逃婚后,這短短的一個月來,像陡然老了十幾歲一般。
Advertisement
姜玄嘆息一聲道:“是朕的貞不在,朕十分想念。今日有人到我面前,說他不是朕的兒,真是笑話,是朕從小看著長大的,怎麼可能不是親生?”
姜曜雙目看著他:“所以朕將那些滿胡言的宮人都給杖殺了,曜兒,朕做的對嗎?”
姜曜沉默,未發一言。
皇帝瞇了瞇眼,搭在寶座龍首上的手一下收:“朕,就算不是朕的兒,朕也不在乎,母妃早產誕下,朕確實懷疑過的脈,但朕更愿意信的母妃。”
“朕蘭昭儀,朕做錯了嗎?”
這次姜曜回道:“沒有,”
“是啊,一個人有什麼錯呢,朕當初只是想要將蘭昭儀留在邊,便將搶進了宮。今日朕看到了姜灼,就像看到了當年的自己。所以朕留了一命,朕心腸十分寬宥。”
皇帝目落在姜曜上,帶著幾分慈,一寸寸描摹他的廓。
“曜兒,貞走了,如今朕的邊只有你了,只有你從來不會讓父皇失。”
姜曜輕笑:“兒臣自然一輩子都聽父皇的話。”
皇帝滿意地笑了笑道:“再陪父皇說幾句話吧。”
姜曜應下道:“好。”
燭將二人的影子映照在窗戶上,殿外夜深沉,霧氣一點點彌漫。
東宮大殿。
夜三鼓,姜玉跪坐在配殿的案幾前。
寫完留給姜曜的信,走到外殿,將信放在他的書案上。
之后,姜玉便穿著一宮的裳,離開了東宮。
有暗衛從一旁跟了上來,悄無聲息好似鬼魅。
“公主要去哪里,太子殿下叮囑過您不能隨便出這間屋子。”
姜玉注意著腳下的路,道:“我想皇兄了,我要去接他回來。”
暗衛一愣:“這……”
姜玉大步往東宮外走,道:“你跟著我吧,大晚上東宮外沒什麼宮人,有你護著我,就不會被人發現,我只想早一點見到我的皇兄,然后和他一起回來。”
暗衛看著懷中抱著一只鼓鼓囊囊的東西,問:“公主見殿下帶著這個?”
姜玉秀眉一挑,“我給皇兄準備的東西。”
暗衛猶豫再三,還是跟隨姜玉出去。
出了東宮,走上縵回的長廊,兩側點著幽幽的燈火,檐牙上首好似猙獰而笑。
行了約莫一刻鐘,到了長廊的盡頭。
暗衛攔住姜玉道:“公主,最多只能到這,不能再往前走。殿下回東宮會經過這條路。您就在這里等即可。”
姜玉環顧四周黑黢黢的環境,道了聲“好”,抬起手,指著一丈遠外的一個涼亭閣子。
“我想進閣子里等皇兄,行嗎?外面風大。”
暗衛見那涼亭就在自己視線范圍,不假思索地答應:“好。”
姜玉朝他笑了笑,道:“若是皇兄到了,記得來亭子里喊我。”
說罷,一個人進了亭閣。
亭閣子是封閉的,四周圍繞著扇門,閣子里里面漆黑一片,手不見五指。
姜玉進來后不久,在地磚上到了道的機關。
敲了敲轉頭,一道石門在腳下打開。
姜玉抱著行囊,慢慢走了下去。
姜玉最初的謀劃就是,在東宮照顧姜曜,等他雙目復明,便從后山的地宮離開。
現在也到了離開的時機了。
已經知曉自己的世,藏在東宮也已經被發現。沒理由再待在這里,給皇兄添麻煩了。
姜玉點了一支火折子,照亮了前方的路。
想,等出去,就和長安城的蘭家的人接應,讓他們護送自己北上。
到時候平安去到河西外祖家,再和皇兄取得聯絡。
當初姜曜對去后山,想要出宮的行為,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想來若這次自己真的逃出宮去,他應該最多只是開始詫異一下,便慢慢不會在意了。
姜玉極其悉這里,快步往前走。
行了有兩三刻鐘,姜玉出了道,走進后山。
今夜無風,衛燕安在山上的侍衛全都被調走了,周圍沒有守衛。
姜玉一路無阻,很快就索到了地宮的口,打開門。
在進前,姜玉站在山腰,俯看了一眼下方巍巍的皇城。
皇宮在幽幽燈火中,巍峨且蒼茫。
姜玉鼻尖發紅,心里浮起幾難言的緒,努力吸了一口氣,到底沒再留,轉走進地宮。
卻在這時,約約,好似瞧見遠林子間有一個人影子廓逐漸清晰。
姜玉后退一步,背抵在樹上。
“公主莫怕,是奴婢。”
這道聲音一出,姜玉攥手心,喚道:“陳琦?”
果然,那道影從黑暗中走出,面容逐漸變得清晰。
陳琦撐著燈籠從黑暗中走出,笑道:“十月十七,公主果然還是上后山來了。”
姜玉心里豎起警戒,比陳琦快一步,進地宮,按下機關。
下一刻,陳琦面驚異,丟下燈籠跑上來,
厚重的石門將將在他面前關上,將他隔絕在外頭。
姜玉轉過,快步往里走。
不清楚陳琦為人,也不敢輕易相信他,便趁著這個檔口,將他甩掉最好。
當務之急是離開皇宮。
地宮外連接著的是長安城的東市。
天子的萬壽節將至,長安城十日不設宵,外面的長安城,當正是繁華之時。
如果走快一點,應該能趕在陳琦進來找到之前,走出地宮。
姜玉快步往前,走了半刻鐘,忽然發現一件不妙的事,漸漸停了下來。
看見前方地宮的道路,兩側點了宮燈。
知曉地宮道的人,統共的不過幾個。一年天子也只會派人進來打掃三四回。
是誰點染了這些宮燈?
姜玉心中疑,倏忽間看到了遠墻轉角,壁上投出一道男子的影。
斷斷續續談聲傳來。
——“人還好嗎?最近肯吃東西了嗎?”
這悉的聲音,讓姜玉倒吸一口涼氣。
——“回陛下,娘娘肯吃了。”
——“很好,你繼續勸,只要不要再絕食,朕就答應讓見兒一面。”
姜玉不清楚那個“”是誰,這一刻,心中像是被一無形的聲音召喚,腳下生出一種的意念,開始邁開步子,往前走去。
越往前走,宮燈越亮。
到轉角,姜玉呼吸慢慢屏住。
卻在這個時候,一只手出,捂住了的口鼻。
陳琦的聲音在耳畔響起:“公主別過去!”
姜玉子僵住。
一直到那邊談完,皇帝的腳步聲逐漸遠去,姜玉才覺得捂住自己的那只手,漸漸松開了。
陳琦湊過來,低聲音道:“公主要出宮就趕去出吧!地宮最近才關押進來了一個人,有重兵把守!眼下正值換班的時候!”
姜玉捉住他的袖子,問:“那被關押的人是誰?一個妃子?”
陳琦道:“出去再說!”
二人后的道里傳來咚咚的腳步聲。
陳琦催促道:“快走,后面的侍衛來了!”
陳琦探出頭,確保前面的路沒人了,才拉著姜玉往前奔。
姜玉心跳如雷,轉過轉角往前跑時,經過一閉鎖的屋子。
燭將殿人的影投在門上。
那似乎是一個曼妙的子,形裊娜,側廓致。
那奇怪的覺再次在姜玉心底涌起。
姜玉想要停下來,卻便被陳琦拽著,帶了下一道。
二人的影消失在路盡頭的不久,換班的侍衛也從轉角轉了出來。
晚風飄,長安城竹笙歌迷離。
姜玉從道中出來,疲力盡跌坐在漆黑的巷子里,外面是來來往往的人流。
風吹起的長發,手捂在心口,著劇烈地心跳,腦海里不斷閃過在地宮里見到的那一幕。
站起來,雙目明亮,看著對面的陳琦:“那地宮里的子是誰?”
陳琦搖頭:“奴婢也不清楚。”
姜玉又問了一遍:“告訴我,那是誰?”
皇帝為何會關押著這個人?似乎還有一個兒?
陳琦凝視了半晌,了:“公主,那是——”
地宮,蘭香殿。
子一襲紫的逶迤拖地,背對著門,坐在案幾邊,給自己倒了一杯茶。
聽到了外面發出的靜,挑眉問伺候的婢:“外面是不是有人經過?”
侍聞言,走到門邊,向外瞧了瞧,回頭道:“娘娘,外面沒有人影。”
“是嗎。”
那案邊的子轉過來,出一張極其熾麗的眉眼,雪玉貌,瓊鼻紅,即便生過一個兒,被幽過十幾年,依舊不折損一一毫容貌。
手撐著下,目懶洋洋地落在花瓶中的芍藥花上。
此人,正是當年盛寵一時、風無限的——
蘭昭儀。
侍欠行了個禮:“蘭昭儀,陛下來見您了。”
猜你喜歡
-
完結413 章

這太子妃不當也罷
楚姣梨重生了,上輩子含恨而死的她,對於求而不得的太子妃之位,此刻不屑一顧地道:「這太子妃不當也罷!」 在決定親手為他與原太子妃牽橋搭線的時候,她聽到了一個晴天霹靂的消息—— 什麼!太子妃不娶了?! 我上輩子為了太子妃之位都熬成病嬌了啊喂! 罷了罷了,咱再幫您物色新人選,但您可不可以不要總往我身上瞧?! 她逃,他追,他們都插翅難飛! 楚姣梨抬頭望著越疊越高的圍牆,不禁悵然道:「我的太子殿下啊,您快成婚吧!別再吊著我了!」 (PS:姐妹文《寵杏》已完結)
69.1萬字8 6534 -
完結805 章

掌家娘子福滿滿
配音演員福滿滿穿越到破落的農家沒幾天,賭錢敗家的奇葩二貨坑爹回來了,還有一個貌美如花在外當騙子的渣舅。福滿滿拉著坑爹和渣舅,唱曲寫話本賣包子開鋪子走西口闖關東,順便培養小丈夫。她抓狂,發家致富的套路哪?為何到我這拐彎了?錢浩鐸說:我就是你的套路。
151.8萬字8 32027 -
完結650 章
暖妻之誤惹首富王爺
某女臉上漸漸浮上一抹不明的笑容,“居然讓我睡地鋪,也不知道憐香惜玉,現在我要懲罰你,今晚你打地鋪! “ 某男終於意識到他自己挖了個坑把自己給埋了,趕緊湊上去,在女人紅唇上輕啄了一口,”夫人恕罪啊,你忍心讓相公打地鋪嗎? “ ”我很忍心!” 某女笑得眉眼彎彎,雙手環過男人的脖頸摟著,“從今晚開始,我以前睡了多少晚地鋪,你就睡夠多少晚,不許有異議!” “夫人確定?” “確定,從今晚開始,你睡地鋪!” “好! 本王今晚睡地鋪。 “ 某男墨黑的鳳眸裡蘊藏著點點精光,俊臉更是深沉莫測。 “本王這麼爽快答應夫人,夫人是不是該給點獎勵,嗯?”
121.6萬字8 16418 -
完結280 章

嬌養 慕如初
嬌軟笨美人×外表溫潤如玉,實際上腹黑狠厲的太子殿下。小時候阿圓逛廟會,不慎與家人走散,是個好心的大哥哥送她回家。那個大哥哥長得真好看吶,俊朗清雋,皎皎如天上月。大哥哥說他寄人籬下命運悲慘,甚至連飯都快吃不上了,但他人窮志不短,立誓要成為人上人。阿圓心疼又感動,鼓起勇氣安慰他:“大哥哥別難過,阿圓存銀錢養你。”也就養了兩三年吧,結果大哥哥搖身一變,成了傳說中心狠手辣的太子殿下。阿圓:QAQ 我感覺我養不起了。仆從們驚訝地發現,自從他們殿下遇見褚姑娘后,就變了個人,不再是那個陰郁狠厲的少年。他喜歡逗弄小姑娘,還親手給她喂糕點;教小姑娘讀書寫字,送許多精美華服讓她穿得可可愛愛;甚至,小姑娘受委屈,他耐心幫著擦眼淚后,暗暗地收拾了人。有一天,小姑娘兇巴巴道:“沈哥哥說自己寄人籬下還欠了許多債,怎麼總是揮金如土不知儉省?往后可莫要如此了。”仆從們冷汗:“不得了!居然有人敢管他家殿下!”可悄悄抬眼看去, 他家殿下竟是眸子含笑,無奈應了聲“好。”后來,誰人都知道東宮太子蕭韞有顆眼珠子,寶貝得緊。然而一朝身份掉馬,眼珠子生氣,他愣是哄人哄了好幾個月。 小劇場:太子恢復儲君身份的第二年,宮宴上,皇帝有意為太子擇妃。候府家的小姐明艷,公爵家的姑娘端方,個個貌美如花,含羞帶怯。可太子殿下卻突然起身,走到個五品小官之女跟前。 他神色寵溺:“阿圓,過來。”
37.9萬字8 30094 -
完結200 章

媚寵
齊春錦在周家宴上鬧了一場笑話,之后就隨父母遷到了苦寒的定州,自那日后,她卻開始日日做夢,夢里男人孤傲狠戾,像個活閻王,到了后來更每每掐著她的腰,像是要將她整個掐碎了一般;五年后,齊家大房敗落,齊春錦一房得以回京,周家又舉大宴,宴上人人討好攝政王,齊春錦小心翼翼地縮了縮身子:……這不是那個日日入她夢的男人嗎?-攝政王宋珩權傾朝野,俊美無雙,年近三十卻仍未娶妻,無人知曉日日神女入他夢,只是宋珩遍尋不得其人。周家宴上,眾人紛紛向他薦上自家女,宋珩一眼就瞥見了那張熟悉的面容,嬌軟動人,承三分媚意,還不等高興,面容的主人撞上他的目光,驚慌失措地往后躲了躲。宋珩:……他有這樣可怕?女主嬌媚柔軟貪吃好睡小慫包,男主表里不一每天都在被女主可愛哭的大壞蛋。 一個小甜甜日常文,炮灰死得快,配角都可愛,看女主怎麼變成團寵。免費章杠我我會杠回去哦寶貝~
28.7萬字8 44459 -
完結1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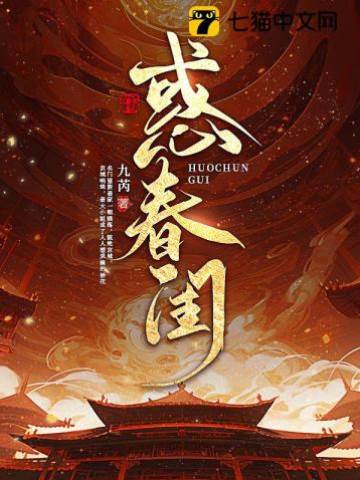
惑春閨
名門望族薑家一朝隕落,貌絕京城,京城明珠,薑大小姐成了人人想采摘的嬌花。麵對四麵楚歌,豺狼虎豹,薑梨滿果斷爬上了昔日未婚夫的馬車。退親的時候沒有想過,他會成為主宰的上位者,她卻淪為了掌中雀。以為他冷心無情是天生,直到看到他可以無條件對別人溫柔寵溺,薑梨滿才明白,他有溫情,隻是不再給她。既然再回去,那何必強求?薑梨滿心灰意冷打算離開,樓棄卻慌了……
31.5萬字8.18 789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