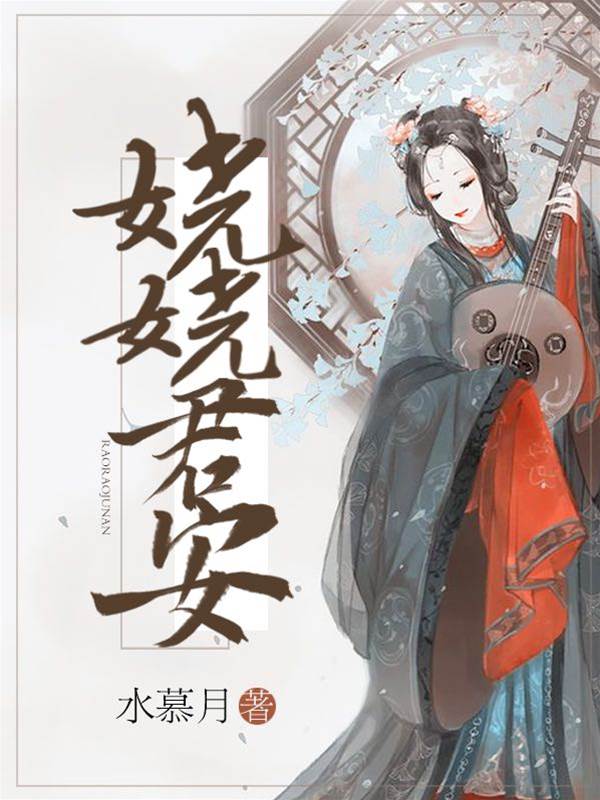《公府貴媳》 第135章 刺殺
酉時正,圣上乘坐玉輦自宮中出發,沿著中軸平康街,再繞東西市巡游觀燈。按照計劃,應是先往東市再去西市,但臨時改了計劃,便先去西市。
今年太子,秦王,蜀王一同伴駕,皇后與容貴妃陪行。太子騎馬居右,秦王蜀王居左。近來太子寵,話也多,自出宮起便與圣上大談盛世繁華。
“父皇您瞧,今年平康街與往年可有什麼不一樣?”
圣上放眼去,寬闊的平康街修整一新,燈火璀璨,兩邊商販整齊排列,個個笑容滿面,街面上舞龍舞獅上下翻飛,活靈活現的像是下一刻就能活過來飛你臉上。
繁華是繁華,熱鬧也是真熱鬧,但圣上總覺得像是搭臺唱戲,再加上那條隨時可能活過來飛臉上的龍,讓他想起了去年啟明樓上的幻龍,繼而又想起了夭折的孫子,頓時什麼心也沒了。
不過大過節的他也不好掃興,便點頭稱贊,“修整得不錯。”
這就完了?太子為了修整街道,不知道花費了多心思,就為了讓這些商販臉上由衷地洋溢出幸福喜氣的笑容,他可是整整人訓練了半個月!
“父皇,這皆是工部的功勞,兒臣為了趕在上元之前修整完畢,把他們得上冒泡,兒臣以為應當論功行賞。”
蜀王在一邊替太子把汗,這兩年國庫空虛,上個月又為著蒙古使節割了好大一塊,正是拿銀子當眼珠子的時候。今年上元節之所以選擇游街,也是為了省些銀子,誰知道太子為了討好,擅自讓工部修繕街道,說好聽點是孝順,說難聽點是沒眼力見兒。
修就罷了,還非要給工部討賞,這要不是在外面過節,太子這會兒怕是要挨罵。
Advertisement
“父皇。”秦王道,“今年西市比往年熱鬧得多,商鋪多了兩,百姓的日子眼見的好。”
秦王這話說得討巧,近年是頻繁災,但那都是北都城外的事,城鬧市區繁華不減,商鋪甚至多了起來。雖說是表面,但這個節骨眼上說百姓日子過得好,比太子那一心邀功請賞的強出了十萬八千里去。
圣上那差點兒拉下去的臉又提了起來。要麼說秦王討圣上的喜,就這冷落的時候都比太子讓人順眼。
“如此甚好。”圣上滿意地看著街市上的百姓,冷不丁的,他瞧見一個糖人的,的糖人那一個惟妙惟肖,頓時來了興致,“小十一,你去替朕買一個糖人來,就照著朕的樣子,像不像的沒關系,錢照給。”
對盛明宇來說,只要別問他朝政,讓他干什麼都行,“得嘞父皇!”
盛明宇從馬上下來,走向那商販,樂呵呵道:“聽見沒有大兄弟,給圣上好了糖人,你可就發達了。”
他大兄弟好懸沒給嚇尿了,撲通跪地討饒:“小人惶恐!小人手藝不,斷不敢龍!”
“別惶恐啊你。”蜀王忙上前將人扶起,“讓你你就,什麼樣都賞你。”
這糖人的膽子小,嚇了,起來的時候踉蹌了一下,趁機在蜀王耳邊說:“裴鈺跟秦王要在西市刺駕。”
盛明宇心里一怔,立刻明白過來,這大兄弟是裴二的人。
裴修此時人在東市,他之所以能確定裴鈺要在西市刺駕,全靠秦惠容。他拿著裴延慶的私印領家里府兵時,故意鬧得大靜,讓秦惠容知道他要去攔著裴鈺。
秦惠容在他離府之后就出了門。裴修斷定一定知道裴鈺在哪,就派人暗中跟著,這一路就跟去了西市。
Advertisement
唯一可惜的是不知道安排在西市什麼地方,裴鈺狡猾得很,他并不親自出面,只是待在酒肆中看熱鬧。
不過只要確定在西市,吳循那邊應該就能保護好。裴修現在是擔心二姑娘,到時候一旦鬧……他想到這里忽然一愣。
壞了,裴鈺很可能安排在天坊刺駕!
駕即將駕臨西市,早早就有兵跟西市的商戶打招呼,該清場的清場,該拉出來裝門面的裝門面,奏樂的奏樂,舞龍的舞龍,不消片刻就搭好了繁華盛世的臺。
西市的一家酒肆二樓,裴鈺臨窗而坐,悠閑地喝著酒。
秦惠容坐在對面,有些不放心,“能確保萬無一失嗎?我聽那意思,父親正找你呢,二弟帶了一百府兵去了東市,萬一他要是回過味來,再跑來西市如何?萬一父親去提醒了圣上又如何?”
裴鈺擺手,說多慮,“父親沒那麼傻,他興許會攔著我,但不可能去跟圣上說,說了我們宋國公府可攤上麻煩了。至于裴二,他猜到了也不會來,你想,宋國公府的府兵冒然出現在西市這什麼?這造反,到時候沒攔住我,再把他自己還有宋國公府搭進去,他除非腦子讓驢踢了。”
秦惠容知道他說得有道理,但是總有不好的預,“我在想,二弟跟父親是怎麼知道你的計劃呢?這件事只有咱們倆,還有你安排的心腹,以及秦王知道,你我不會說,還能有誰?”
這事裴鈺也納悶,他能確定自己的那些心腹不會有問題,秦王更不可能賣了自己,這豈非活見了鬼?
“總不能是那小子自己查到的吧,可查到了,卻查到了東市,這又是怎麼回事?”
秦惠容鎖眉思索,神有些凝重,“你說,有沒有可能是秦王?”
Advertisement
“這怎麼可能?”裴鈺無論如何不能相信秦王會把這件事告訴老二,“這對他沒有好啊,我安排這一切可都是為了他!”
秦惠容搖頭,“主要還是為了咱們自己,秦王不傻,這件事有風險,萬一不能功,鬧開了未見得不會影響他,而且,他也未必完全信任你。”
“可他為什麼要告訴老二?還是錯誤的信息?”
秦惠容搖頭,秦王是個瘋人,他做事的用意只有他知道,即便猜準了,也未見得能改變什麼。說白了,他們現在都已經是秦王的棋子,進是自己選的,退卻不由他們。
此時天坊外站滿了圍觀圣駕的百姓,外圍是一隊兵,帶刀帶槍的跟這街上的熱鬧多有些違和。
晏長風跟裴萱,姚文竹,還有姚文竹的兩個姐兒站在鋪子門口。兩個姐兒一直鬧著要上前去,但晏長風怕人群擁,不讓們去。
“等圣駕走了,這里就沒那麼多人了,表姨母再領你們去街上玩。”著兩個小腦袋哄著,“聽話的話,這些漂亮的燈就先讓你們挑,如何?”
兩個姐兒眼瞅著那些燈,聽表姨母這樣說也就不鬧了。
們不鬧,裴萱心里鬧,鬧二哥怎麼還不來!真是個沒腦子的,就不能直接來天坊死纏爛打嗎!
“表姨母,你看!”二姐兒指著街口過來的駕,“好大好漂亮啊!”
駕一到,軍立即開道清場,以供寬大的玉輦通過。駕過去之后,敲鑼打鼓的舞龍隊又會立刻占據街道。
皇后一直盯著天坊的花燈,待看見那花樣時新的燈時,果然眼前一亮。
皇后關注了哪家的燈,底下自有人會意,然后再傳到圣上跟前的陳公公耳朵里。陳公公會酌跟圣上提。
Advertisement
天坊如今的東家是大長公主的外孫,是宋國公的兒媳婦,是裴大人的夫人,這面子無論如何要給。
“圣上您瞧,這家的花燈真是別致,皇后娘娘跟容貴妃好像都很喜歡呢。”
圣上抬頭一看,還真是,他當即大手一揮,“那就下去瞧瞧去,那門口站的是誰,那不是姚家大姑娘,還有那誰……”
“是姚家表姑娘,裴修裴大人的夫人,晏長風。”
圣上:“哦,對,是,我想起來了,這姑娘不會行禮。”
盛明宇聽見了毫不客氣地笑了起來,“父皇您記真好。”
他陪著笑,一邊關注著四周。他一路都在琢磨裴鈺會在哪里刺駕,時時警惕著。
圣上也笑,“由不得不好,這世上朕就沒見過第二個行禮比難看的人。”
惹得邊人大笑。
晏長風見駕停在了天坊門前,心里那一個樂,駕臨過的鋪子,以后門檻怕不是要踏破了。
領著兩個姐兒退到一邊,低著頭做出恭迎之態。圣駕在前,一般人不能直視龍,可二姐兒年紀小不懂事,就想看圣上長得什麼樣,水靈靈的圓眼睛一直盯著走過來的圣上。
“那是誰家小丫頭?”圣上見了二姐兒十分喜歡,笑著問。
二姐兒立刻自報家門:“我是安侯府的馮嫣,我娘是姚家文竹。”
“原來是朕的侄,到朕邊來。”圣上稀罕二姐兒,又是姑母的重孫,便要抬舉。
姚文竹十分惶恐,擔心二姐兒沖撞圣上。而晏長風覺得這是個給們母仨抬面子的好機會,便輕輕推了一下二姐兒的肩膀。
馮嫣聽表姨母的話,上前見過圣上,聲氣的十分討人喜歡。
圣上彎腰想將抱起來,誰知就在此時,變故橫生。
一把刀自周圍的百姓中出來,直刺向圣上的前。
因著今日圣上要做出與民同樂的樣子,他周圍沒有層層護衛,只有一個陳公公。而這刺客的位置剛好在陳公公不在的那一邊,這一刀連個緩沖都沒有。
一時間驚慌聲四起。
“圣上!”
“二姐兒!”
“救駕,快救駕!”
盛明宇第一個反應過來,他上前一步先將離圣上最近的太子拉到一邊,正拽住圣上的胳膊閃躲,可沒想秦王搶先一步擋在了圣上跟前,并將馮嫣到了一邊。
那刺出來的一刀對著秦王的后背一頓,而與此同時,一繩索自百姓群中飛出來套住了刺客的脖子,像掛燈似的,噌的將人拎到了半空中。
這當街吊人的正是事先藏在百姓中的白夜司兄弟。
就在所有人以為危機過去了的時候,另一邊人群中又飛出一名刺客,他手握匕首直刺向了與圣上相距不遠的皇后。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圣上跟那個吊起來的刺客上,本沒人注意皇后。
只有晏長風看到了。覺得刺殺圣上那一刀放棄得未免太快了,幾乎是秦王的瞬間,那一刀的去勢就弱了,不像是為了刺殺圣上。
腦海中閃過的第一個念頭是刺客在聲東擊西,于是一雙眼睛不假思索地轉向了另外兩個貴人,剛巧就捕捉到了這一幕。
可惜,距離不近,恐怕很難及時阻止。
猜你喜歡
-
完結389 章

農門姐弟不簡單
穿越而來,倒霉透頂,原身爹爹戰亂而死,送書信回家後,身懷六甲的娘親一聽原地發作,立即生產,結果難產大出血而亡。 謝繁星看著一個個餓的瘦骨嶙峋還有嗷嗷待哺的小弟,她擼起袖子就是乾,看著滿山遍野沒人吃的菜,有這些東西吃,還會餓肚子、會瘦成這樣? 本以為她這是要帶著弟妹努力過活,改變生活過上好日子的,結果,弟妹沒一個簡單的。 本文又名《弟妹不簡單》《弟妹養成記》《弟妹都是大佬》《全家都是吃貨》
70.4萬字8.18 35613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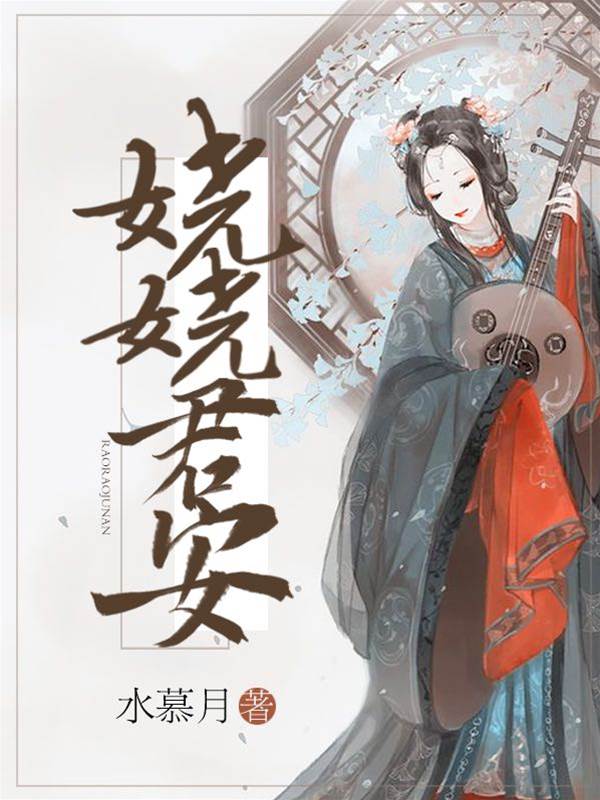
嬈嬈君安
原想著今生再無瓜葛,可那驚馬的剎那芳華間,一切又回到了起點,今生他耍了點小心機,在守護她的道路上,先插了隊,江山要,她也絕不放棄。說好的太子斷袖呢!怎麼動不動就要把自己撲倒?說好的太子殘暴呢!這整天獻溫情的又是誰?誰說東宮的鏡臺不好,那些美男子可賞心悅目了,什麼?東宮還可以在外麵開府,殿下求你了,臣妾可舍不得鏡臺了。
16.6萬字8 13926 -
完結171 章

錯撿瘋犬后
病嬌太子(齊褚)VS聰慧嬌女(許念),堰都新帝齊褚,生得一張美面,卻心狠手辣,陰鷙暴虐,殺兄弒父登上高位。一生無所懼,亦無德所制,瘋得毫無人性。虞王齊玹,他的孿生兄長,皎皎如月,最是溫潤良善之人。只因相貌相似,就被他毀之容貌,折磨致死。為求活命,虞王妃許念被迫委身于他。不過幾年,便香消玉殞。一朝重生,許念仍是國公府嬌女,她不知道齊褚在何處,卻先遇到前世短命夫君虞王齊玹。他流落在外,滿身血污,被人套上鎖鏈,按于泥污之中,奮力掙扎。想到他前世儒雅溫良風貌,若是成君,必能好過泯滅人性,大開殺戒的齊褚。許念把他撿回府中,噓寒問暖,百般照料,他也聽話乖巧,恰到好處地長成了許念希望的樣子。可那雙朗目卻始終透不進光,幽深攝人,教著教著,事情也越發詭異起來,嗜血冰冷的眼神,怎麼那麼像未來暴君齊褚呢?群狼環伺,野狗欺辱時,齊褚遇到了許念,她伸出手,擦干凈他指尖的血污,讓他嘗到了世間的第一份好。他用著齊玹的名頭,精準偽裝成許念最喜歡的樣子。血腥臟晦藏在假皮之下,他愿意一直裝下去。可有一天,真正的齊玹來了,許念嚴詞厲色地趕他走。天光暗了,陰郁的狼張開獠牙。齊褚沉著眸伸出手:“念念,過來!”
26萬字8 6846 -
完結232 章

陛下輕點罰,宮女她說懷了你的崽
為了活命,我爬上龍床。皇上不喜,但念在肌膚之親,勉強保了我一條性命。他每回瞧我,都是冷冷淡淡,嘲弄地斥一聲“蠢死了。”我垂頭不語,謹記自己的身份,從不僭越。堂堂九五至尊,又怎會在意低賤的宮婢呢?
43.7萬字8.18 509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