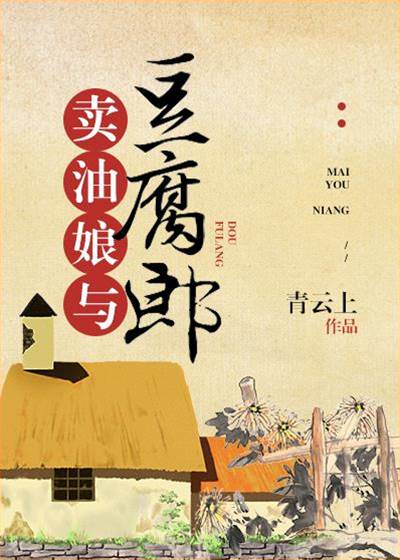《權傾裙下》 第55章 第55章 少淵
聞人藺近來不知在忙什麼,已連著數晚不曾來東宮監督「學習」。
趙嫣忙著籌備皇后壽宴的大小事宜,也就樂得個小懶,將沒看完的那兩本鎖屜中,拋諸腦後。
明日事來明日愁,等聞人藺哪天想起檢查功課了再說。
六月中,殿中靜謐,冰鑒的微涼難抵中伏酷暑。
趙嫣捧著兩三張玉佩花紋的草圖,夏衫下還裹著不氣的束,烙餅似的在簟席上翻滾。一旁的案幾上,刻刀、鉸雜陳,錦盒中擺著幾塊極佳的玉料。
流螢握雙手進殿,接過李浮手中的扇子,輕輕為趙嫣扇風納涼。
李浮很有眼力見地退下,順便掩上了殿門。
「有柳白微的消息了?」
趙嫣知曉流螢有要事要稟,問道。
流螢搖了搖頭,低聲道:「是娘娘邊的何史來過,說潁川老郡王昨日已攜庶孫京,意在求聖上恩旨,讓小王孫認祖歸宗。」
「潁川郡王?」
趙嫣搜羅了一番朝中宗室名錄,想起來了。
這位老郡王勉強算是父皇的堂叔,年近古稀,膝下只有一個獨子,且這位獨子十年前就因病故去了。
「我記得潁川王世子故去得突然,並未留後,這個小王孫是從何來的?」
「據聞是外邊子生的,前不久才認回。」
「偏偏是這種時候……從哪裡撿回的?」
「暫且未知,老郡王將消息滿得。」
趙嫣想了想,角一提道:「潁川郡王雖與父皇同宗同姓,但畢竟已出了五代,空爵位而已,並無實權。多個小王孫,也不會對東宮造影響。」
倒是許婉儀肚裡那個,還未出生就已經鬧得滿城風雨。
流螢道:「雖說如此,但這位小王孫畢竟出現得太過巧合,又急著進宮來,娘娘擔心事出蹊蹺,讓殿下多加小心。」
Advertisement
趙嫣點頭以示明了,而後想起什麼,從枕下出趙衍留的那塊蓮花玉佩,以指了上面的輕微的裂紋。
「就選這個花樣吧。」
而起,下榻行至案幾后坐著,比對著從錦盒中挑了塊一致的玉料。
趙衍素蓮紋,以他的名義親手雕琢贈送,母后應該會喜歡吧。
趙嫣心想,就當是為趙衍盡孝了。
……
「去年冬天苦寒,非但叛黨熬不住,城外流民也不知凍死多。誰承想夏了又熱這樣……」
崇文殿中,裴颯挽袖袒兩條手臂納涼,斷眉擰一團。
趙嫣以扇扇風,裳裹得嚴實不說,還有束層層纏繞,亦憋得悶氣短。
這天氣,著實反常。
正想著,李浮自殿外,悄聲請示道:「殿下,潁川小王孫求見。」
「誰?」
「潁川老郡王剛認祖歸宗的庶孫。」
趙嫣和潁川老郡王面都沒見過,與小王孫更是不,不由訝然:「他求見孤作甚?」
李浮環顧殿端茶送水的宮侍們,言又止道:「您見了便知。」
趙嫣沒想到這麼快就會和這位小王孫打照面,對方到底意何為,一見便知分曉。
此時離聞人藺的武課還有一刻鐘,思索片刻,吩咐道:「你讓他去後殿等著。」
趙嫣穿過長廊,朝後殿行去。
房舍門扇半掩,約可見一位著月白緞滾金邊的貴氣年臨窗而立,環抱著雙臂,高束的馬尾隨著他輕點的靴尖微微抖,似乎等得有些不耐。
脾氣倒是大,趙嫣仿著「太子」的神態,溫聲開口道:「聽聞你找孤……」
年聞聲轉過頭來,趙嫣未說完的話語戛然而止。
四目相對,趙嫣裝出的溫和霎時崩裂,半晌,睜大眼眸道:「怎麼是你!?」
Advertisement
潁川小王孫……不,柳白微放下環的雙手,所有的焦躁不耐都在見到趙嫣的那一瞬煙消雲散。
他微抬下頜,長眉習慣一挑,張揚道:「我說過,會回來找殿下的。」
不遠宮牆的樹蔭上,一隻通油黑的碧眼烏雲弓背抻了個懶腰,邁著優雅的步伐穿梭於錯的枝丫間,而後縱一躍,踩著飛翼翹起的屋檐往上,翻闌干中,稔地蹭了蹭那雙修長筆的靴。
「是嗎,姓柳的果真選擇回來了。」
聞人藺坐於椅中,從隨的小袋中出一顆乾投喂玄貓,容逆著,不見半點波瀾。
「那真是個魂不散的狐貍,換了皮囊,搖一變了潁川小王孫。」
張滄盯著崇文殿後殿的廊下,義憤填膺道,「王爺何不用點手段,讓他小王孫的份作廢?反正流亡在外這麼多年,誰知他是真是假。」
聞人藺著黑貓的皮,睨向張滄:「聰明。」
張滄嘿嘿一笑:「那當然……」
察覺到主子漸沉的目,張滄笑容凍結,訕訕低頭道:「卑職僭越,又教王爺做事了。」
他認錯快,可腦子轉得不快。
以前柳白微扮子黏在小太子邊時,王爺眼裡容不得沙子,不惜得罪小太子也要將姓柳的假死弄走,怎麼這會兒反倒不著急了?
張滄琢磨著,忽然想到什麼,做出恍然的樣子道:「卑職明白了!那狐貍既認回了小王孫的份,就算與太子是同姓同宗。本朝禮法,同宗同姓之人哪怕相隔十七八代,也是不能在一起的!」
還得是王爺高明啊!兵不刃,就徹底絕了那男狐貍的心思!
張滄佩服得五投地。
他這邊排山倒海,聞人藺倒是淡然。
他以帕子拭凈了手,垂眸轉著霜白修長的手掌,忽然想換一樣更細膩的東西。
Advertisement
遂轉下樓,朝崇文殿而去。
廊下,趙嫣與柳白微比肩而立,聽檐鈴丁零作響。
「老爺子去太極殿面聖了,估著要候上一陣,我便自己溜來此。」
柳白微換了雲緞錦,金白二襯得他紅齒白,極富年氣,比扮裝、做儒生時大為不同。
他哼了聲:「明德館的燈要亮著,可我也不願如深閨怨婦一般翹首等候殿下音信,只能出此下策了。」
趙嫣著實用了好一會兒,才接眼前所見。
「到底怎麼回事?」
不知從何問起,「你不是姓柳嗎?」
柳白微似是難以啟齒,張了張,才坦誠道:「柳,是我的母姓。」
潁川王世子為老郡王獨子,在當地一手遮天,看上哪個人也不過是一句話的事,輕而易舉就能奪去一個的清白。
那是私塾夫子的兒,生得如蘭花般清婉麗,卻無端遭此橫禍。世子吃飽饜足,拍拍屁走人,轉頭迎娶了門當戶對的士族貴,連個名分都沒給柳家姑娘,氣得柳夫子嘔而亡。
柳白微嘲笑:這些惡霸行徑放在話本中都嫌老套,而可笑的是,它竟是真真實實發生過的噩夢。
柳家姑娘變賣家產投靠親戚,拚死生下了兒子,本以為會這樣了此殘生,誰知潁川王世子作孽多端遭了報應,突發惡疾而亡。
郡王府絕了后,一旦老郡王撒手人寰,則朝廷將收回潁川郡王府的爵位與俸祿。
皇家祿蠹,怎麼可能放棄到手的?
世子妃這才想起,丈夫還有個留在外的私生孽種。
派人追殺柳家婦,想要去母留子,穩住郡王府基業。
料那婦人卻帶著兒子逃了出來,於傾盆的雨夜,拼盡最後一口氣,將年僅九歲的兒子託付給先父好友臨江先生。
Advertisement
「我改名換姓,跟著臨江先生遊歷七年,潁川郡王府從未停止搜尋我的下落,直到天佑十六年,臨江先生舉薦我明德館。」
柳白微背靠著闌干,平靜道,「第二年春,我遇見了下榻明德館的太子殿下。」
他恨極了這些摧毀了柳家的皇親權貴,也恨極了自己上那一半骯髒的脈。他畢生所求,唯見天日昭昭,暗夜魍魎無從遁形,以告母親、外祖父亡魂。
是以和太子殿下談的第一天,他就知自己跟對了人。
趙嫣忽而想起,在玉泉宮聽雨軒,柳白微向吐「拂燈」真相時,的確提到過:「我來明德書院,本就是為了藏。能有機會藏到東宮之中,自是更好。」
只是那時的趙嫣阿兄一行人飛蛾撲火般的純粹風骨所震撼,心中悲翻湧,一時忘了深究柳白微那句剖白的深意。
柳白微別過頭,低聲解釋道:「我並非刻意瞞。後來,也想過向殿下坦白世……」
可後來鏡鑒樓點燈,見王裕,又得知肅王欺負殿下,繼而被迫假死……事樁樁件件湧來,他終是喪失了剖白的良機。
聽到這,趙嫣似乎明白了什麼。
也靠著闌干,通的眼眸向邊這個悉而又陌生的倨傲年,輕聲問:「你回來,是為了東宮嗎?」
柳白微所有的顛沛流離都拜潁川郡王府所賜,他應是,極其厭惡這個「小王孫」的稱謂。
柳白微一怔,隨即失笑,下意識要去攬趙嫣的肩。
而後反應過來,他如今的份已經不能再親昵地去勾殿下的袖邊或肩頭了。
抬起的手於空中轉了個彎,他了自己的鼻尖道:「也不全為了名正言順見殿下。我只是想通了一些事,有現的權勢可以利用,何樂而不為。」
趙嫣彷彿看他的心事,道:「你不必勉強自己。」
「殿下此言,是在擔心我嗎?」
柳白以手指心,清朗道,「殿下放心,我只是換個份和殿下並肩作戰罷了。我的心志,不會因此而改變。」
趙嫣明白,可世間最難能可貴的,便是『堅守』二字。
柳白微如此,死去的趙衍與拂燈者們亦是如此。
笑了聲,認真道:「柳白微,你是真有年意氣,君子之風。」
一笑,雲間所有璀璨的都落在了的眸中。
柳白微頓了頓,而後不甚自然地別開視線,著自己的腳尖道:「殿下這般謬讚,也不怕良心痛。世可憐並非自甘沉淪的借口,我拚命抗爭,就是為了不為作惡之人,怎能因自己居高位而忘記當初的信念。」
然深究起來,到底是有憾的。
柳白微有些失神:「我常說要替趙衍照顧殿下,如今,倒真一家人了……」
「為一家人也無甚不好,算起來,我得你一聲堂兄呢。」
「都六七代開外的遠親了,算什麼堂兄?」
柳白微似是抵,又似是不甘,咬牙切齒的模樣頗有幾分「柳姬」的影子。
然而同姓已是不爭的事實,他只得悻悻斷了念想。
趙嫣看著他一會鼓氣,一會泄氣,不由好笑:「父皇怎麼說?」
柳白微興味索然道:「老爺子求皇上給我賜個字,就算認祖歸宗了。」
「這麼早就要取字了?」趙嫣訝然。
記得柳白微還未到行冠禮取字的年紀。
柳白微解釋:「老爺子急需我撐當門面,故而未及二十歲也可取字。」
趙嫣瞭然,想起舅舅寧侯魏琰十四歲為家主,十五歲就取字為「澤然」。
聞人藺呢?
好像從未聽誰過聞人藺的字,儘管他早兩三年就及冠了。
正想著,柳白微想起此行的真正目的,打斷的思緒道:「殿下還在查那毒香的來源?」
趙嫣回神,凝神道:「是。」
果然如此,柳白微正。
「我發現連潁川郡王府都在求丹問葯,和神教道士有往來,可見這群妖道的鬚已經遍布朝野。」
雲翳掠過,蟬鳴低伏,柳白微低嗓音道,「我總覺得近期會有大事發生,殿下務必小心。」
趙嫣頷首:「我知道。文脈乃一國之魂,明德館那邊就給你了。」
二人換了報,便見一名侍遠遠地走來。
柳白微知道那侍是來尋自己的,站直子道:「我該走了。」
話雖如此,他雙腳卻沒捨得離開分毫。
趙嫣頷首說「好」。
柳白微張了張,似乎想說什麼,最終只別過頭說了句:「我會常來看殿下的。」
說畢行了個儒生禮,深吸一口氣方轉離開。
趙嫣回到崇文殿中,遲了半盞茶時間。
猜你喜歡
-
完結491 章

鳳花錦
仵作女兒花蕎,身世成謎,為何屢屢付出人命代價? 養父穿越而來,因知歷史,如何逃過重重追捕回歸? 生父尊貴無比,一朝暴斃,緣何長兄堂兄皆有嫌疑? 從共同斷案到謀逆造反,因身份反目; 從親如朋友到互撕敵人,為立場成仇。 富貴既如草芥, 何不快意江湖?
90萬字8 10798 -
完結536 章

傾城醫妃不好惹
一朝穿越,成了不受寵的秦王妃,人人可以欺辱,以為本王妃是吃素的嗎?“竟敢對本王下藥,休想讓本王碰你....”“不是,這一切都是陰謀....”
97.2萬字8 114912 -
完結492 章
穿越醫妃不好惹
穿越前,她是又颯又爽的女軍醫,穿越后,她竟成了沒人疼的小白菜,從棺材里爬出來,斗后媽,氣渣爹。夫婿要悔婚?太好了!說她是妖孽?你再說一個試試?說她不配為后?那我做妃總可以了吧。只是到了晚上,某皇帝眨巴著眼睛跪在搓衣板上,一字一頓地說天下無后是怎麼回事?
88.1萬字8 19921 -
完結14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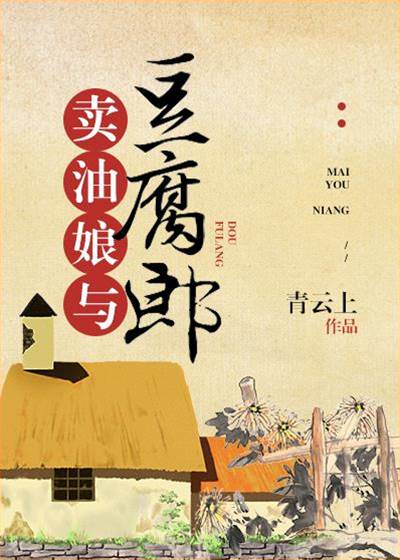
賣油娘與豆腐郎
每天早上6點準時更新,風雨無阻~ 失父之後,梅香不再整日龜縮在家做飯繡花,開始下田地、管油坊,打退了許多想來占便宜的豺狼。 威名大盛的梅香,從此活得痛快敞亮,也因此被長舌婦們說三道四,最終和未婚夫大路朝天、各走一邊。 豆腐郎黃茂林搓搓手,梅香,嫁給我好不好,我就缺個你這樣潑辣能幹的婆娘,跟我一起防備我那一肚子心眼的後娘。 梅香:我才不要天天跟你吃豆腐渣! 茂林:不不不
77.7萬字8 12157 -
完結257 章

春水搖
赫崢厭惡雲映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她是雲家失而復得的唯一嫡女,是這顯赫世家裏說一不二的掌上明珠。 她一回來便處處纏着他,後來又因爲一場精心設計的“意外”,雲赫兩家就這樣草率的結了親。 她貌美,溫柔,配合他的所有的惡趣味,不管他說出怎樣的羞辱之言,她都會溫和應下,然後仰頭吻他,輕聲道:“小玉哥哥,別生氣。” 赫崢表字祈玉,她未經允許,從一開始就這樣叫他,讓赫崢不滿了很久。 他以爲他跟雲映會互相折磨到底。 直到一日宮宴,不久前一舉成名的新科進士立於臺下,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包括雲映,她脊背挺直,定定的看他,連赫崢叫她她都沒聽見。 赫崢看向那位新晉榜首。 與他七分相似。 聽說他姓寧,單名一個遇。
38.5萬字8.18 469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