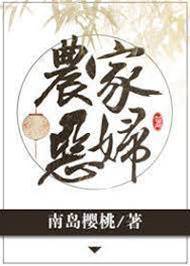《侯府長媳》 075生死未卜
["朝堂上一片烏煙瘴氣人心惶惶,安奉候府裏可謂兵荒馬,有謝景翕跟侯爺在的時候,外院都能穩得住,但聖上一道詔令下來,侯爺跟顧恒都要進宮,這下剩了一家子的婦人,頓時就顯的沒了章法。
最關鍵的是,沒有人知曉到底發生了什麽,這種時候傳侯爺跟二爺進宮,是還是提審還是幹脆就回不來,沒有人說的清楚,侯府上下一時間如臨大敵,大姐兒夭折的事竟是沒人再有暇顧及,任由停放在屋子裏無人敢。
侯爺臨走的時候安排了他的人守在前院,也沒來得及跟謝景翕囑咐幾句,隻盼謝景翕能撐住才好,畢竟侯爺心裏清楚,單靠曾氏一個人,侯府是穩不住的。
實際況是,曾氏不穩不住侯府,自己都快穩不住了,方才因為大姐兒夭折的事已經備打擊傷心過度,這下侯爺跟顧恒一走,心裏的主心骨都要塌了,侯府的一家之主生死未卜,府裏的家下人也人心不穩,有那些主意打的早的,已經開始準備跟侯府劃清界限逃之夭夭了。
曾氏這下在床上躺不住了,喊了謝景翕過來就開始哭,“老大媳婦這可如何是好,侯爺跟恒兒都召進宮,一定沒什麽好事,萬一關起來用私刑,他們兩個怕是兇多吉啊,大姐兒剛剛沒了,我們侯府後繼無人,真真是天要亡我顧家啊!”
謝景翕簡直無語,曾氏想的可真遠,一家主母都這樣了,家裏其他人不生二心才怪,謝景翕跟芹打了個眼,“看好了母親屋裏的人,別們出去胡說八道擾人心。”
“是,大,我醒的。”
好在芹還算懂事,沒跟著曾氏一起犯糊塗,謝景翕扶住傷心絕的曾氏重新趟回床上,“母親先莫慌,聖上不過是請父親跟小叔進宮問話罷了,不會有什麽事的,咱們侯府幾代人忠心耿耿,聖上不會輕易傷了人心的,恐怕是外頭有什麽誤會,問清楚了就沒事了,您才發了病,先顧著子要,要不父親跟小叔也不能放心您不是。”
Advertisement
曾氏就隻是抹眼淚,“你說如今家裏沒個主事的男人,這一大家子可如何是好,大姐兒還停在那不能發喪,我可憐的大姐兒啊……”
“母親放心便是,家裏還有趙家跟媳婦在呢,出不了子,大姐兒出殯的事我會安排,現的棺槨在,停靈幾日也不礙事的。”
還是上次大哥兒出事的時候趕著做了兩個放在家裏,生怕再有這樣的急事來不及準備,沒想到不過一年,就真的用上了,說來也是令人唏噓。大姐兒的無人敢,生怕是中了什麽要命的毒,萬一給自己沾上就不好了,連謝景琪這個當娘的都不敢,謝景翕隻好親自將大姐兒抱出來,跟方玳一起將大姐收斂了。
謝景翕好說歹說的把曾氏哄住,最後幹脆做主開了一副安神藥給灌下去,讓睡一會清靜,但侯府這下打著出走心思的人越來越多,剛剛下去的象又開始鬧騰。趙家是侯爺的心腹,奉命守住前院,一但發現有那生了二心的家奴,立刻就地嚴懲,還做主就地格殺了一個帶頭鬧事的,這一見,其他的人頓時不敢鬧了。
到底是跟了侯爺多年的人,殺伐果決先斬後奏,理幹淨過來跟謝景翕回報的時候,謝景翕讚許的點點頭,“幸而有趙管家在,如今府裏人心不穩,是該震懾一下,等到事了解了,再把人打發了便是,既然對侯府生了二心,也就不必顧忌旁的,隻是張弛有度,也不必過於繃,剩下的事,我會善後的。”
趙家心中放心稍許,侯爺臨走還囑咐他,若是大立不起來,就由他便宜行事,如今看來,大是個穩得住的,後院有在,當是出不了大子。
有趙家震懾在前,侯府上下安穩不,但難免戰戰兢兢,於是謝景翕吩咐各的管事媽媽,府一切照舊,一日三餐如常,並每人各添二兩恤銀子以示,皆從的賬上出,府裏一時才又重新安定下來。
Advertisement
倒不是謝景翕冤大頭,侯府庫裏一下出這麽多銀子,各種因由皆要記的清楚詳盡不說,還難免被人詬病,這種時候還拿侯府的銀子做好人,正經的吃力不討好,索花點銀子買個清靜。
眼下讓謝景翕頭疼的不是侯府,而是顧昀的下落,心裏清楚此事必定因顧昀而起,沒有侯府什麽事,隻要顧昀沒事,侯爺跟顧恒轉眼就能安穩的送回來,可是眼見著天兒都要黑了,跑出去的趙章還是沒有靜,謝景翕便有些坐不住。
“方玳,可有法子混出去?”
方玳一直守著謝景翕,似乎看出了的心思,忙道:“夫人不必涉險,現在咱們院子外麵看守的人最多,混不出去不說,您一走,侯府必定就了,何況咱們就是出去了,也是沒頭沒腦,不如等趙章的消息,如果我猜的沒錯,後半夜他就應當回來了。”
謝景翕的確想跑一趟晉王府,覺的晉王定是知的,但這樣冒然跑過去到底有些莽撞,萬一因此壞了他們的大事,反倒弄巧拙,於是隻好打消混出去的念頭。顧昀現在沒有消息,至能確定沒有在兵部出事,隻要他跑了出去,便隻能等消息了。
“也罷,累了一天,你們也都先去休息,明天還不知道有何事,不能把子熬壞了。”
謝景翕打發他們都去休息,自己躺在床上卻怎麽也睡不著,腦袋哄哄的都是事,實在熬不住的時候就點了一安神香,可剛點上沒多一會就又轉去掐了,想到要盡快調理子幫顧昀添個娃娃,狠狠心,就把安神香全部都浸在了水裏。
隻是這樣一來,必定是睡的不踏實,到了後半夜,窗外又約有了靜,謝景翕上了發條似的猛地睜開眼,知道是趙章回來了。
Advertisement
謝景翕不敢燃燈,借著屋外昏暗的,悄悄給趙章開了門進來,一直守在外屋的方玳聽見響,也跟著一起進到謝景翕的裏屋。
“趙章,況如何?”
“夫人,我打聽到了大爺的消息。”趙章低聲音道:“大爺是在安次縣找到的,聽聞是誤打誤撞找到了一個火藥庫,懷疑是太子的手筆,此事幹係重大,可能要拖些時日才能回來,聖上也派了人過去,大爺我回來給您報個平安。”
太子的火藥庫?謝景翕對朝堂的事了解不深,但也不至於什麽都不知道,太子是有野心不假,但火藥庫這樣這種幹係掉腦袋的地方,怎麽會被顧昀輕易找到?
“你跟我說實話,大爺當真無事?”
謝景翕盯著趙章,暗下的眸子顯的格外晶亮,趙章有些不敢看,支支吾吾道:“不瞞夫人,大爺是追著太子的人一路跟到那邊的,原本有些兇險,但正巧晉王也在那邊,支援及時,隻是見了些,並無要,大爺怕您胡思想,就不讓我告訴你,我一會還要趕去嵇老爺子那邊取些藥帶過去。”
趙章說的半真半假,至打消了謝景翕五六分的疑慮,但這幾句話並不足以表達顧昀這一路兇險的萬分之一。
事還得從兵部炸之前說起,的確是有人買通兵部的人,想蓄意引起兵部炸,但要炸的並非是兵部的火藥庫,而是顧昀,再順便栽贓個私造火藥的罪名,還能順手牽下幾隻倒黴羊來。
也是顧昀運氣好,他這幾日一直在駕部幫忙,人鮮待在兵籍庫,偶爾回來取些資料,順便幫楊壽禮理一些事,正巧就遇見了鬼鬼祟祟在庫房外徘徊的同僚,這位同僚是庫部一個小主事,顧昀隻依稀記得他姓李,正準備上前與他打招呼,那位李主事卻撒丫子就跑。
Advertisement
這一看就是有鬼啊,顧昀怕他了什麽東西,於是就上前去追,可是剛跑出沒多遠,就聽見一聲巨響,回頭一看,是庫部的方向發生了炸,顧昀直覺以為一定是這個李主事幹了什麽見不得人的事,更是對其追不舍。
李主事一路逃出城外,卻並沒發現後麵跟著的顧昀,隻顧一路逃命,最後逃到安次縣附近,隻進了一個人跡罕至,顧昀仔細觀察了一下,覺著此路線有些眼。
這幾日盛鸞將軍回京,聖上準備親迎接,京城外的路線都是要事先安排好的,從天津港下船開始,盛將軍所要走的路線,在什麽地方駐軍,在什麽地方繳械,顧昀心裏門清,而這位李主事所到之,正巧就離盛將軍大軍停步駐紮的地方不遠,故而顧昀便猜測其中定有貓膩。
正巧前短時間此流傳過鬧鬼的言論,說經常有人發現這裏半夜三更有鬼火重重,有些膽大的人會冒險過來看,但據說第二天都莫名其妙的死了,於是這裏就了名副其實的地,輕易不敢有人來。
猜你喜歡
-
完結540 章
醫品庶女代嫁妃
中西醫學博士穿越成宰相府庶出五小姐,憑藉著前世所學的武功和醫術,懲治嫡出姐姐,鬥倒嫡母,本以爲一切都做得神不知鬼不覺,卻早已被某個腹黑深沉的傢伙所看透。既然如此,那不妨一起聯手,在這個陰謀環繞暗殺遍地的世界裡,我助你成就偉業,你護我世世生生!
97.3萬字8 169968 -
完結177 章

重生之賢妻難為
上一世,她是將軍府的正室夫人,卻獨守空房半生,最後落得個被休棄的恥辱。直到她年過四十遇見了他,一見鍾情後,才發現遇他為時已晚。 今世,上天待她不薄,重生那日,她便發誓,此生此世必要與他攜手一世,為他傾盡一生。
39.6萬字5 7742 -
完結15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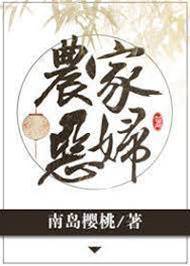
農家惡婦
何娇杏貌若春花,偏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恶女,一把怪力,堪比耕牛。男人家眼馋她的多,有胆去碰的一个没有。 别家姑娘打从十四五岁就有人上门说亲,她单到十八才等来个媒人,说的是河对面程来喜家三儿子——程家兴。 程家兴在周围这片也是名人。 生得一副俊模样,结果好吃懒做,是个闲能上山打鸟下河摸鱼的乡下混混。
48.4萬字8 670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