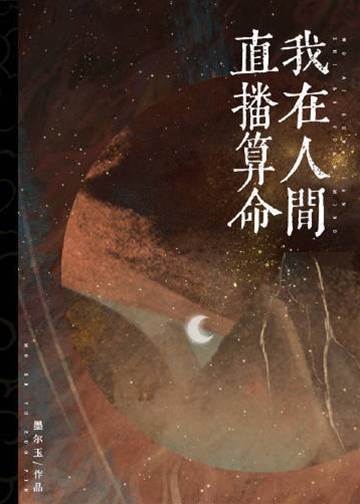《跪求老祖宗好好做人》 第四百三十五章 西塢村【一十二】
村的道路是石子鋪設而的,間隙裡長滿了雜草,足有膝蓋高,因季節原因而枯萎泛黃。
沿著道路往前走,是錯落有致的房屋,皆是頗有年代的木頭房,有些房屋早已塌陷,雜草叢生,滿是荒涼景致。
放眼看去,毫無生氣。
不見一人蹤跡。
四周依舊寂靜得可怕。
墨傾走在進村的道路上,冷不丁覺到刺骨的寒意,余一瞥,捕捉到一木屋牆側雜草中的黑影,但定睛去看時那黑影一掠而過。
速度快得出奇。
墨傾神一凜,當即追了上去。
除了進村的道路,其他的道路都已荒蕪,墨傾在其中穿梭,因不悉地形,很快就失了黑影的蹤跡。
「啊呀——你嚇我一跳!」
正在此時,墨傾聽到一陣悉的聲音。
心下疑,墨傾往前走了一段距離,赫然見到一木屋門前,蹲著宋一源那個夯貨。
天依舊昏暗,有一盞油燈照明。
Advertisement
宋一源正蹲在一個水缸旁淘米,手裡是個高鍋,除了服有些褶皺、破舊,沒有一點傷的樣子,臉蛋白白淨淨的,發都沒。
他不知在跟誰講話:「就剩這點米了,早上只能喝粥,我說你……剛剛做什麼去了?」
「……」
沒有人回應他。
木屋建築是兩層,中間是大廳,木門檻又高又寬,左右兩側都有房間,在右側,加了一個敞開的小廚房。
廚房除了一個土灶、一個大水缸,就簡單的幾樣品。
墨傾觀察了下宋一源的神狀態,確定他還算正常後,就直接走進了宋一源的視野。
「宋老師。」墨傾喊。
冷不丁聽到這麼一聲,宋一源被嚇了一跳,差點把高鍋給扔了。
但很快,在看清墨傾的模樣後,驚訝就轉化為驚喜。
「墨傾!」
宋一源將高鍋一放,立即站起來。
「你終於來了!」他張了一圈,發現沒有其他人的影,「江刻呢?」
Advertisement
想到被自己扔到營地的江刻,墨傾停頓了一下,很快就轉移話題:「他沒來。你怎麼會在這裡?遲時呢?」
頓了一秒,又皺眉:「……你剛剛在跟誰說話?」
「我——」
宋一源回頭看了一眼。
他了下手,然後往裡走了兩步,拿出個小木凳過來:「來,你先坐,我慢慢跟你說。」
墨傾沒,靜靜地看著他:「就這麼說吧。」
在大霧裡忽然消失的人,過了幾天后出現在西塢村,還把這兒當自己家一樣……
這事過於邪門。
墨傾在無法確定宋一源毫無問題的況下,斷然不能放松警惕。
宋一源怔了下,算明白過來,乾脆自己坐下了:「況是這樣的……」
宋一源起了個頭就卡了。
他眼睛眨了眨,跟墨傾面面相覷幾秒,然後攤手:「我一覺醒來,就到了西塢村。」
墨傾神的警惕更甚:「一覺醒來?」
Advertisement
「真的,」宋一源抬手了鼻尖,「過程我都不知道。」
「遲時呢?」
「他跟我應該是一起來的,但我只是醒來後見了他一面,他也什麼都沒說,給我介紹了一個朋友,讓我在這裡等你們過來。」宋一源說。
「朋友?」
墨傾頭一偏,見到側門落下的虛影。
「對……」宋一源點點頭,有些含糊、謹慎
地提醒,「他吧……你可能需要一點心理準備。」
墨傾瞇了瞇眼,語氣果斷:「他就是霧裡的怪吧?」
「不不不!」
宋一源連忙道。
可很快的,宋一源又糾結起來:「怎麼說呢,也不能說完全不是。」
「婆婆媽媽。」墨傾說,「把人出來。」
「……」
宋一源被噎了噎,最後眉眼一耷拉,回過頭看向側門。
「阿布,你出來吧。」宋一源語氣緩和地說,「就是我跟你說的朋友。」
墨傾眼皮一抬:「他知道。他把我引過來的。」
Advertisement
側門外落下的虛影了。
很快, 那虛影從黑暗中走出來。
當墨傾看清的那一刻,沒來由愣住。
那是一個高三米、手長腳長、酷似人類卻遠超於固有的人類特征的……人——如果還能這麼稱呼的話。
他皮乾的,漆黑實,沒穿鞋,服破破爛爛的,有五,可又跟人類沾不著邊,細長的眼眶裡那鮮紅似的眸子,讓墨傾似曾相識,又不寒而栗。
他著墨傾,眼神赤的,著好奇、探究。
可墨傾分明又能覺到一點什麼。
——那是一雙屬於人類的眼睛。
良久,墨傾徐徐問:「他是什麼?」
宋一源走到「阿布」邊,說:「遲時說,他是人。如果西塢村外面那些東西屬於怪的話,那他就是介於人和怪之間的存在。」
猜你喜歡
-
完結797 章

厲少,你老婆又想離婚了!
蘇可曼曾經以為,她要嫁的男人,一定是溫潤如玉這款。可婚後,他惡狠狠地將她抵在牆角,咬牙切齒地說:「我對你沒興趣!」更過分的是他提出霸王條款:不準碰他、不準抱他、更不準親他。蘇可曼見識了他的冷漠無情,發現他就是一塊怎麼也捂不熱的石頭。她將離婚協議拍在桌子上,底氣十足:「老孃不幹了,我要和你離婚!」他一本正經道:「離婚?門都沒有窗更沒有!」後來小包子出生,她揚起小臉緊張地問:「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喜歡我的?」男人瀲灧眸光一閃:「寶貝兒別鬧,咱們該生二胎了!」
180.6萬字8 31774 -
完結914 章
重生八零辣妻當家
許卿直到死才發現,她感恩的後媽其實才是最蛇蠍心腸的那一個!毀她人生,斷她幸福,讓她從此在地獄中痛苦活著。一朝重生歸來: 許卿手握先機先虐渣,腳踩仇人吊打白蓮。還要找前世葬她的男人報恩。只是前世那個冷漠的男人好像有些不一樣了, 第二次見面,就把紅通通的存摺遞了過來……
161.9萬字8 137690 -
完結23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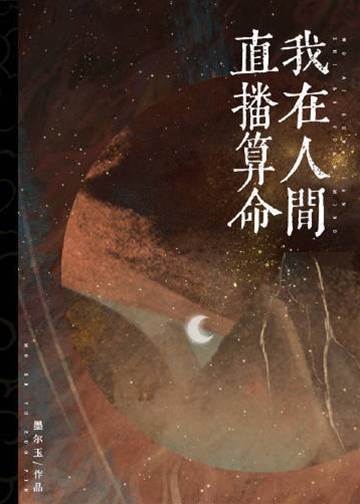
我在人間直播算命[玄學]
安如故畢業回村,繼承了一個道觀。道觀古樸又肅穆,卻游客寥寥,一點香火錢也沒有。聽說網上做直播賺錢,她于是也開始做直播。但她的直播不是唱歌跳舞,而是在直播間給人算命。…
134.6萬字8 964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