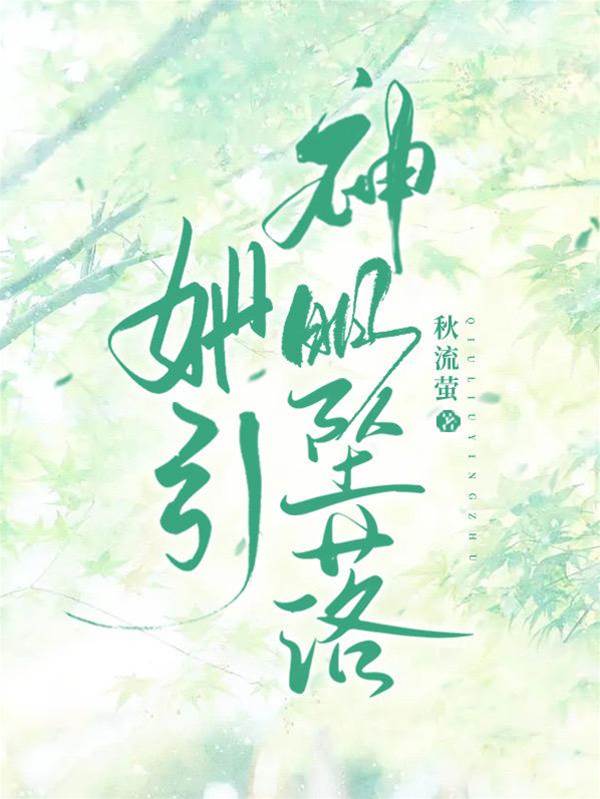《我閉眼了,你親吧》 第60章
仿佛回到了那個夏夜。
阮枝想,原來真的是見過他的。
“哥哥。”
阮枝輕聲喊。
面前林丞宴的模樣終是和那個纏著繃帶的年重合起來。他比大幾歲,不知道他什麼,只是他哥哥。甚至不知道他的模樣,只記住了這一雙眼睛。
明明上一秒殺意還在沸騰。
在阮枝喊了哥哥之后,林丞宴忽然就靜了下來。
他走到阮枝前蹲下,小心翼翼地解開了綁著手腳的繩子,像時在心里的名字一般喊:“枝枝,傷到沒有?”
在這樣近的距離下阮枝能聞到他上淡淡的味道。
在新聞上看到了當年的窯廠炸案,再一想就明白了。是顧衍把林丞宴帶回了家,在博館聞到的那味道也來自林丞宴。
阮枝沒說話,只是搖頭。
林丞宴垂眸看著紅腫的手腕,沒敢,只低聲道:“別怪他,他原是想讓我像常人一樣生活的。是我放不下才從北城回來。”
俊和鄭子的死是他自作主張,顧衍從來都是那麼心。
不論是對他還是對阮枝。
阮枝抿著角,抬眸看向了林丞宴的眼睛,輕聲問:“你們是因為姜家,他是為了什麼?新聞上說的那些理由,我知道都是假的。”
顧衍從來都不在乎名利,他孤傲卻也溫。
可那天他在提起姜家的時候,眼神卻也和林丞宴一樣。
林丞宴沉默片刻,嘆息道:“他們都知道先生父母雙亡,先生的父親為了將那些畫收回來花了大力氣。枝枝,是姜家人先生的父親去借水錢的,也是姜家人找人上門討債,他們想要那些書畫,所以死了先生一家人。這些事,他從來不說。有了你師祖后,先生將心中的恨意和痛苦都藏了起來,他忘卻往事,重新開始。”
Advertisement
阮枝手腳冰冷,流下淚來:“可是師祖也死了。”
林丞宴下上的大將阮枝裹住,低聲應:“是。我們這些人做這些事并非他脅迫,都是自愿的。早在六年前,先生就知道有這麼一天。他之所以出家,就是想放手去做這件事,無牽無掛。”
姜家勢大,他們幾個人與姜家相比實在是小人。
顧衍布了六年的局才將姜家的犯罪事實完全翻開來攤在明面下。從造假案開始到最后的百年展,讓輿論和公眾的緒達到頂峰,只是為了讓姜家無一翻的可能。
他們這些人,都不曾后悔。
話已至此,阮枝什麼都明白了。
不再問。
“能走嗎?”
林丞宴克制著自己想去為抹眼淚的沖,指尖蜷起。
阮枝低頭了眼淚,點頭:“他們還有兩個人,來這里是來找東西的,但找什麼我不知道。應該是為了案子的事。”
林丞宴虛扶著阮枝起,正想說話的時候外面忽然傳來了靜。
林丞宴蹙眉,隨即抬手握住了阮枝的手腕:“抱歉。”
說完他就帶著阮枝從禪房里跑向了走廊盡頭,那間禪房被空蟬改了工作間,窗戶被所有房間的都大。他帶著阮枝從窗戶跳了出去。
山路本就難走,更何況是在夜里。
林丞宴想直接帶著阮枝下山,可兩人剛跑到寺口遠卻傳來了,還有凌而嘈雜的腳步聲。他幾乎在瞬間就分辨出來了這些人不是警察,極有可能是姜家的人。
林丞宴不是沒有自信能突圍出去。
可是他帶著阮枝,他不敢賭。
林丞宴斂了神,語速極快地說了一句:“暫時不能下山。邢驚遲在路上了,很快就趕來,跟我,跑不就說。”
Advertisement
南北兩邊都有人,東邊是死路。
他們只能往西崖跑。
阮枝力有限,更不說在山里凍了那麼久。
不過十分鐘阮枝就跟不上林丞宴了,可后的追逐聲卻在漸漸近。在劇烈的息中,阮枝疑心自己聽到了槍聲。
忽然,側的男人將攬在了前。
阮枝清晰地聽到了他悶哼一聲,了,下意識地喊:“哥哥?”
林丞宴穩住氣息,溫聲應:“沒事,別怕。”
等跑到一陡坡下,林丞宴攥住阮枝將藏了樹叢里,他將后腰的手/槍拿出來塞給了阮枝:“會開槍嗎?我聽秦律說邢驚遲帶你去擊俱樂部玩過,別害怕,枝枝。我..邢驚遲很快就到了。”
阮枝知道自己此時是他的負累,握了槍,含著淚點了點頭。
林丞宴笑了一下,終是沒忍住了的腦袋。
他頓了頓,又道:“枝枝,那個夏天,謝謝你。”
...
邢驚遲循著槍聲鉆了西崖的林。
混的槍聲雜在一切,其中一道槍聲不同,沉悶卻準,彈無虛發。
邢驚遲和林丞宴曾經是隊友。對他來說在這林間找到林丞宴不是難事,他像雪豹一般無聲又迅速地在林間穿梭。
邢驚遲在一的高地找到林丞宴的時候對上的是黑漆漆的槍口,他卻沒停下腳步,直接迎了上去,蹙著眉問:“阮枝呢?”
林丞宴肩頭一松,移開槍口:“藏起來了,我中了槍,帶著不方便。”
邢驚遲眉頭擰得更深:“在哪兒?傷沒有?”
林丞宴剛想說話,子彈就著樹干飛過來了。邢驚遲和林丞宴同時矮躲開,這一瞬間兩人都想起來在北城執行最后一個任務那一晚。
Advertisement
邢驚遲看了林丞宴一眼,因為失,他的臉發白。
林丞宴似乎知道他在想什麼,淡聲道:“當時的事和我沒關系,我知道你查過了。不論你怎麼想,我當警察的時候從來沒做過違反紀律的事。”
他停頓了片刻,聲音放低:“沒傷,凍著了。”
邢驚遲明白這一點。
他也是前些時間才想通了林丞宴忽然離開突擊隊的原因。那時顧衍已經在收網了,林丞宴拋下了已經擁有的一切回到了這里。
在聽到阮枝沒事后邢驚遲腦繃的弦也沒法松下來。
林丞宴微微側頭,又恢復了之前冷漠的模樣:“先解決這里的人,你的人什麼時候到?”
邢驚遲拿出槍,應道:“快了。”
邢驚遲和林丞宴都沒有想到,在這個夜晚他們還能像以前那樣并肩作戰。那時候他們是隊友,此時他們完全站在利益的對立面,卻都為了阮枝妥協。
在今晚,他們的目標是同一個。
林丞宴走了。
阮枝的思緒糟糟的,一會兒想起十九年前的那個夏夜,一會兒想起那個纏滿了繃帶的年,一會兒又想起溪林村的雨夜。
這段時間接連發生的事讓覺得疲憊不堪。
如果不是有邢驚遲在邊可能會找個地方躲起來,好讓這些事都離遠遠的。
這是第幾次躲在山里了?
阮枝覺得自己可能和山不太合,幾次出事都是在山里。
手電筒的亮在細的林間晃,阮枝屏住呼吸,但心跳聲卻越來越快,明明周圍沒有腳步聲,卻覺得比什麼時候都危險。
下一秒,一只手從后面出地捂住了的。
阮枝睜大了眼睛,陌生的味道。
不是林丞宴,也不是邢驚遲。
Advertisement
...
夜深沉,海浪洶涌。
三藐山靠海,西崖下是翻涌的海浪。凜凜的夜風吹過來都帶著咸的味道,冬夜的風像刀,刮過臉頰時讓人生疼。
阮枝黑的長發如海藻一般在風中飛揚,如雪的在月下像是泛著。
的目穿夜和不遠的邢驚遲的目撞上。今晚邢驚遲的模樣是從沒見過的,他想讓自己冷靜下來,可眼底皆是瘋狂。
邢驚遲握著槍盯著和挾持的男人,咬繃著。
崖邊周邊圍滿了警察,姜家的人已全部落網。除了挾持著阮枝的那個男人,邢驚遲和林丞宴解決了眼前的麻煩后立即去找了阮枝,可那里空無一人。
他們循著痕跡一路追到崖邊。
林間視線昏暗,崖邊反而很亮。
月如水一般傾瀉,秦野他們能清楚地看到男人猙獰的面孔,槍口抵著阮枝的頭,握著槍的手在微微抖,似乎隨時都會槍走火。
遠的狙擊手已經待命。
冬夜的風和不明亮的視線以及混的場面都讓這場狙殺變得困難起來,他們隊伍里最優秀的狙擊手是余峯,但他暫時趕不過來。
秦野張看了一眼邢驚遲,他眸底泛紅,漸漸失了耐心。
這不是邢驚遲的正常狀態,遇上阮枝的事他總會變得不像自己。
秦野將槍口對準那個男人,有力的喊聲在崖邊回:“放下武!你已經被包圍了,其余的人已被抓獲,放下武出人質,我們不會開槍!”
他們這樣的人和警察打道慣了,哪會害怕這樣的話。
男人勒著阮枝的脖子,槍口又抵了一點。阮枝呼吸微滯,盡量忍著,忍著痛苦、忍著眼淚,不讓邢驚遲看到難的表。
可對邢驚遲說是雪上加霜。
他快要瘋了。
“邢驚遲,刑警隊長啊?”
“你想過有這一天沒有?”
男人笑得張狂,他知道自己走投無路,幸而手里還有這麼一個好用的人質。他們要抓的人正好是邢驚遲的人,這像是命中注定一樣。
他們恨邢驚遲,恨他不留面,恨他手段狠厲。
邢驚遲結滾,黑眸盯著蹙著眉的阮枝,繃著,從嗓子里吐出的字眼像是被碾過:“你想要什麼?”
他要什麼?
當然要看邢驚遲痛不生。
男人啞著嗓子笑:“要我放開,容易。你平時不是很能跑嗎?不抓著人就不停是吧,你兄弟給你上來上一槍,我看看你以后還能不能跑。”
話音落下,崖邊一片死寂,只所有人都握了槍。
他又笑:“不敢?”
說著收了勒著阮枝的手。
阮枝怔住,蒼白的臉上滿是淚痕,下意識地搖頭:“邢驚遲,你不能聽他的。邢驚遲,你...”
“枝枝,別。”邢驚遲像是在懇求,眼睛已經紅了。他握著槍的手沒,只冷聲道:“秦野,開槍,快點。”
秦野咬牙:“隊長!”
阮枝里的哭腔本掩飾不住:“邢驚遲!”
邢驚遲面無表,他盯著阮枝,一字一句道:“秦野,這是命令。”
阮枝的淚像流不盡的水。
水讓的視線變得模糊,心上像是被重重地撞了一下。從未像此刻一般清晰地意識到,這男人為了,命都可以不要。
秦野覺得自己要炸了,恨不得沖上去用自己把阮枝換回來。他們的槍從來是對準敵人的,從來不會對準自己的兄弟、同事。
這違背他作為警察的職業道德。
但命令他開槍的是他的隊長。
但即便是這樣,秦野握著槍的手也沒有抖,那男人已經準備扣上扳機了。他閉了閉眼,再睜眼時眼底再沒有毫猶豫,槍口下移,對準邢驚遲的小開了一槍。
“砰”的一聲槍響。
“隊長!”“隊長!”
數道聲音重疊在一起。
阮枝嗚咽出聲,男人開始大笑。
邢驚遲的形在寒風中沒有搖晃一下,即便他的小被打得皮開綻,他卻像山一樣沒有被撼分毫,連臉都沒有變。
一時間這頂上除了阮枝的小聲嗚咽和男人的笑聲之外竟再沒有其他聲音。
海浪拍打在礁石上的聲音打斷了男人的笑聲,他看了一眼面不改的邢驚遲,毫沒有他想的狼狽的模樣,恨道:“另一條!”
秦野額間青筋暴起,他極快地瞥了一眼男人的后。
那男人的后是斷崖,本應該什麼都沒有。可現在卻有一個影在靠近,他的作小心而蔽,即便了傷也不妨礙他從另一邊攀到崖下再繞過來。
男人吼:“快點!”
這樣冷的冬夜,秦野的額間沁出了汗意。
他抿著,槍口微微下移。
邢驚遲似是覺不到疼痛一樣,只盯著阮枝,一直在流淚,耳朵已被凍得通紅。雖然上裹著林丞宴的大,但這樣的溫度對來說太難熬了,何況先前已經凍了那麼久。
他不著痕跡地往男人后看了一眼,忽然抬手比了一個手勢。
這時候一道影猛地從男人后撲來,男人握著槍的手被扣住,槍落在地上被林丞宴踢開,他狠狠地把男人從阮枝邊扯開,兩個人滾做一團。
邢驚遲毫不猶豫地上前將阮枝扯進了自己懷里。
秦野等人立即沖上去想把林丞宴和男人拉開,那男人卻瘋了似的抱住林丞宴往斷崖邊滾。林丞宴本就中了槍,一時間竟沒掙開,眼看著就要墜斷崖。
“林丞宴!”
邢驚遲放開阮枝撲上去手一把抓住了林丞宴的手,兩個男人的重量讓邢驚遲悶哼了一聲。
冷風席卷而過。
懸在崖邊的林丞宴抬眸看著皺著眉的邢驚遲,忽然笑了:“隊長,在北城那段時間我過得不錯,多謝你。還有,照顧好。”
說完林丞宴就用力地掰開了邢驚遲的手。
秦野出的手懸在空中,他們撲在崖邊眼睜睜地看著林丞宴和那男人一同墜下了崖。下面是海,這樣冷的天掉下去生還的概率微乎其微。
阮枝跌坐在地上,神倉惶地看著斷崖。
邢驚遲攥了拳,起道:“把搜救隊喊來。”
他頓了頓,又說:“活要見人,死要見尸。””
說完他大步地走向阮枝將從地上抱起來地摟在懷里,懷里的人睫了,終是支撐不住在他懷里暈了過去。
作者有話說:兔崽安靜如。
猜你喜歡
-
完結431 章

萌寶歸來:爹地放開我媽咪
他冷血無情,隻懂強取豪奪!她被逼無奈,放下傲骨,與他糾葛,踏入豪門。五年後,她攜萌寶歸來,勢要雪恥前仇。萌寶狡詐呆萌,像極了他。“叔叔,你想做我爸比?可你好像不合格。”某男人俯視身邊的女人,“合不合格,隻有你媽咪說了算。”這個男人不但霸道,還寵妻入魔。
78.4萬字8 25363 -
完結955 章

先婚后愛:權少的迷糊小老婆
蘇煙怎麽也想不到交往了四年的男朋友會爲了前途而選擇另壹個世家女,既然這樣,那她選擇放手。 可是對方卻不依不饒,幾次出現在她面前秀恩愛!她忍讓,對方卻越發囂張。 蘇煙:“我已經有男朋友了。”誰知她在馬路上隨便找的男人竟然這麽優質,而且還全力配合她。 她感動的想以身相許,結果人家說,他需要壹個能洗衣做到拖地的人。 蘇煙傻兮兮的被帶回家,發現自己的老公是壹個經常出任務的軍人,而且她什麽都不用做,只要被寵愛就行了! 婆婆:“寶貝兒媳婦,這是婆婆炖了幾小時的湯,快喝。”公公:“妳那些客戶要敢欺負妳,妳就告訴我,我讓他們消失!”老公:“我老婆是我的,妳們誰也別想霸占!”………………婚前:蘇煙:“妳爲什麽幫我。”沈右:“我是軍人,爲人民服務是應該的。”婚後:蘇煙:“妳最喜歡吃什麽。”沈右:“吃妳。”【歡迎跳坑~】
242.7萬字8 42778 -
完結985 章
南方有喬木喬妤
父親年邁,哥哥姐姐相繼出事,24歲的喬家幺女喬妤臨危受命接管風雨飄搖的喬氏。為了保住喬氏,喬妤只好使盡渾身解數攀上南城只手遮天的大人物陸南城。 初見,她美目顧盼流兮, “陸總,您想睡我嗎?” 后來,她拿著手中的懷孕化驗單,囂張問著他, “陸總,娶不娶?” 男人英俊的面容逼近她,黑眸諱莫如深, “這麼迫切地想嫁給我,你確定我要的你能給的起?” 她笑靨如花,“我有什麼給不起?”
229.9萬字8 6953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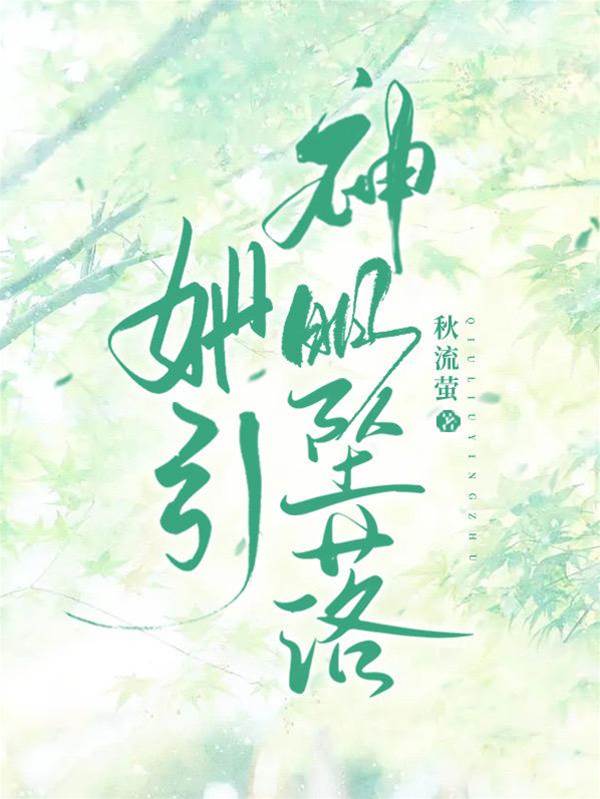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50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