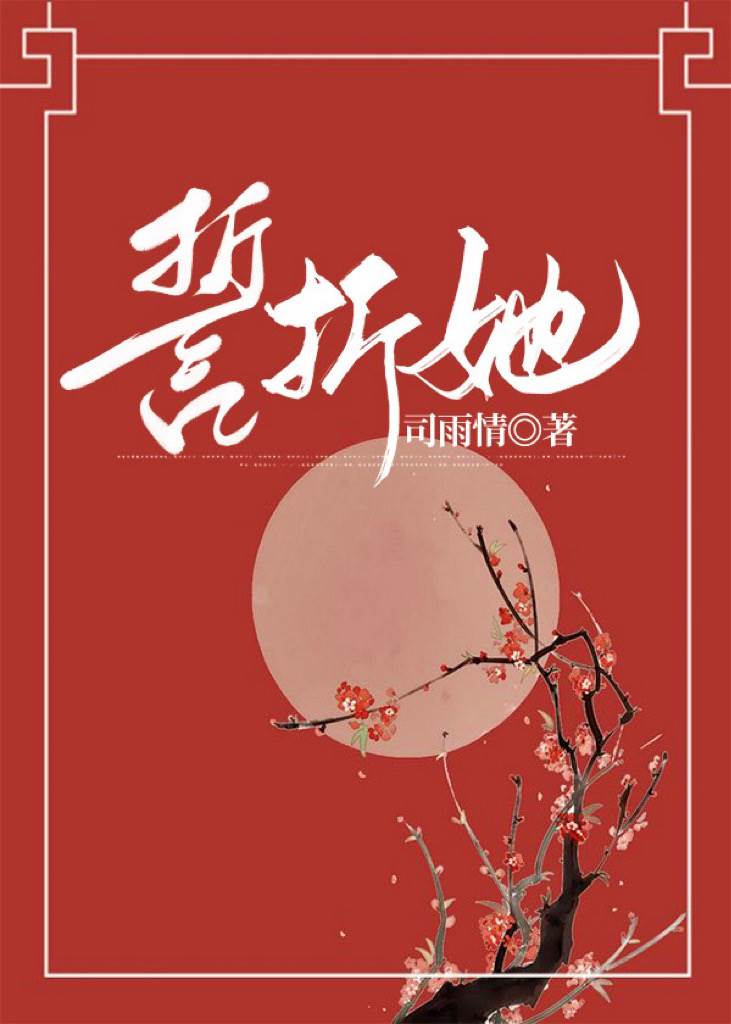《我力能扛鼎》 第300章 第300章
“火銃準頭極差,雖填滿藥能八十步遠,但它不像弓箭,指哪打哪。這一枚彈球里鐵殼裹著碎鐵屑,分量不勻,是以飛不直線,距離遠了,能不能傷敵全憑運氣。”
“北地的軍營里沒有專門的火銃兵,幾十年前,騎兵還會人人配一把,用火銃擾敵騎陣型。可馬上瞄準更不容易,敵騎瞬息即至眼前,而火銃填藥、填彈,打一發需數二十數……二十、秒?”
晏昰頓了頓。
他在唐荼荼驚喜的眼神里,知道自己沒講錯,接著道:“填彈太慢,不堪大用。后來工部造出了連發弩,大炮也一年比一年威風,火銃就被扔出了陸戰。”
“直至六年前,趾郡王(越南王)叛,又霸了瓊州島。咱們的海將久攻不下,那地方,大炮常常啞火,弓箭也因風向阻,只得起用火銃——這東西瞄人不行,唯有一條好,只要咱們的船夠高,以上攻下,專攻敵船與水兵防薄弱之,百發可中八十,不風與水汽所阻——各地軍械作坊就又揀了起來,重制了五花八門的火銃,鉆研海戰。”
……
簡而言之,準頭不好、陣仗大,是個方便攜帶、但作流程繁瑣的中程武,遇敵需要有足夠的準備時間才行。
二殿下講學,像國子監夫子給三歲小兒講課,把這東西的發展簡史、優缺點,乃至銃管上每一個部件的用,全掰開了碎了講。
他剛訓完人,板著張臉,聲卻清亮,戴著張面也是相貌堂堂的。
周圍有不會使火銃的姑娘好奇地圍過來,漂漂亮亮站定,才糯糯地喊了聲:“公子也教教我……”
晏昰厲眼一瞪:“火銃對人,營三十。收回去!”
Advertisement
唐荼荼:“……”
姑娘巍巍地跑了。
唐荼荼鬼使神差地暗爽了一下,憋住笑:“像我這樣把槍頭朝地才對吧?”
晏昰:“不填藥時怎麼拿都不為錯,填了藥,就是沒敵人也得空響一聲打出去。硝石硫磺積在膛管里,遇曝曬則燃,是要人命的。”
唐荼荼聽得仔細,一字沒。
“握。”
他握在小臂上給矯正姿勢,掌骨很,像鐵板一樣的,隔著裳都有蓬的熱度過來。
站得也近,唐荼荼耳畔那一小片,隨著他說話間的吐息微微泛起,忍不住偏著頭躲了躲。
一截扇柄敲到肩膀上:“專心。”
唐荼荼就差屏蔽覺了。
對武沒有天分,不是一教就會、一就的天才,唯一的優點是不畏懼。剛才那一著火,嚇走一半新手,全躲得遠遠的了,唐荼荼兩手的炭黑印還沒洗呢,眼下也敢把銃管架回自己右邊肩膀上,用的頸窩輕輕一夾,這就算是“瞄準”了。
反反復復架起、瞄準、落下,練這一套姿勢就花了半個時辰。城里來的小姐們在軍屯子弟的教學下都拿火銃炸著魚了,唐荼荼還在那邊練習弓步位,學著怎麼裝卸支架。
不覺煩瑣無聊,只是周圍“嗵嗵嗵”的,靜震耳朵,唐荼荼難免分了分心,回頭想看他一眼,這一回頭,卻正正好地與他對上視線。
唐荼荼又趕把目挪回來,臉上有點臊。
“二哥,那邊有姑娘在看你哈。”
晏昰:“嗯。”
唐荼荼:“好家伙,那邊也有倆姑娘在看你——那黃姑娘是剛才過來的那個吧?”
晏昰:“怎麼?”
唐荼荼:“二哥過完今年生日就滿十八了噢?”
Advertisement
晏昰:“有話直說。”
唐荼荼瞇起一只眼,瞄著海面慢吞吞講:“這是相顧船,是沒定親的姑娘小伙兒相看的地方……我聽和說,一般這種‘相看’都是姑娘看小伙兒的。因為,十六七的姑娘是竇初開的年紀了,十七八的爺們還都是二愣子呢,自然是孩兒看人更準些。”
“船上見見面,玩耍玩耍,要是哪家孩兒看見哪個小郎君順眼,等下了船,會悄悄地去跟爹娘講,回頭兩家人探探口風,要是都有那意思,就奔著做親家去了。每年過完娘娘會,都能好幾對呢。”
一副好妹妹關心哥哥婚姻大事的模樣。
晏昰“呵”了一聲,語調涼涼:“有意思,繼續說。”
唐荼荼壯了壯狗膽,把火銃的藥室倒干凈,扭回頭,裝作一臉誠懇地看著他。
“二哥翩翩佳公子,自然是無一不好的,孩子慕你也是正常——但二哥你想啊,一來,你戴著張假臉,誰也沒看見真實的你,這份慕輕飄飄的不經事兒啊。”
“再說,你一外地人,又不會在天津久待,萬一哪個姑娘看上你了,還得跟你一塊回京城,忍與爹娘離別之苦……這不好。”
晏昰眼里帶出笑來:“難為你,思慮得周全。那依你之見,我該如何?”
唐荼荼把剛想好的說辭拎出來:“今晚他們還要聽戲,還要開席設宴,一群陌生人鬧哄哄的,多煩。不如咱倆關起門來吃海鮮,配兩壺小酒,豈不哉?”
晏昰被逗樂了,一點頭:“甚善。”
唐荼荼安分了,從牛角罐里捻了撮火藥填進藥室里重新練。
公孫景逸鬼鬼祟祟過來,前腳被哥罵一頓,這會兒見了人,規規矩矩一拱手,話都不敢大聲講。
Advertisement
“茶花兒,我也一塊教你吧,我火銃使得可好了,指東不打西,指高不打低,保管讓你一天出師,兩天炸魚,三天把海盜船都轟回姥姥家去。”
晏昰:“呵。”
他那標志的冷笑又出現了,唐荼荼回頭瞄了瞄,果然沉著臉,掀著,整張臉都寫了“大言不慚”四字。
公孫景逸自然聽出來了,忙拍著口:“哥,這話不是我吹,我火銃用得真的可好,五歲時候我太爺爺就把我抱上教我炸魚缸了,練這麼些年,閉著眼睛都能打鳥!”
晏昰有心瞧瞧“閉著眼睛能打鳥”是多大的能耐,把火銃遞過去,拉著唐荼荼退開兩步:“你來幾發,看看。”
公孫景逸:“好嘞哥!”
這桿銃槍是填好了藥的,公孫景逸利落地以肩架起銃筒,他認真起來的那一瞬間,往常吊兒郎當的樣子全不見了。
到底是練家子,手上穩,腳下更穩,讓唐荼荼趔趄了三步的后坐力只夠讓公孫景逸手掌晃一晃,連他小臂都撼不得。
這小子,填藥填彈和速快得出奇——別人填火藥用小匙,一滿匙是多克,兩滿匙能打多遠,填夠分量再用木馬子搗實。
公孫景逸不一樣,他分寸全在手上,指尖多,裝進去指肚一摁就正好,卷香一,點火就發,一點不含糊。
最后他甚至換了一三眼銃,三管并聯,每銃管里塞進三顆鐵子,這東西后坐力太大了,放在頸窩有崩裂管的風險,要夾在腋窩下。九顆鐵子砰得出去,鐵屑迸濺,海面剎那間騰起個小浪頭,暴雨般噼里啪啦砸回海面上,無數明晃晃的銀肚魚噗鈴噗鈴打著滾。
“好啊!公孫哥哥太厲害啦!”
Advertisement
“公孫你跑校場練了吧?這技比去年又有進啊。”
“我家老祖宗手把手教出來的,那還能差得了?”
“那自然是天下第一、舉世無雙呀!”
周圍爺小姐們振臂喝著彩。
公孫景逸不知謙虛為何,舉著銃管朝夕又放了一炮,痛痛快快大笑起來。
這比盛朝建朝還要久的三百年老將門,淺淺了一條的鋒芒,就能鎮住一大波人。他家的旁系不知道什麼樣,單說嫡支這脈,唐荼荼見過的公孫老爺、他家大爺,還有這位嫡重孫倒倒是都有真本事。
“表哥快歇一歇。”
公孫家的堂表姐妹們、城里來的家們,各個眼睛亮晶晶,這邊倒茶的、送梅子湯的,那邊送汗巾子的、吩咐下仆給他肩膀松松筋骨的,一團殷勤。
這公子哥抹了一把汗,誰也顧不上,先躥到這頭來討夸,喜滋滋問:“哥,我打得還不賴吧?教茶花兒綽綽有余吧?”
一聲“哥”得比“茶花兒”還親。
晏昰掃他一眼:“前三發過得去;第四發填藥了,水前便鐵屑迸濺,只見水花,不見死魚浮起;后頭五發彈沒法看,你手上失了準頭,歪一發,跑一發,只剩個花架子好看。”
“……我那是震得手腕疼!”
公孫景逸剛出個驚愕的表,只聽唐二哥又說。
“至于三眼銃麼,五十步之可擊穿半寸厚的船殼,是水兵先鋒駕艨艟、快速突擊敵船時用的——而海滄船是主帥船,周圍全是麻麻的隨行船,配這三眼銃,除了傷自己人毫無用,不是主帥船上該有的東西——你特特帶上船來顯擺,就為在姑娘們面前長臉?”
公孫景逸:“……”
這是什麼神仙人!!!
他這噼里啪啦一陣轟,別人能數清幾聲響就不容易了,海里的鐵子誰能看著?要麼是憑超絕的眼力,要麼是聽靜聽出來的!
公孫景逸差點給他跪下。一時間覺得自己沒出息,招花惹草,嘩眾取寵,真是沒出息大發了。
晏昰背著手,明明兩人高相當,偏偏他看人能呈俯視的角度。
公孫景逸瞪著一雙燈眼,聽他言語。
“軍中手填藥、填彈、定準、點火,打出這麼一發需三息,你比他們快了半息,這很好。但圖快、打不準有甚麼用?殺不了敵,還不如一聲炮響——你父輩蔭庇,領了幾百個兵,也算是個小將軍了,為將者不知進,只會賣弄風頭,遲早像你這幾發彈一樣,開頭鮮,后勁不足。”
他說完,突地叱了聲:“再來!填藥!”
“還來?!”
公孫景逸后頸發麻。
他大可以把火銃往甲板上一扔,嚷嚷一聲老子不這窩囊氣了——卻鬼使神差地握住了火銃,架上肩頭,用震得發麻的手臂繼續瞄準。
遲遲不見下一個口令。
公孫景逸在這個半弓步姿勢下定了片刻。晏昰招手吩咐:“取只湯盅來。”
很快有人取了來。燉湯用的盅是一個大肚、兩只耳朵,瓷厚,手大的一只得有兩斤重。晏昰滿滿當當倒了一盅酒,兩耳窟窿里栓繩,吊在了公孫景逸的銃管下。
“……!”公孫景逸眼珠子差點瞪出來。
這是訓什麼妖魔鬼怪的辦法!
他眼也不敢眨一下,一發鐵彈嗵得出去,那盅酒吊得晃晃,嘩啦灑了一地。
晏昰往旁邊瞪了一眼,瞪住一個笑得開花的唐荼荼:“你傻樂什麼?跟著練。”
唐荼荼:“……噢。”
“填藥!”
“填彈!”
“定準!”
“點火!”
就這樣“填藥填彈定準點火”,一遍遍地練他倆,練得周圍一群姑娘爺都驚掉了下,納悶這不是相看船嗎,怎麼突然就變演武場了。
晏昰一個眼神掃過去,一群公子小姐怕被抓壯丁,全灰溜溜跑邊上躲著了,遠觀這冷面煞神練人。
瓷盅連酒將近三斤,開始時一發彈出去能灑一半,可再倒滿以后,只灑出來三分之一。一次一次倒滿,灑得越來越。
夕愈盛,照得兩人頭臉紅撲撲的,公孫景逸從小扎到大的弓步都快扎不住了,汗淌了一脖子,一遍一遍刷新自己“力竭”的極限。
整片海不知多條魚遭了殃,這公子哥茫然地著海里的魚,他堂堂校尉在,恍惚間竟覺得自己像剛進軍營第一天的小兵蛋子。
直到將勉為其難點點頭,落了聲:“像個樣子了。”
公孫景逸心神一垮,解下湯盅就癱那兒了。
這位唐二哥拍拍他肩膀,意味深長來了句:“加油,好好練。別墮了你家先人威風。”
也不知是唐二哥手勁大,還是他累得了力,這輕輕兩下拍下來,公孫景逸下盤得差點沒站住,茫茫然心想:‘加油’是個什麼?
晏昰拂拂袖上的灰塵,徐緩抬步走了,留下后半條船震驚的目,一齊籠統圍住了公孫。
“不是說茶花兒哥是個掉書袋嗎!不是在國子監啃書?這兵則例背得比咱?”
“銃管上吊瓷盅?!這什麼虎狼招數?”
“怪不得都說國子監人才濟濟,這、這也太神了。”
“……神什麼神,國子監你還不知道,紙上談兵誰也沒那群人會說,真能打仗的有幾個?你看他這麼能,方才落公孫面子時怎麼不自己打兩炮?讓人瞧瞧他什麼能耐啊。”
“倒也是,喊住他讓他亮亮自個兒什麼能耐啊?”
“嗐,就一叭叭能說的書生。”
“這他娘是書生?這能是書生?!你們沒瞧見那板,那腱子,還有罵人那中氣足的,這要是書生,我腦袋摘下來給你當球踢!”
“公孫,你怎麼看?”
公孫景逸著船舷西頭的那道影,喃喃。
“你們懂個棒槌。義山兄弟高義,實讓人心折……你們說,我倆要是義結兄弟,將來我再相看他妹妹,是不是不太講究?”
猜你喜歡
-
完結300 章
王妃脾氣爆:皇叔,請節製
一朝穿越成傻妞,廚房茅房傻傻分不清。幸有爹孃疼愛,四位兄長百般嗬護成長。笑她目不識丁癡傻愚頑?一朝驚天地,袖手弄風雲。從此商界多了個不世出的奇才!說她軟弱可欺任意拿捏?上有護短狂老爹撐腰,下有妹控兄長為她收拾善後。權傾朝野號稱天下第一美色的輔助親王,更是化身寵妻狂魔,讓她橫著走!某天在金子堆裡數錢數的正歡慕容明珠,被一雙大手覆上「王妃,今晚我們……」「一邊去,別妨礙我數錢」「……」
52萬字8.18 10629 -
完結11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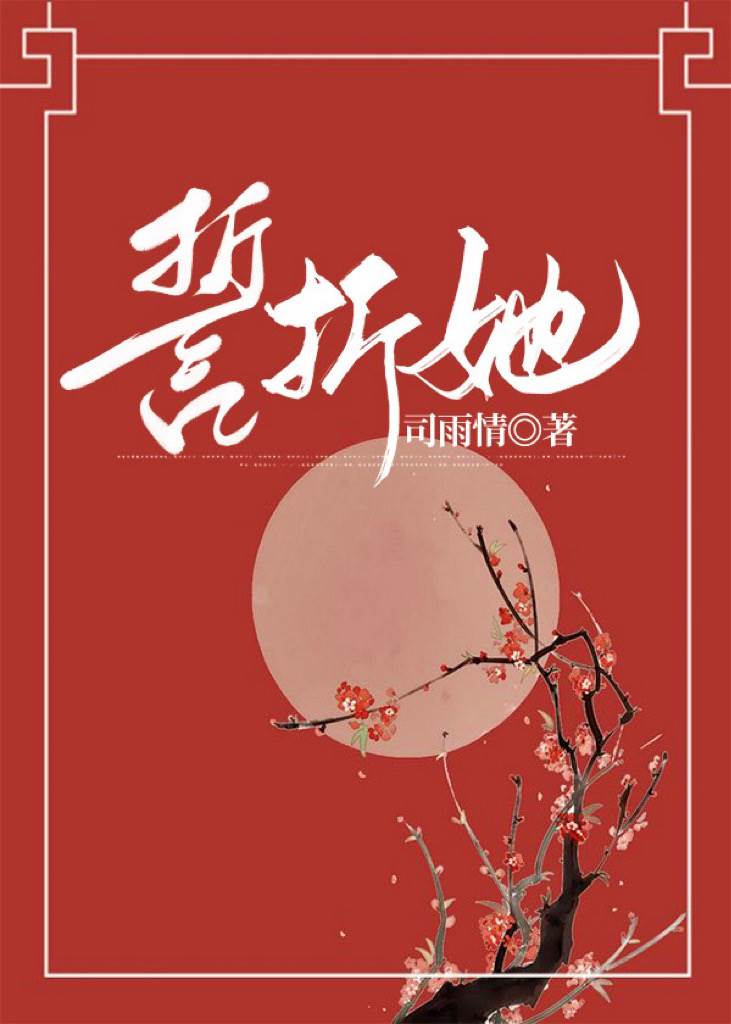
妄折她
昭華郡主商寧秀是名滿汴京城的第一美人,那年深秋郡主南下探望年邁祖母,恰逢叛軍起戰亂,隨行數百人盡數被屠。 那叛軍頭子何曾見過此等金枝玉葉的美人,獸性大發將她拖進小樹林欲施暴行,一支羽箭射穿了叛軍腦袋,喜極而泣的商寧秀以為看見了自己的救命英雄,是一位滿身血污的異族武士。 他騎在馬上,高大如一座不可翻越的山,商寧秀在他驚豔而帶著侵略性的目光中不敢動彈。 後來商寧秀才知道,這哪是什麼救命英雄,這是更加可怕的豺狼虎豹。 “我救了你的命,你這輩子都歸我。" ...
40.2萬字8.18 6646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