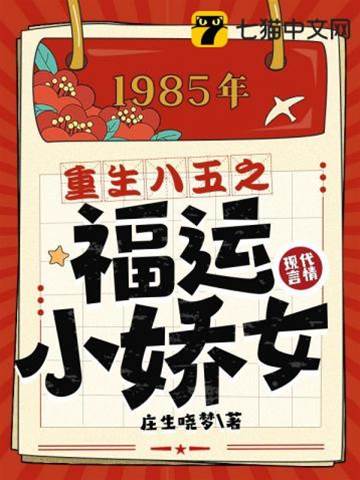《你最好別哭》 第33章 裙下之臣(二)
崇京在北,港廈在南。
從港廈飛崇京大約小時左右,為了不過分引人注目,岑浪沒安排家里的私人飛機,選擇跟時眉一起坐民航。
畢竟作為港廈太子爺的未婚妻,既然都省辦泳派對找男模了,總不能還明目張膽地讓岑家包機給。
兩人買了晚間航班。
起飛平穩后,岑浪從包里拎出扣頭式耳機戴好,縱機艙配有的手柄遙控屏幕開始打起游戲。
大抵是頭等艙太舒服了,時眉起初在聚會神看著電影,過了沒一會兒,岑浪無意間抬頭斜一眼,發現人在搖搖晃晃地犯瞌睡。
盤坐在沙發椅上,前傾,腦袋一點一點地不停點頭,整個人像只不倒翁一樣昏沉沉地閉著眼。
這時,飛機一個氣流顛簸。
時眉隨慣猛力朝前栽去,眼看著腦袋就要磕上對面的屏幕,岑浪丟下手柄迅速手托住的尖巧下顎。
手膩微涼。微弱淺淺的呼吸噴落在他的熾燙掌心,帶著熱氣,似小貓細短茸茸的尾尖輕輕蹭劃,幅度很小,頻率均勻,惹的。
岑浪虛斂著睫,指骨略微施力起的臉頰拉近眼前,眼底冷冷招搖著捕獵與侵略的頹靡,不聲,狼一樣的視線徘徊在臉上。
時眉在他掌心上睡著了。
雙眸閉闔,長睫低垂,薄白眼皮上敷纏著青藍細管,錯盤絞,總凝練出幾分凌的漂亮。
目拉下,游移過飽滿氣的鼻線,當指腹不自覺上的,的熱溫,被他指尖按,本不住反復逗弄,瓣邊緣很快變得殷紅勾人。
岑浪凝視著這張臉,有些想不通。
Advertisement
為什麼的這麼,
說的話卻那麼刺人;
為什麼的那樣韌溫暖,
心卻這般又冷又。
當以極其無所謂,甚至有些嘲意的口吻說出“奪走他的初吻”時,其實岑浪是沒有生氣的。
畢竟,那是事實。
當用一副荒唐可笑的表告誡他,“幾個吻而已,大家都是年人”,讓他清醒點的時候,岑浪也沒有生氣。
畢竟,那也是事實。
的確是他夠荒唐。
天真覺得自己在沒經過的允許,在喝醉的況下,騙走了的吻這種行為是不紳士的,不妥當的,無論如何他應該要主承認這份“罪行”。
他可以負責。
可就在他甚至還沒來得及思考怎麼去負責的時候,得到的時眉的態度是冷嘲熱諷,是劃清界限,是將他所謂“負責任”的行為視作一種無聊的麻煩。
說:
“如果我向你道歉的話,會讓你覺得比較舒服一點嗎?”
當然不會。
他怎麼會覺得舒服,
他只會到挫敗。
于是接連幾天岑浪都在避開。他想知道,到底他這段時間古怪又詭異的異常行為,是不是真如所說的那樣,僅僅只是孤男寡在一起住久了而已。
但當他發現自己看到會心煩,看不到更煩的時候,
岑浪就知道不是了。
那是什麼呢?
他對時眉產生的,
到底是什麼。
岑浪移開拇指,放過膩的瓣,收輕力度,將放躺在沙發椅上,調低椅背,拎過小毯替蓋上。
卻在撐起之前,
眼神無意識地凝定的,
然后在岑浪反應過來時,發現自己已經不知道什麼時候逐漸彎下腰,一點點移湊近的前。
Advertisement
而時眉驀然這一刻,睜開眸子。
被岑浪驚了一跳,本能扶住他的肩頭,后仰脖子,薄睫劇烈眨,磕絆著問:“怎、怎麼了…?”
“刺眼。”
岑浪嗓音冷淡,眸未變地抬起手,“嘩”一聲用力扣下頭側的遮板。
隨即淡淡瞟了眼的,平靜從容地直起子,拿起手柄開始新一的游戲戰斗,除了不記得戴回耳機的耳骨在眼可見地速度泛紅以外,別無異樣。
“遮板不是可以自調節嗎?”
時眉向他呢喃一句。
岑浪清清嗓子,眼神停留在游戲屏幕上,頭也不回地冷漠接了句:
“忘了。”
“但是……”時眉翻了個朝他的方向側躺著,手撐著腦袋,另一手抬指輕緩過他的耳,慢慢出笑容,
“岑浪,你耳朵怎麼又紅了。”
人指尖冰冷,蹭過耳廓似被水淌過,膩,沃,又像勾著燎原的一簇火,缺限度的明目張膽。
總是這樣。
時刻提醒他劣勢,
給他帶來麻煩,
又讓他貪婪。
岑浪皺眉捉住的手指,冷冷丟開,側偏過頭低睫盯視著,問:
“你想說什麼?”
時眉饒有興致地挑了下眉梢,梨渦淺現,饒有興致地看著他:
“我想知道,那天晚上…真的是你初吻嗎?”
岑浪平淡地看了好一會兒,倏爾角微勾,回答干脆:“是。”
他強調散漫,慵懶淡漠地將問題反拋給:“所以,你打算怎麼賠給我?”
時眉反倒被他問愣了下,下意識口而出:“是我先的嗎?你可別趁我喝醉了想誆我。”
“誆你?”岑浪低嗤一笑,“我派人調監控出來,幫你好好回憶一下?”
Advertisement
時眉:“……”
那倒也大可不必,
有誰會想要看酒后社死的視頻…
“回答問題。”
見愣神不說話,岑浪屈指輕扣眼前的桌面,深意提醒道。
時眉還有點兒沒反應過來,“什麼、什麼問題?”
岑浪半瞇著眼,“裝?”
時眉認真反應了下,才驚覺到他剛才的問題問得有多曖昧不清,后頸騰升些許燥熱,道:
“那你想我怎麼賠?”
“賠錢的話…”
“別想。”時眉迅速果決打斷他的話,甚至激得坐了起來,表堅定不移,“想都別想。”
開什麼玩笑,秦嬋這案子本就是為了見到夏婕住進他家,而不得不答應的免費義務勞。
昨晚為了速戰速決,好不容易想到一個好的提案,只不過是要委屈他假裝當下狗。
假裝而已啊!
結果他居然要加錢。
不加錢就不配合。
合著一分錢不拿還倒,倒就算了,他現在居然還敢跟談錢?
岑浪輕輕挑眉,毫不意外,仿佛等的就是這句話。
“賠錢,或者還吻抵債。”
他懶地給出建議,告訴說,“我允許你選擇其一。”
“還吻抵債?”
時眉驚然重復這四個字。
過了好半天,
“抵多?”竟然這樣問。
岑浪挑,“清平。”
時眉躺回去,裹起小毯遮住大半張臉,只出一雙眼睛鶻伶伶地眨睫著他,就像是…
就像是真的有在思考他的提議。
“慢慢想。”岑浪轉過頭,角弧度暗暗加深,撥調回屏幕游戲,漫不經心地留給一句,
“今晚,我們有的是時間。”
……
崇京的氣溫比港廈低,一下飛機,岑浪便從手提的小行李箱中拎出一件厚外套給時眉穿上。
Advertisement
之后時眉跟著他去拿行李,去地下停車場,總之一路兜兜轉轉時眉都不用心不用帶腦子。
跟著他走就對了。
時眉跟在后面索玩起手機,一直走到地下,才發現肴跟另一名男助理早已等候多時。
兩人后分別停著兩輛超跑。
一輛油白布加迪,一輛牛油果法拉利。
“你開哪輛?”
岑浪從肴手中接過車鑰匙,轉問時眉。
時眉回了條喻卓的微信,看了眼車,又看了一眼他,驚訝問道:“什麼意思,你不跟我一起嗎?”
“分開走,酒店集合。”說著,岑浪掀眸一眼,哧笑了下,近耳側低聲說,“不是想包我麼?”
時眉眨眨眼,瞬間懂了他的意思。按照給出的方案,兩人要先裝不認識,在今晚的泳趴上互相對上眼才勾搭一起去。因此當然不能一起從機場進酒店。
“戲快啊。”時眉忍不住調侃。
岑浪懶得理,輕揚下頜,扔了個字:“選。”
時眉抿抿,看上去有點猶疑。
岑浪一秒讀懂的躊躇,淡勾了下,直接握著的手按下語音鍵,將這條語音證據發給喻卓:
“車全保,事故不用你賠。”
時眉瞬間亮了眸子,彎起,指著那輛牛油果的法拉利說:“這個……多適合你啊。”
岑浪:“?”
時眉笑瞇著眼,挪移手指,又指向一旁的油白布加迪說:“我要這輛。”
岑浪抬手將車鑰匙扔給,“位置發你了,出發。”
/
說是不用負責,
可時眉畢竟開車經驗并不足,加上這車比人還金貴,腳下油門不敢往深了踩。
岑浪原本跟特意隔了一條街,奈何時眉車速只減不增,越開越慢,這樣開下去恐怕天亮都到不了酒店。
岑浪實在忍不了,干脆變道加速直接追上來,降下敞篷,抬起手在前車里朝打了個手勢,示意跟上。
時眉滴按兩下喇叭回應,之后一路跟著他飛馳在崇京的繁華車流中。
半小時后,兩輛超跑一前一后開一座皇宮花園式酒店后院。
時眉看到岑浪停了車,也跟著停下來,兩人將車鑰匙遞給泊車員后,時眉忽然被岑浪拉著跑向一旁的叢林口。
“記住這里,一直走到頭就是今晚的森林泳池趴。”岑浪指給看,叮囑說,“待會兒換完服吃完飯,十一點左右下來,我在這邊等你。”
“好。”時眉點頭應下,然而一抬頭,莫名覺得岑浪的眼神似乎不太對勁,“還有事兒?”
“正事說完了,是不是該聊聊私事了?”岑浪瞇起眼,緩緩朝邁近。
時眉被接連退,直到后背抵在堅糙的樹前,試探著問他:
“什麼…私事?”
岑浪欺困住,微微歪頭,指腹施力磨蹭過脆弱薄的紅,說:
“親我,現在。”
猜你喜歡
-
完結437 章

禁愛冷婚:噬心總裁請走開
十歲那年,她被帶回顧家,從此成了他的專屬標籤.性子頑劣的他習慣了每天欺負她,想盡各種辦法試圖把她趕出這個家.在她眼中,他是惡魔,長大後想盡辦法逃離…孰不知,傲嬌的他的背後是他滿滿的深情!在他眼中,她是自己的,只能被他欺負…
79.8萬字8 51621 -
連載1508 章
媽咪爹地要抱抱
豪門陸家走失18年的女兒找回來了,眾人都以為流落在外的陸細辛會住在平民窟,冇有良好的教養,是一個土包子。結果驚呆眾人眼球,陸細辛不僅手握國際品牌妍媚大量股份,居然還是沈家那個千億萌寶的親生母親!
127.1萬字8 107896 -
完結518 章

六歲妹妹包郵包甜
【團寵、高甜、前世今生】農村小野丫頭樂萱,靠吃百家飯續命,家家戶戶嫌棄她。 某天城里來了個謫仙似的小哥哥沈易,把她領了回家。 噩夢中驚醒,覺醒了萱寶某項技能,六歲女娃琴棋書畫樣樣精通,徹底虜獲了沈家長輩們和哥哥們的心,她被寵成了金貴的小寶貝。 每天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叔叔嬸嬸、還有哥哥們爭著搶著寵,鄉下野生親戚也突然多了起來,自此萱寶每天都很忙,忙著長大,忙著可愛,忙著被寵、忙著虐渣…… 標簽:現代言情 團寵 甜寵 豪門總裁
109.9萬字8 94533 -
完結872 章

婚華正茂
蘇念恩被查出不孕,婆婆立馬張羅,四處宣揚她有病。丈夫出軌,婆婆惡毒,當蘇念恩看清一切,凈身出戶時,丈夫和婆婆雙雙跪求她留下。她瀟灑走人:“我有病,別惹我。”愛轉角某個牛逼轟轟的大佬張開雙臂說:“你有病,我有藥,天生一對。”
138.1萬字8 70063 -
完結3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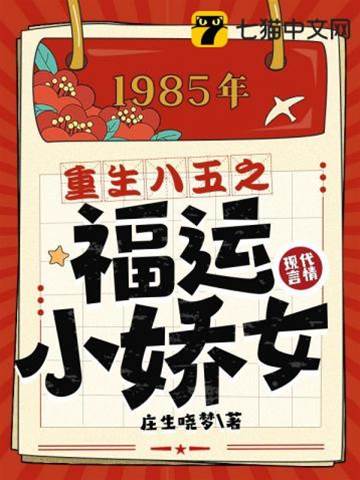
重生八五之福運小嬌女
前世,喬金靈臨死前才知道爸爸死在閨蜜王曉嬌之手! 玉石俱焚,她一朝重生在85年,那年她6歲,還來得及救爸爸...... 這一次,她不再輕信,該打的打,該懟的懟。 福星錦鯉體質,接觸她的人都幸運起來。 而且一個不留神,她就幫著全家走向人生巔峰,當富二代不香嘛? 只是小時候認識的小男孩,長大后老是纏著她。 清泠儒雅的外交官宋益善,指著額頭的疤,輕聲對她說道:“你小時候打的,毀容了,你得負責。 ”
70.5萬字8 19167 -
連載285 章
相親對象是富豪總裁
她著急把自己嫁了,不求此人大富大貴,只要沒有不良嗜好,工作穩定,愿意與她結婚就成。沒想到教授變總裁,還是首富謝氏家的總裁。……當身份被揭穿,他差點追妻火葬場。老婆,我不想離婚,我在家帶孩子,你去做總裁,謝氏千億都是你的,你想怎麼霍霍就怎麼霍霍。其實,她也是富豪。
50.8萬字8 1449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