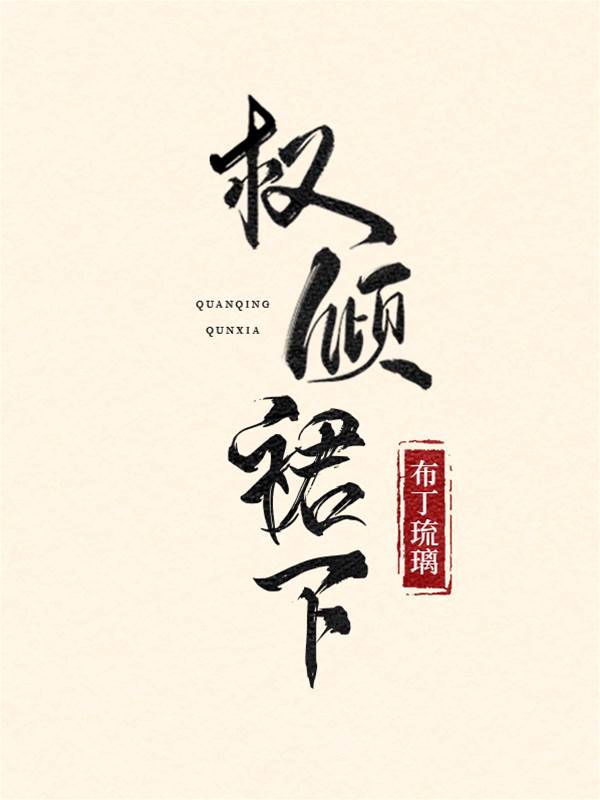《穿成虐文女主的長嫂》 第62章 抄家
譚孝閆抓著鐵欄桿,指骨那里因為用力顯得青白,他道:“你得答應我一個條件,不能放姓鄭的出去。”
他出不出去無所謂,鄭柄理得在牢里待一輩子。
譚孝閆瘋起來六親不認,他連徐燕舟都敢罵還有什麼不敢。他在寧州,一不小心命就沒了,還有什麼不能說。
鄭柄理都快被氣笑了,“譚兄,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我可曾得罪過你,你就如此記恨我。徐將軍,他這般胡言語,里能有幾句真話?”
雖然有窗,但牢房里還是暗,顧妙看了眼外面的天,已經暗了下來,道:“到底說不說。”
譚孝閆目有一瞬間的沉,徐燕舟也就算了,一個人還敢對他大呼小,“我在寧州做生意,一半利潤,都送到王府。”
大楚總共就一個王爺,便是永親王。
他是先帝的庶兄,不喜弄權,越是不正經的東西,就越喜歡,他有一個獨子,名為周寧敘,和他一個樣子。
譚孝閆道:“除了四利潤,還要從天下搜羅各種寶,越是珍貴的東西王爺就越喜歡。
名貴花草,前朝字畫,古玩玉石。反倒對金銀珠寶,不屑一顧。”
“我若有一句假話,就天打雷劈!”譚孝閆忽然笑了笑,“鄭柄理就是王爺的狗,明明我尋到的寶多,可他會擺尾乞憐,王爺給他的好多。”
一朝王爺,尊貴無比,哪怕沒有實權,也有人上趕著結。
鄭柄理神并不好看,他怔怔的,想說些什麼又忍住了。
顧妙拿出了一枚金牌,前面是一個令字,后面是繁復的花紋,“可認得這個?”
譚孝閆心里有幾分不屑,他瞥了一眼,道:“不認得。”
顧妙問:“花紋也不覺得眼?”
Advertisement
譚孝閆道:“都說了不認得,還要我說幾遍!”
顧妙問鄭柄理,“你見過嗎?”
鄭柄理道:“好像在哪里見過,但記不得了。”
“真見過還是假見過,我看他本就沒見過,故意這麼說!”譚孝閆說完,渾都舒暢了,“他這張里就沒一句真話。”
顧妙把金牌收起來,看向徐燕舟,“就問到這兒吧,他們兩個這麼關著也不是辦法。”
隔著一個鐵欄,吵的厲害,影響別人。
徐燕舟道:“那分開關?”
顧妙:“嗯,這邊朝南,能照到,譚老板還在這兒,鄭老板委屈些,關到里面吧。”
每間牢房都不一樣,自然是能曬到的好一些,里面沒窗,倒是有蟑螂老鼠。
譚孝閆和鄭柄理兩人沒一個好臉,譚孝閆還以為會放他出去。
顧妙道:“在牢房里閑著也是閑著,你們就發豆芽,也好好想想,到底見沒見過那枚金牌,我要聽實話。”
江一自告勇,“夫人,我去拿豆子,我來教他們!”
譚孝閆眼睛瞪大,“你說什麼!發豆芽?”
江一已經很懂了,“沒錯,發豆芽,不干沒飯吃,這也不強求,你要是干我就去拿,過了這個村就沒這個店。”
譚孝閆什麼時候發過豆芽,他連農活都沒干過,真是欺人太甚。
譚孝閆咬著牙道:“你讓我發豆芽……”
劉偉湛就不明白了,人都進天牢了,還有什麼不能干的,江一江三他們還是朱雀衛呢,不也發豆芽嗎。
他還是三品將軍呢,不也推磨養豬嗎。
劉偉湛問:“你是發不得嗎?”
顧妙看著這兩個人,當真是含著金湯匙長大的,沒干過活,看著桌上沒過的飯,道:“你們兩個誰做的好,就吃的好,不做就沒吃的。”
Advertisement
譚孝閆總算明白了,這世上不僅有鄭柄理這種口腹劍的小人,還有顧妙這種心思歹毒的子。
他要比姓鄭的吃的好。
“我干!”
鄭柄理點了一下頭,“……我也做。”
譚孝閆就是條瘋狗,他們謀劃一番,未嘗不能騙過徐燕舟,何必弄的這麼不面,現在誰都出不去。
現在好了。
顧妙道:“譚老板要是做的好,能出去放風。”
譚孝閆有點高興了,“放風?”
顧妙點點頭,“沒錯,可以出去。”
譚孝閆認真發了兩天豆芽,得到了一次外出放風機會。
寧州風景好,青山綠水,山上種滿茶樹,現在采的是最后一批春茶。
如今這茶山已經不屬于鄭譚兩家,顧妙想等茶農有錢了,可以用原來的價錢把山和炒茶方子贖回去。
也算歸原主。
顧妙頭發用布巾裹住,臂彎挎著竹筐,“譚老板跟著一起采茶,若有不懂就問茶農。”
譚孝閆想不通,在山上采茶和在牢房里發豆芽能有什麼區別。
無非是一個在里面一個在外面。
他何時采過茶,都是雇人。
譚孝閆問:“不采茶有飯吃嗎?”
劉偉湛說:“你在說什麼鬼話,當然是沒有了。”
譚孝閆吃的并不好,早上是稀飯饅頭,只不過他的是白饅頭,鄭柄理的是黑饅頭。
不吃午飯,他鐵定走不下山。
他從前出門都是坐轎子坐馬車,上山腳都磨出泡了。
譚孝閆也學聰明了,“我就問問,中午在山上吃?”
要在山上待一天,總不能不吃午飯,他現在就了。
劉偉湛也不采茶,只不過張大人說明后兩天可能有雨,他們才來幫忙。
劉偉湛道:“茶農一天兩頓飯。夫人人好,中午有飯。”
Advertisement
譚孝閆道:“有飯就好。”
劉偉湛嘆了口氣,譚孝閆這種人,一時半會也不會明白百姓不易,等干活多了,就知道了。
“你采的茶不行,老梗都放進去了,再這樣,中午就別吃飯了。”劉偉湛看譚孝閆的茶簍,“就這,能賣的出去?”
譚孝閆:“……我撿一遍。”
采了一上午茶,可算能吃中午飯了。
山上打的山野兔,還有在溪邊撈的魚,收拾干凈,肚子里塞上野蔥野蒜,香料,再刷一層蜂,架在火上慢慢烤。
帶來的干糧燒餅也烤一烤,把外皮烤,這樣才好吃。
只不過沒帶鍋,不然還能燉鍋魚湯。
顧妙吃了兩天青菜,想吃。
其他人更是無不歡的主,五只山六只兔子還有四條掌大的魚,都不知道夠不夠吃。
徐薇摘了一上午的茶,臉都曬紅了,坐在顧妙旁邊,看著火上的忍不住吞吞口水。
已經烤了長時間了,烤的金黃,不時會有油滴下來,本來山上是草木香,現在都是的香味。
徐薇記得他們在豫州那邊,吃了回烤魚,那魚什麼都沒放,半個多月沒吃,吃的也香。
這放了這麼多調料,烤的金黃,得多好吃。
徐薇道:“嫂子,咱們兩個吃一只,一只兔,一條魚吧!咱們能吃完!”
顧妙點點頭,“行,吃不完就帶回去。”
劉偉湛算了算,那他們還剩不,夠吃。
譚孝閆慌了,除了山上的茶農,顧妙帶了八個人,徐薇,劉偉湛,還有六個朱雀衛。
七個男人肯定比人吃的多,那他吃什麼。
譚孝閆有點燒的胃,吃慣山珍海味,連吃兩天白面饅頭,真的不住,他小聲問:“我……我也跟著一塊吃?”
Advertisement
劉偉湛看譚孝閆有些可憐,可山上的茶農更可憐,他道:“你吃骨頭。”
譚孝閆:“……”
中午吃飯,分了烤和兔子。
譚孝閆坐在石頭上汗,眼睛不住地往這邊看,香,真香。
大概是因為沒被過,他聞著比自己吃過任何名肴都好吃。
和兔子烤的金黃流油,一口一口餅,喝著山上的清甜的泉水,饞人的很。
譚孝閆吞了吞口水,他倉皇站起,走過去對著顧妙道:“我那天說的都是實話,令牌真的沒見過。”
“……鄭柄理……他應是故意那麼說的。”
譚孝閆了解鄭柄理,若真見過反而不會這麼說,他這樣無非是為了保全自己。
顧妙拿出了兩塊餅,又掰了一個兔子,譚孝閆直直盯著,問:“你同黎襄嗎?”
江二到鎮上的時候已經人去樓空,黎襄跑了。
譚孝閆聞著香味,腦子都不聽使喚,“認得,他每三月就來寧州一趟,來了也不住城里,而是去鎮上莊子里住半個多月。”
顧妙點了點頭,又割了一個兔,連著剛才的一起遞給譚孝閆。
譚孝閆沖著顧妙點了點頭,然后捧著吃的去了一旁,大口大口地吃起來。
顧妙把切小片,放在葉子上,跟徐薇慢慢吃。
顧妙看了眼譚孝閆,有些事想不通,都說永親王喜好玩樂,連世子都隨了他的子。
所以,永親王給他們庇護,譚孝閆便為他搜羅寶。
而黎襄幫著殺人放火。
為了喜好,連人命都不放在眼里,的確紈绔。
譚家鄭家有將軍府的東西,也說的過去,畢竟將軍府有不好東西,永親王玩膩了,就賞給他們了。
嶺南城守府室里的屏風,也是徐家的東西。
也許他們都是永親王的人,譚孝閆為他攬財,嶺南城守為他攬權。
顧妙咬了一口,烤的焦黃,還有點點甜味,問:“薇從前去過永親王府嗎?”
徐薇道:“王妃辦過賞花宴,我去過幾次,可實在想不起是在誰上看過那種花紋。”
這種花紋,除了子的飾上,應該不會出現在別了。
那花紋細,上面的花看著像牡丹,又像荷花。
徐薇仔細回憶,發現無論是擺,帕子,還是屋里的紗帳上都沒有這種花紋。
顧妙道:“那先不想了,你大哥去搜黎家,興許能搜到,快吃飯。”
顧妙干了一上午的活,肚子得厲害,和徐薇分了一只,又吃了幾口兔魚,剩下的用葉子包起來,準備帶回去。
譚孝閆看的眼饞,可活了這麼多年,真做不出要人吃剩下東西的事。
他只能多干點活,多想點事,這樣晚上才能多吃點。
譚孝閆生平最厭惡鄭柄理這種人,結果,他現在了自己最討厭的人。
不過,靠著一張,就能得到想要的東西,還舒服的。
下午轉瞬而過,最后一波春茶采完,要等六月再上山采夏茶。
顧妙讓茶農們先回去,然后給徐薇指了一片坡地,“以后這一片要種莊稼。”
民以食為天,茶葉只有有錢人喝得起,寧州是山城,山上茶樹多,空著的地就開荒種糧。
就如張先言設想的,開梯田,上面種小麥花生稻谷,以后百姓就有糧食吃。
徐薇點點頭,“云州還有許多荒地,都開出來,以后地越來越多,就不愁吃了。”
顧妙點點頭。
一步一步來,先吃飽再吃好,日子會慢慢好起來。
一行人下山,晚風吹著,倒也涼爽。
張先言從地里回來,他鞋上沾著泥土,肩頭扛著刮鋤。“地里草多蟲多,得想個法子……譚老板,你好啊。”
譚孝閆累了一天,一點都不好。從前,他沒給張先言使絆子,現在風水流轉,到張先言跟他說風涼話了。
譚孝閆頂著一張土臉道:“好得很,多謝張大人掛懷。”
張先言不得譚孝閆倒霉,“那就好,譚老板這是回……牢房?”
譚孝閆是炮仗,一點就炸,尤其張先言還往他心口刀子,“你他娘的什麼意思!”
“譚老板注意言辭。”
譚孝閆氣的臉紅脖子,他控訴道:“他先者賤!”
顧妙自然是向著張大人的,“張大人也沒說錯,你難道不回牢房。”
譚孝閆這輩子就沒過這麼大的委屈,他道:“我回不回還不是你說了算!”
顧妙道:“那你得回。”
譚孝閆:“……”
既然必須回去,面子得有,譚孝閆沖顧妙要了那半只兔子,帶回去,還特意去給鄭柄理看了看。
在牢里待了兩天,鄭柄理服也臟了,頭發也了,他邊是三個豆芽筐,鄭柄理正蹲著給豆芽灑水。
譚孝閆站在門口,道:“鄭兄,好久不見,別來無恙呀。”
鄭柄理記得,他們都在牢房,雖然離得遠,也能看見,他們早上才見過。
鄭柄理:“滾。”
————
顧妙晚上給徐燕舟他們做的熱乎吃食。
燥子面,上面鋪一個荷包蛋,小青菜撒了一大把,又熱乎又管飽。
徐燕舟道:“搜出來三百多兩銀子,黎家是空的,莊子也是空的,其他什麼都沒有。”
黎襄估計已經回盛京了,他們白跑一趟。
顧妙道:“那黎家拆了,三百兩銀子,正好養豬養,種菜種瓜。”
劉偉湛拍手,“好,黎家大的很,能養一百多頭豬。”
顧妙什麼時候給過三百兩銀子讓他買豬!
張先言也道:“黎家花園花草多,土好,種出來的瓜果鐵定好吃,有,別的地方也能變好土。”
顧妙道:“對了,明月樓和賭坊怎麼置。”
徐燕舟對這兩個地方深惡痛絕,恨不得把青樓賭坊全拆了,顧妙問了,自然是任置。
徐燕舟道:“聽你的。”
劉偉湛心想,那可是姑娘樓,不會真一樓酒樓二樓鹵味三樓豆腐吧。
顧妙問:“明月樓里姑娘好看嗎?”
徐薇悄悄豎起了耳朵,看著兄長和楚淮,等著他們回答。
徐燕舟眨了一下眼,楚淮把筷子放下。
徐燕舟道:“沒仔細看,不知道好不好看。”
楚淮道:“就看見花花綠綠一片,看的眼睛疼眼睛疼,就沒看。夫人,你可以問劉將軍。”
一群人齊齊看著劉偉湛,劉偉湛多覺得有些不自在。
怎麼了,他看怎麼了,他一個大男人,沒婚沒家,看看漂亮姑娘怎麼了。
除了后面進來那幾個大娘,其他人還湊合。
劉偉湛把筷子放下,道:“……不好看。”
作者有話要說:
這是一更!
啾咪!
猜你喜歡
-
完結307 章

妃揚跋扈:重生嫡女好妖嬈
上一世鳳命加身,本是榮華一生,不料心愛之人登基之日,卻是自己命喪之時,終是癡心錯付。 重活一世,不再心慈手軟,大權在握,與太子殿下長命百歲,歲歲長相見。 某男:你等我他日半壁江山作聘禮,十裡紅妝,念念……給我生個兒子可好?
56.5萬字8 7103 -
完結201 章

逆天嬌妃:皇上把持不住
宋微景來自二十一世紀,一個偶然的機會,她來到一個在歷史上完全不存在的時代。穿越到丞相府的嫡女身上,可是司徒景的一縷余魂猶在。
52.1萬字8 27669 -
完結148 章

丞相重生后只想擺爛
柳枕清是大周朝歷史上臭名昭著的權臣。傳聞他心狠手辣,禍亂朝綱,拿小皇帝當傀儡,有不臣之心。然老天有眼,最終柳枕清被一箭穿心,慘死龍庭之上。沒人算得清他到底做了多少孽,只知道哪怕死后也有苦主夜半挖開他的墳墓,將其挫骨揚灰。死后,柳枕清反思自己…
57.7萬字8 9491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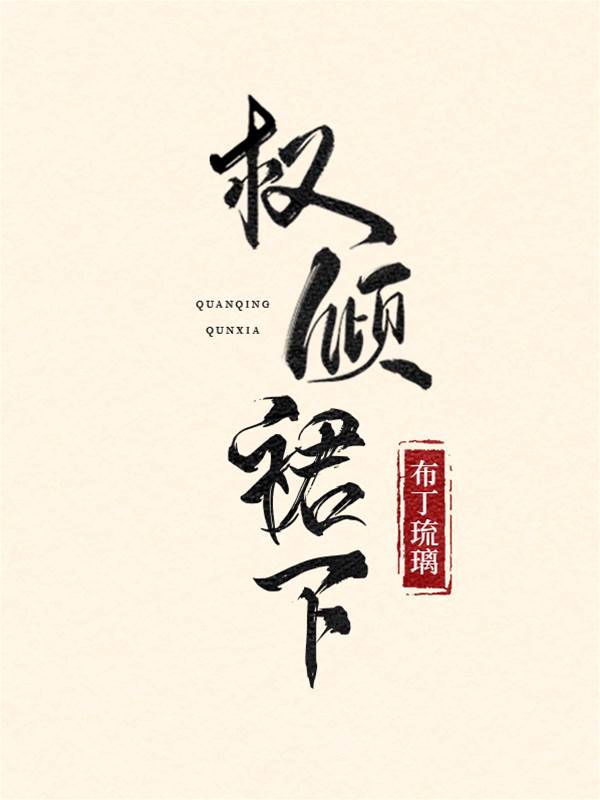
權傾裙下
太子死了,大玄朝絕了後。叛軍兵臨城下。為了穩住局勢,查清孿生兄長的死因,長風公主趙嫣不得不換上男裝,扮起了迎風咯血的東宮太子。入東宮的那夜,皇后萬般叮囑:“肅王身為本朝唯一一位異姓王,把控朝野多年、擁兵自重,其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聽得趙嫣將馬甲捂了又捂,日日如履薄冰。直到某日,趙嫣遭人暗算。醒來後一片荒唐,而那位權傾天下的肅王殿下,正披髮散衣在側,俊美微挑的眼睛慵懶而又危險。完了!趙嫣腦子一片空白,轉身就跑。下一刻,衣帶被勾住。肅王嗤了聲,嗓音染上不悅:“這就跑,不好吧?”“小太子”墨髮披散,白著臉磕巴道:“我……我去閱奏摺。”“好啊。”男人不急不緩地勾著她的髮絲,低啞道,“殿下閱奏摺,臣閱殿下。” 世人皆道天生反骨、桀驁不馴的肅王殿下轉了性,不搞事不造反,卻迷上了輔佐太子。日日留宿東宮不說,還與太子同榻抵足而眠。誰料一朝事發,東宮太子竟然是女兒身,女扮男裝為禍朝綱。滿朝嘩然,眾人皆猜想肅王會抓住這個機會,推翻帝權取而代之。卻不料朝堂問審,一身玄黑大氅的肅王當著文武百官的面俯身垂首,伸臂搭住少女纖細的指尖。“別怕,朝前走。”他嗓音肅殺而又可靠,淡淡道,“人若妄議,臣便殺了那人;天若阻攔,臣便反了這天。”
52.5萬字8 2214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