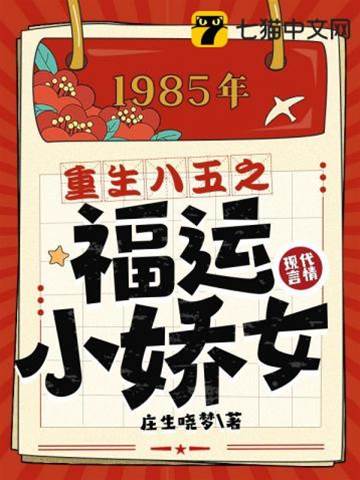《丈夫下鄉后[七零]》 第67章 前途光明
“媽媽你們為什麼關門?”
衡衡蹬蹬跑到床邊問,這小孩兒年紀小但卻有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倔病。
喬茗茗:“你爸幫我涂藥唄。”
這沒啥不能說的。說完,起下床,藥也涂得差不多了。
衡衡輕蹙眉頭忙追問:“媽媽傷啊嗎?”
呦!還曉得傷才是涂藥呢。
“是啊,生你和妹妹時好痛的,疤痕留到現在所以還得涂藥才行。”
喬茗茗說著,把手放在火爐上烤烤,然后拉著衡衡到面前,把他上棉襖的扣子打開,然后從他領往服里手。
“媽媽那你現在還痛……媽媽!!”
衡衡得直,喬茗茗干脆把他抱,了后忍不住給他一個腦瓜崩兒。
“你瘋跑了是不是?”喬茗茗瞪他,“怎麼里頭的服都了。”
大冬天的,和寧渝還在堅持每天洗澡,但是小孩兒卻只讓他們五天洗一回,平常隔天就行。
衡衡昨天才洗的澡,服還在火塘邊烤呢,這會兒又得洗。
喬茗茗他臉蛋,起去把門關上,了這孩子的服,把他那已經被汗浸的秋換下來,到柜子里翻了翻,拿一件干爽的秋再套上去。
衡衡笑嘻嘻說:“我們在太爺家玩兒跳繩,我跳了五次呢。”
喬茗茗:“……”
“是兩個人牽著的跳繩嗎?”問。
“對啊對啊,和哥哥姐姐們跳。馬蘭開花二十一嘛,媽媽你會跳嗎,要不要我教教你呀。”
喬茗茗“哼”了一些,不屑極了。
“教你媽媽我你恐怕還不夠格呢。”小時候也常跳,沒人幫忙牽繩時還會用椅子來代替。
“是嗎,那媽媽教我吧……”
“去,自己看書去。”
Advertisement
說話間,外頭的雪又大了。
寧渝不曉得從哪里搞了一把松針回來。
松針這玩意兒好似越冷越翠綠,半點不懼寒冷,在這白茫茫的大地上極其奪人眼球。
喬茗茗站在門口,看他修剪松針,剪完后把碧綠的松針進花瓶中,放在書桌上。
屋外白雪皚皚,隔著一扇窗戶的屋卻有一束碧綠,好似讓整個房間都靈起來。
“你從哪里搞來的?”喬茗茗好奇。
寧渝鼻尖紅紅:“山腳。”
是了,后山山腳是有一棵松針樹。
寧渝修剪完松針,又把剩下的松針葉子給剪下來,洗了又洗后放在籃子里道:“這東西還能煮著喝,松針茶。”
喬茗茗心說你可真有閑心。
可寧渝的這些“閑事”,確實能給無聊的冬日生活帶來一些小趣味兒。
看慣了蒼白的雪時,書桌上的一束翠綠松針異常養眼。
喝慣春天的野茶時,那松針煮后的滋味兒也很是清新。
他會趁著雪停之時上山下套子,等再一次雪停后又上山收套子。
這時候他往往會帶一兩只野兔回來,喬茗茗就會興地把野兔給剁小塊,放辣椒炒,炒個香辣兔丁吃吃。
通常這時候喬茗茗還會跑去找舅爺要一壺自家釀的米酒,亦或者是春末夏初時釀好的楊梅酒。
十一月中旬的時候就斷了,彰彰和哥哥一樣都能接羊,加上盛的輔食和首都寄來的,所以喬茗茗喝酒也沒啥。
舅爺不僅做子彈有一手,釀酒更是厲害。
夫妻倆把孩子放在房間里,自己跑到火塘邊點起炭火小酌一杯,熱酒加上香辣無比的兔丁,把里的寒冷都給驅散,那覺得不行!
總這樣吃也容易上火,喬茗茗一上火脾氣就容易暴躁。
Advertisement
寧渝又是涼茶又是鴨子湯,甚至還帶去冰釣。那湖上刺骨的冷風,莫名對降喬茗茗的躁火有奇效。
冬日也好的。
喝著松針茶的喬茗茗如是想到,就是不曉得小弟這會兒在干啥呢,算算日子,他應該也回來了吧?
首都。
喬小弟坐在供銷社中,心里直打鼓,但還是提著一口氣,和面前這位供銷社主任討價還價(據理力爭)有關明年定金的事兒。
今年這批貨的錢已經說好了,比喬茗茗和周隊長估算的都要高些,足有一千八百多。
一是通方面的本人家卓主任諒了。
二是這山柚油是農民兄弟們辛辛苦苦搞出來的,屬于比較見的農產品,卓主任愿意給個方便。
加上首都的各個供銷社暫且都沒見到,所以他們供銷社就是獨一份,獨一份的東西總是有點兒吸引力的。
就是卓尋雁了。
卓尋雁那是半點不把爹當爹啊,來首都前被喬茗茗臨時拉去培訓了一下商場話,正于興致高昂的時期呢,擺出一副生意場上沒父的模樣。
要知道,卓尋雁和喬小弟是同樣的年紀,放在幾十年后兩人都還是高中學生,最是較真,也最是想讓長輩把他們當大人看的時候。
這種歲數的小孩兒自尊心強,卓主任心說閨兒來跟他談生意不就是過家家嗎,于是便抱著一陪人家玩兒的敷衍心態,這真真惹急了卓尋雁,深覺得自家爹這是小看自己,于是坑起爹來毫不手。
卓主任只愿意給一千六,而喬茗茗的底線也是一千六。
但卓尋雁可不樂意,底線之所以是底線,就是說明誰來都能談一千六!
這樣看,有何用?
卓尋雁擼起袖子,在家里就和爹據理力爭:“卓華同志,我鄭重告訴你,這山柚油必須一千八,最一千八!”
Advertisement
說著,掏出塊生姜來飛速一抹,立刻聲淚俱下:“我們村兒,從開春后就得去除草,為了節省農藥,農民兄弟們得早晨六點,六點拿著鋤頭上山,還要帶著飯,在山上吃飯!除上一天,傍晚六點才能收工!”
卓尋雁邊說手指邊比出個“六”來,眼淚控制不住地啪嗒啪嗒掉,另一邊手捂住口,仿佛得了什麼大病。
卓主任:“……”
別以為他沒有聞到生姜味兒。
還有啊,他閨兒剛去幾個月,怎麼就一口一個“我們村”了?
卓尋雁淚再淚,接著道:“除完草又要澆水,還得施。卓華同志,你本不曉得施有多辛苦。有料好說,料不夠還要用農家!”
卓主任心說:你爹我也不是生來就是主任的,也在田里撿食撿了十幾年,可比你這種半吊子懂得多。
卓尋雁最后道:“到了收獲的時候,還要起早貪黑的去采油茶果,采完得曬,曬了得殼取油茶籽……”
到這兒哭得非常真,嗚咽說:“你閨我之前采得快累死了,你竟然就給我一千六,竟然只有一千六!”
狠狠控訴。
卓主任:“……”
不是啊,做生意沒你這麼來的。
他是個特別能堅持底線的同志,奈何他那被支出去的老娘提早回來了,見到孫哭得眼淚嘩嘩流止都止不住,就雙手一叉腰開始罵兒子。
“不給就不給唄,怎麼還欺負人啊。人家搞了大半年的東西,就靠著這個掙錢,滿心滿眼運到首都來,能讓人家失嗎你。我告訴你卓華,你不能這麼給人家老鄉價!”
卓主任:???
他手一擺,干脆不說話。
這生意沒法談了,生意就是生意,真不應該摻和進閨老娘來。
Advertisement
賊啊,真賊,那村里竟然派閨兒來,也不跟個主事兒的人,有個主事的人反而能好辦許多呢。
卓主任又嘆氣,也是他自己賤的慌。
瞧瞧,人就是不能有私心,當初私心想見見閨,想讓閨好過點,如今……
唉!
他又算了算賬,考慮許久,最終松口把錢提到一千八。
這批貨錢的事兒解決完,接下來就該由喬小弟去解決明年定金的事兒。
卓主任想看看效果,萬一賣得不好他不定都有可能,但喬茗茗不是很想放過他。
最重要的是想讓小弟通過他,多認識幾家其他供銷社的主任,總不能就指著卓主任對吧。
不過這事兒還早著,起碼得瞧瞧山柚油在首都賣得好不好再說。
喬小弟從早晨八點談到中午十二點,談得口干舌燥,終于拿下百分之十的定金。
隨后,又起笑笑說:“卓主任這是我們公社的電話,您往后有事兒可以直接聯系我們。”
卓主任臉上也笑呵呵,心里想著和你們做生意累得慌,早知道的話他一定是會重新謹慎考慮的。
理完首都的事兒,喬小弟就準備回綿山了。
此時喬家已經在新家生活了四天,徹底適應了新家的生活。
于喬家的人口來說,新家即使比老房子大好多,住起來還是有點擁的。
不過即使這樣,喬母也沒把隔壁喬茗茗的小房間收拾出來讓家里人住進去。
家里的很多事是說不清的,特別是他們這種多子人家,就應該從子上把關系掰扯開來。
家里再都不能住到隔壁房間去,等往后住著住著小妹回來了,你說兩邊的孩子心里都有沒有疙瘩?
小妹那心大的估計是沒有,但你不能因為人家小妹心大就委屈人家是不是?
喬母實在是被幾年前二兒媳頂工作的事兒嚇到了,從那時候起就忽然意識到孩子們都家了,有太多的關系啊啊摻雜進來,自己老兩口對于一些事已經有心無力了。
喬母心里有時候真難的,有時候甚至想著要是都住出去就好了。逢年過節回來吃頓飯,看看他們老兩口,這生活多自在。
喬小弟臨走前,喬母收拾了一堆的東西:“你給我老老實實背去,這兩袋記得千萬放好。小妹那死丫頭真是的,彰彰才幾個月啊就敢斷。哎,斷就斷吧,可憐我彰彰了,當年衡衡是這樣,彰彰又這樣,這當娘的都不曉得心疼娃。”
喬小弟聽不下去:“彰彰養得好,二姐可心疼了,每天蛋喂著泥吃著,那小孩鬼鬼的,才不喝呢。”
喬母踢他:“你懂個屁,娘上的才是最好的。”
喬小弟不說話了,他永遠是爭不過他媽的,看看左右,一把將大侄子手上的凍梨搶來,然后躲回房間。
“,!小叔欺負人!”
馬上十一歲的喬榮軍對小叔的這種行為表示譴責,叨叨個不停,等他媽回來時屁挨了一掌才停下。
第二天一大早,喬小弟又背著大包袱離開首都。
這次離開首都,心中沒有惶恐不安,只有欣喜和期待。
這次任務圓滿完,可不得欣喜嗎!
又是長時間的火車,兩天后,兩人終于到達屏北縣。
此時的喬茗茗已經把小弟拋腦后去了,正在樂此不彼地試著家里的電燈。
好幾天過去,每次打開電燈時都幸福滿滿。
冬日的天黑得早,喬茗茗每到傍晚時就把電燈打開,屋里頓時燈火通明。
“來來來,開課了!”燈一裝,就有興致抓著衡衡學認字。
寧渝收拾著飯碗,臉上含著笑。
衡衡一聽這話就想跑:“我不學了,我只想聽故事。”
喬茗茗皺眉:“你不學等你牙齒掉了怎麼和我們流呢?”
衡衡:“大家都掉,大家都丑,這樣我就不怕。”
彰彰聽著咯咯笑:“丑丑丑!”
喬茗茗:……
孩子越大越不好糊弄怎麼辦?
不學就不學吧,喬茗茗心說要是可以的話最想教的是外語。
再過十幾年,等到衡衡上學的時候外語可重要了,那時候是出國,如果可以的話出國走走,看看其他地方的風土人也不錯。
但是吧,就是不曉得這小孩會不會大的說出去。
喬茗茗沉思片刻,扔了教鞭,去廚房找寧渝。
屋外是厚厚的積雪,但房子的屋檐在今年夏天的時候被寧渝加寬了,又用石板鋪出一條到達廚房的道路來,所以從屋檐底下的小道上可以直達廚房了,此時會方便許多。
寧渝正在洗碗,喬茗茗湊過去,小聲說了這事兒。
“你會英語?”寧渝問。
喬茗茗:“你看不起人!”
寧渝:“沒有啊,咱們學的不是俄文嗎?”
喬茗茗:“……”
抱歉,給忘了。
喬茗茗立刻改口:“不是還有你嗎,你肯定會英語的,要不然教俄語也行。”
寧渝搖搖頭:“俄語不行,一是太難,二是俄語多人學的,萬一衡衡不小心說一,不人都能聽得出來。”
也對!于是喬茗茗期待地看著他:“趁著衡衡小,你教衡衡英語,我在旁邊剛好聽著。”
寧渝邊洗碗邊點頭:“行啊。”
喬茗茗登時高興了,剛轉想走,就不思考寧渝為什麼答應得這麼利索。
按照當下的形來看,顯然不教才是最好的,這時代的浪之中,誰能肯定希就在幾年后呢?
又怎麼肯定,學外語的重要能得過此時學外語的風險呢?
想到這里,喬茗茗忽然發現,寧渝好像一直都淡定的。
在信上和謝善文談起未來之事時,都勸人家放寬心,仿佛一副對未來充滿希的模樣。
說起老師,他擔憂老師的,但話里話外都著老師肯定能平反的意思。
從前喬茗茗沒聽出來,這會兒突然想到,總覺得什麼地方怪怪的。
喬茗茗是個直子,有話就問了。
天已暗,黑暗中寧渝手一頓,然后笑了笑道:“我要去找大隊長借書了,你真應該把《關于重慶談判》找出來看看。”
喬茗茗聽得云里霧里,翻了翻記憶,才恍然大悟。
這本書上說:總之,前途是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喬茗茗看向寧渝的眼神里,頓時充滿崇拜。
人才啊,能記得這麼。
猜你喜歡
-
完結73 章

霍先生的妄想癥
薛小顰通過相親嫁給了霍梁。 這個從骨子里就透出高冷與禁欲的男人英俊且多金,是前途無量的外科醫生。 薛小顰以為自己嫁給了男神,卻沒想到婚后才發現,這男神級的人物竟然有著極為嚴重的妄想癥。
24.6萬字8 9100 -
完結3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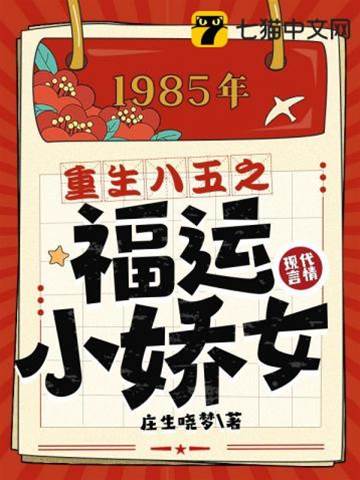
重生八五之福運小嬌女
前世,喬金靈臨死前才知道爸爸死在閨蜜王曉嬌之手! 玉石俱焚,她一朝重生在85年,那年她6歲,還來得及救爸爸...... 這一次,她不再輕信,該打的打,該懟的懟。 福星錦鯉體質,接觸她的人都幸運起來。 而且一個不留神,她就幫著全家走向人生巔峰,當富二代不香嘛? 只是小時候認識的小男孩,長大后老是纏著她。 清泠儒雅的外交官宋益善,指著額頭的疤,輕聲對她說道:“你小時候打的,毀容了,你得負責。 ”
70.5萬字8 19147 -
連載940 章

替嫁新婚夜,植物人老公要離婚
甜寵1v1+虐渣蘇爽+強強聯合訂婚前夜,林婳被男友與繼妹連手設計送上陌生男人的床。一夜廝磨,醒來時男人不翼而飛,死渣男卻帶著繼妹大方官宣,親爹還一口咬定是她出軌,威脅她代替繼妹嫁給植物人做沖喜新娘。林婳???林婳來,互相傷害吧~林妙音愛搶男人?她反手黑進電腦,曝光白蓮花丑聞教做人。勢力爹想躋身豪門?她一個電話,林氏一夜之間負債上百億。打白蓮,虐渣男,從人人喊打的林氏棄女搖身一變成為帝國首富,林婳眼睛都沒眨一下。等一切塵埃落定,林婳準備帶著老媽歸隱田園好好過日子。那撿來的便宜老公卻冷笑撕碎離婚協議書,連夜堵到機場。“好聚好散哈。”林婳悻悻推開男人的手臂。某冷面帝王卻一把將她擁進懷中,“撩動我的心,就要對我負責啊……”
112.4萬字8.18 3155 -
連載833 章

人潮洶涌
周稚京終于如愿以償找到了最合適的金龜,成功擠進了海荊市的上流圈。然,訂婚第二天,她做了個噩夢。夢里陳宗辭坐在黑色皮質沙發上,低眸無聲睥睨著她。驟然驚醒的那一瞬,噩夢成真。陳宗辭出現在她廉價的出租房內,俯視著她,“想嫁?來求我。”……他許她利用,算計,借由他拿到好處;許她在他面前作怪,賣弄,無法無天。唯獨不許她,對除他以外的人,動任何心思。……讓神明作惡只需要兩步掏出真心,狠狠丟棄。
149.8萬字8.18 260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