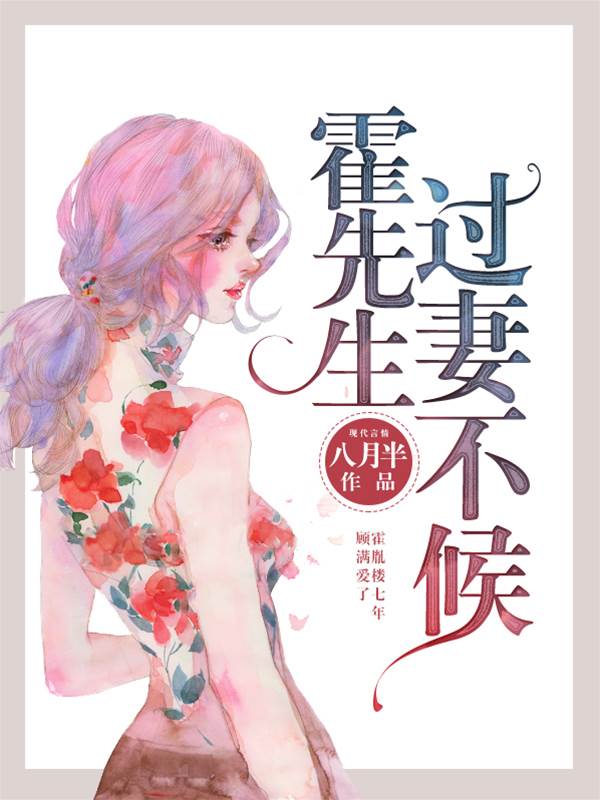《我的機長大人》 第20章 第二十章
出題的乘務長林姐是在北航出了名隨和的人, 給空乘寫的題目大多都十分基礎且日常,比如遇到印度乘客英文口音太重聽不懂怎麼辦,遇空管延誤一小時以上怎麼理。
氣氛輕松,空乘們玩得不亦說乎。
然而新飛們就不是了。
單屹的問題, 對比乘務長的春風十里, 那就是突然驟變冬日的強勁寒風。
單屹的問題尖銳且專業, 那些從來沒領略過單屹棒式教育的一群男新飛, 此時面對單屹悠悠坐在一旁無聲看著你回答不上的眼神, 直接背脊骨都發寒。
到莊棟梁的時候,對方誠誠懇懇地投降:“我錯了!我沒用!我去跳蛙跳!”
全場的人都笑了。
王酈安卡在了A320故障應急的問題上,在座位前的站姿直, 拿著手上問題的紙眼神看不出波瀾。
A320與B737的艙位圖不一樣, 改裝機型是B737,這問題不在的范疇。
新飛里頭改裝的機型各不相同,單屹出的問題也是,王酈安只是隨機到一個與自己機型不相符的。
主持人表示王酈安可以重新一遍,卻拒絕, 直接走到驚喜箱旁,從里出一張紙條。
主持人贊王酈安這個舉夠漢子,隨后打開對方的紙條, 主持人的表便彩了起來。
在場都是年輕氣盛的都市男, 匿名問題,鐵定都帶著一點耐人尋味的話題。
主持人:“請問Villian的第一次是多歲呢?”
在場的氣氛瞬間無聲熱了一個度。
安無聊般努了努。
這個問題似乎在真心話大冒險里已經被問爛了,仿佛這個游戲里就問不出別的什麼新鮮玩意兒似的。
Advertisement
王酈安聞言, 表輕蔑, 沒有回答。
這個游戲無非就三個字, 玩得起, 玩不起的人也沒有人會勉強,主持人見慣場面,笑著說:“Villian也可以選擇蛙跳?”
這是一句調和氣氛的話,莊棟梁此時還有半圈沒跳呢,聞言起招手:“來!”
原本尷尬的場面便又輕松了下來。
王酈安在此時開口:“沒有這個經驗,回答不了這個問題。”
在場不人因為這個答案瞬間挑眉,有的無聲換了個眼神,有的明目張膽投去探究目,反正站著的人似乎了一個被研究對象。
安突然就覺得沒啥意思了,聊兩很正常,但就因為沒有經驗,所以用那種眼看生,就很無聊,甚至有點弱智,好像在這個社會沒上過床是件多麼稀奇古怪的事一樣。
這會安連正經回答問題的心都沒了,站起來,隨便出一個問題給主持人。
主持人:“請問,如何才能在所有儀表都失靈的夜晚安全著落?”
安將耳朵轉向對方,閑散地聽著,聽完后:“……”
主持人:“別看著我啊,我要是知道答案我就不當空了。”
安轉而將頭轉去單屹的方向。
安:“如果我也知道的話,我就不是坐在這里,而是坐在那里了,你說是吧?”
那里,指的是單屹那邊隔岸觀火的位置。
眾人笑。
單屹面無波瀾地挑了挑眉。
安在驚喜箱里了很久,主持人拿到紙條看了后不由“wow”了一聲,他問安:“安還記得當初第一次實上機的覺嗎?”
安點頭:“然后呢?”
主持人笑了笑,將紙條遞給:“那麼請問,跟第一次做.相比,哪個更刺激呢?”
Advertisement
話一落,饒是安這種賊能打馬虎眼的人也頓時沉默了:“……”
要是換作平日里跟阿man吹大炮,安肯定毫不恥地說:那必須是后者了,飛機隨時都能開,極品可不是隨時都能上。
要是換作別的任何一個真心話大冒險里,安也能隨便給出一個答案,前者或后者,選擇題而已,二選一隨便就唬弄過去了。
但此時張了張,卡住了。
安下意識朝單屹那方向瞥了一眼。
對方的座位坐在圓圈的另一頭,禮堂大燈正好懸在頭頂上方,廓的影在單屹臉上猶顯分明,將其切割晴兩面。
安看著對方這幅模樣就想起了對方懸在上方的樣子,一大片影籠罩,眼睛里一整片翻滾的海。
手心都了。
主持人在一旁笑:“安在想自己蛙跳能跳幾圈嗎?”
安擺了擺手,跳了快兩個月,不想再跳了。兩者相較選其輕,這時開口,選了一個不容易延展并幻想的答案:“上機實。”
主持人朝舉起了拇指,底下不知是誰藏在人群里笑道:“男人聽了都要哭。”
場子氛圍松弛過了度,有人玩笑般說道:“男人不行可不行啊。”“是現男友嗎?”“小孩,別問。”
這話意思晦又明了,下面笑聲又是一片。
安覺得后背在滴汗:“行行好,停了停了,給點面子。”
哪知道底下笑聲更甚了。
安夾著尾逃逸,完事了,事不關己地坐下,目下意識一抬,落到單屹頭上,對方平靜地坐在座位上,目藏在影底下。
這個游戲進行到這,單屹一直都于半只腳踏進來另外半只腳還在岸上的狀態,角噙著笑,之泰然,又置之度外。
Advertisement
單屹的目完全沒落在安上,安便坐在位置上肆無忌憚地研究著這個男人。
Man:普通男人喜歡弱妹,極品應該不是。
Man:野的男人喜歡野的人,想拿下極品,你野給他看。
安:靠譜?
Man:野一下不就知道了?
安看著對面的單屹,吧唧了一下。
野?
在行。
游戲過半時,新飛們已經全完了,剩下的都是一幫玩嗨了的空乘,單屹在這時與旁的人留話告別,起離開了禮堂。
沒過一會,安也撤了,口得厲害,呆到這會已經是極限了。
海口的夜晚又悶熱,風帶起發拂過臉龐,黏糊了安一。
抬起頭,云層稀薄,明星閃爍,倒也還是帶著月朗星稀的清爽。
基地的食堂早關了,安一路走出了基地。
基地一公里外有個小賣部,從基地往小賣部只有一條筆直的笑路。
安慢悠悠地走著,路一旁每隔一段距離便有一盞路燈,玩起了踩影子的游戲。
晚上十點多,要不是突然來了個客人,小賣部的老板已經打算拉閘了。
小賣部外的空地上擺了兩張桌子,樹影婆娑,坐在桌前抬頭剛好出一個圓潤的月亮。
單屹坐在其中一張桌子前,桌上是一瓶喝了一半的黑啤。他從禮堂離開時正巧來了通電話,此時的他正帶著藍牙耳機,在跟他兩歲的小外甥語音著。
男孩子的聲音十分稚:“舅舅,媽咪說你這輩子要打了,什麼打啊?”
“我不知道,你讓你媽媽解釋解釋。”
電話那頭的小外甥認真地點頭:“噢噢,好!”
隔了一會,那頭重新傳來蹦跶過來的聲音:“舅舅,媽咪說,打就是老男的意思。”
Advertisement
“舅舅你是老男嗎?”
“……”真是瘋了,“喊你媽聽電話。”
下一秒,“媽咪——舅舅喊你聽電話!”
小外甥扔下手機就跑了,單屹的耳機傳來一陣雜音,他百無聊賴地抬起眸,便看見遠的路燈下走著一個人。
那人穿一長大褂,路燈將遠那人的影子拉長又短,而那人就像個傻子一樣,起擺,低著頭,對著自己的影子蹦蹦跳跳。
不多會,遠那人毫無預兆地抬頭,蹦跶的作頓了頓,原地長了脖子。
人瞇著眼睛努力眺,沒多久,看清了,然后撒開就往這方向跑。
單屹不為所,自個兒拿起啤酒喝了一口。
單屹酒瓶才剛放下,安就氣吁吁地站在他面前:“好巧啊機長,你在干什麼呢?”
與此同時單屹電話那頭被丟掉的手機終于給人撿起,然后明知故問地裝:“哥?在干什麼呢?”
單屹看著安,說道:“在跟傻子聊天。”
安:“嗯?”
電話那頭:“你說誰呢!?”
單屹瞬間笑了,然后將耳機摘下,拋在桌上,順道把電話掛了。
桌上的啤酒罐掛著水滴,著冰冰涼涼的氣,安了半天,此時眼饞心也饞:“你在喝酒?你的酒看上去很好喝。”
單屹:“有錢自己買,沒錢干站著。”
安轉就跑去小賣部要了兩罐啤酒,當場撕拉開其中一罐,瓶口滾出虛白的霧氣,安迫不及待灌下去幾口,然后舒爽地嘆了口氣。
隨后坐到了單屹對面,將另一罐啤酒砸在單屹的桌上,十分豪邁地說:“請你的!”隨后擅自跟對方了杯,仰頭又喝了一口。
單屹無于衷:“我不喝人請的酒。”
安張就來:“別當我人,徒弟請的酒,后天考核,賄賂教///員。”
單屹:“知道憑實力過不了是吧?”
安:“怎麼可能?教///員卡人不算。”
單屹角隨意一挑:“不排除這個可能。”
安頓時皺起了眉頭,舌也跟著生津。
單屹這個男人笑起來真是要命地好看,清冷又,誰靠近都得起點歪心思。
安那顆心此時在單屹的面前得跟什麼似的。
野嘛……
天時地利人和都來了。
安將椅子往單屹那邊挪了挪,見對方不為所,將椅子又挪了挪,直到的大褂邊到對方的邊。
一抬頭,看見單屹涼薄著眼眸一聲不吭地看著,目清冷,帶著一人間正道抓著個狐貍一樣的煞氣。
可看在安眼里卻不一樣了,喝了酒的神仙,那冷颼颼的飄飄仙氣還是染上了幾分凡塵俗氣,人熱的,氣也是熱的。
神仙突然了起來,高高在上,不手不口,就讓安一顆七六心迷得哪哪都不著調。
安將桌上那罐沒開的啤酒給單屹拉開,鋁罐蓋撕拉的一聲,水汽拉拉在瓶口跳躍,遞給他:“這個牌子好喝,冰的。”
單屹沒有手,安便將啤酒在了他的手臂上,頓時在他手臂上留下一塊水跡:“天氣熱,一下舒服。”
安見他還不說話,又自個兒在那嘀嘀咕咕。
單屹這會終于了,他將手臂移開,垂眸:“你想說些什麼?”
安嘻嘻地笑:“明人不說暗話,我想跟你朋友。”
一抹淡薄的笑意攀爬至角,單屹問:“哪種朋友?”
安反問:“哪種朋友?”
單屹:“在手機里躺列的朋友,還是能上床的朋友?”
安吞咽了下,片刻后才問:“能上床的朋友是什麼朋友?”
單屹:“炮友。”
空氣突然安靜。
安干咳了聲,擺手:“我不是那種人,我潔自好來著,我不搞這家伙。”
話剛落安就頓了頓,該不會單屹想搞?
安看向他。
單屹無聲的目落在人的頭上有種虛無的微涼,明明千差萬別,但安卻一剎那想起那晚屏幕上年的那雙眼。
目清澈,帶著一年氣盛的,正氣凜然,是個鐵骨錚錚的男人。
這樣一個男人,上沾不得這些鄙俚低俗的詞。
安甚至在想,一夜恐怕是在他上烙下唯一的一個帶別樣的點。
突然,安一愣。
那張被忘掉的一百歐此時終于又浮了出來。
安頓時就開口:“那晚咱兩有個很深誤會!”
這個誤會讓過上兩個月非人的軍事化生活
猜你喜歡
-
完結491 章

深度淪陷
千方百計成功嫁給男神,她要牢牢抱緊這根金大腿,混吃混喝,順便狐假虎威。沒想到男神居然早有了白月光,想抱大腿,門都沒有!在狠狠抽了“白月光”后,她留下一紙離婚協議書,瀟灑離去。多年后,她重回家族,繼承億萬家產,還成了他死對頭的未婚妻。“我愛你,回到我身邊吧!”他堵住她的去路,深情表白。“愛我的人太多,你算老幾?”她笑靨如花,推開他,攜手其他男人離開!后來她才知道,他真正的白月光竟然就是她!
87.2萬字8 7615 -
完結3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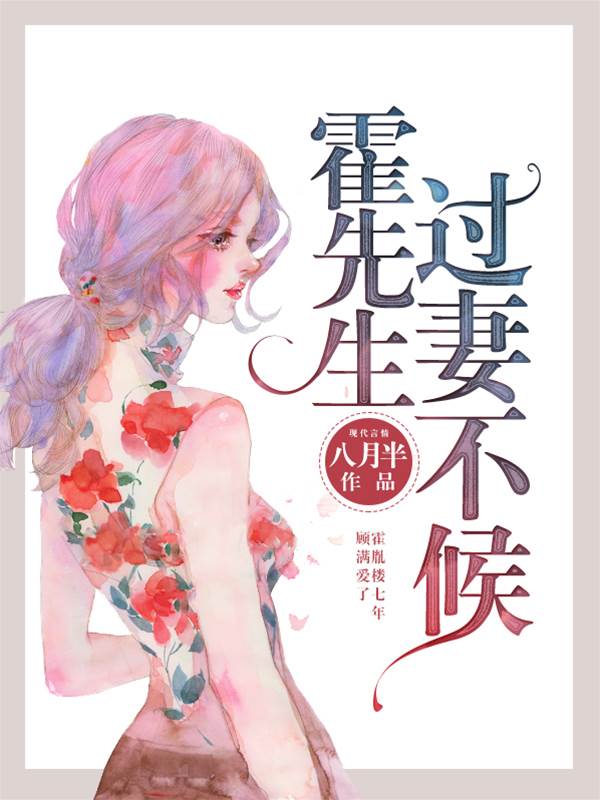
霍先生,過妻不候
顧滿愛了霍胤樓七年。 看著他從一無所有,成為霍氏總裁,又看著他,成為別的女人的未婚夫。 最後,換來了一把大火,將他們曾經的愛恨,燒的幹幹淨淨。 再見時,字字清晰的,是她說出的話,“那麽,霍總是不是應該叫我一聲,嫂子?”
29.6萬字8 88451 -
完結200 章
絕對偏寵
虞稚一反應遲鈍,是從小就容易被忽視的小孩,偏偏天資聰穎的時奕喜歡帶著她。 接她放學、等她回家,用自己的零花錢買最漂亮的小裙子送給她。 幼年的時奕:“如果你想當公主,我就去給你建一座城堡。” 少年的時奕:“我們一起去宇宙,我數星星,你笨就數月亮吧。”
29.9萬字8 8604 -
完結153 章

沉溺蝴蝶
【校園都市 | 男追女 | 久別重逢 破鏡重圓 | SC | HE】【清冷古典舞女神x京圈太子爺 】【冷顏係軟妹x瘋狗】八月,大一新生入校,一段舞蹈視頻迅速火遍了整個京大校園論壇——少女青絲如瀑,一襲白裙赤足立於地上,水袖舞動,曳曳飄飛,舞姿輕盈如蝴蝶蹁躚,美得不似真人。校花頭銜毫無意外落在了伏鳶頭上。但很快有人崩潰發帖:校花就一冰山美人,到底何方神聖才能入得了她眼?!大家不約而同用“樓聿”二字蓋樓。-樓聿,京大出了名的風雲人物,他生來耀眼,長得夠帥,又是頂級世家的豪門太子爺,無論在哪都是萬眾矚目的存在。但偏其性格冷恣淡漠,清心寡欲,因此又有人在帖下辯駁:冰與雪怎麼可能擦出火花?-後來無人不曉,兩人愛的轟烈注定要走到最後。然而誰都沒想到,大學還沒畢業伏鳶就提了分手。-多年後重逢看著女人平靜從他身邊走過,猶如不相識的陌生人,樓聿竭力抑製暴戾情緒。直到那句——“你認錯人了。”..聲音刺耳直穿心髒男人偽裝多年的平靜瞬間分崩離析,他猛地將女人抵在牆上,顫聲問:“伏鳶。”“耍我好玩嗎?”—#回到我身邊#於清醒中沉淪#理智不會永遠占上風,但你會
26.5萬字8 331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