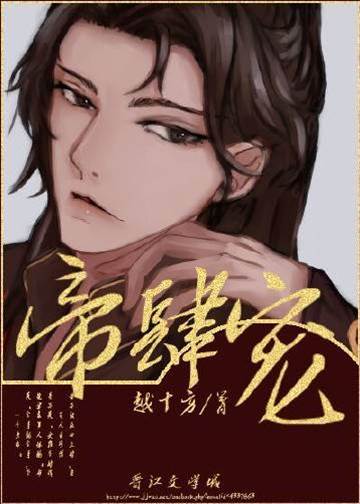《金屋藏嬌》 第67章 給我明日就滾回小院
慕氏用這藥是要他的命?還是只為了嫁給他的手段?
這藥會長期對耶律肅使用麼?
夏寧垂眸細思。
耶律肅待自己還算大方,雖然沒罰,但也庇護三年有余,自己是否要稍加提醒那香囊有問題?
發現香囊有問題的那會兒沒開口說,便已錯過了當時最好的時機,最后再提及,恐怕于他看來太過刻意。
若再生出些事端,還能不能回小院去了?
罷了罷了。
那慕氏是耶律肅未來的將軍夫人,明正娶的大娘子。
一個外室,份卑微不說,此時提及,算怎麼回事。
且中毒需經年累月用著。
到那時候還不知道在哪兒呆著呢。
還是心些心罷。
了了這樁心事,忽覺困乏,長長打了個哈欠回去困覺。
這一夜睡得極好。
起來時神清氣爽,腦袋的疼痛也退了許多。
睡了一夜,屋子里愈發冷了。
小貓不知什麼時候跳上了床,蜷著子在腳邊呼呼睡著。
聽見起來的靜后,兩只小白耳抖了抖,張開眼睛,出金黃的眼瞳,隨即聲氣地沖喵嗚了聲。
的夏寧心都融化了。
“看在你這麼可的份上,就原諒你爬我的床,過來罷。”夏寧拍了拍被面,小貓跑過來,4肢靈活,鉆進了的臂彎里。
親昵的蹭的胳膊。
夏寧與它玩了會兒才穿起床。
里面有了靜,雪音也端著熱水進來伺候洗漱。
漱口凈面后,坐在梳妝鏡前,隨手綰了個發髻,又把銀釵上,再無其他飾品,比雪音的裝扮還要素。
若非那張嫵艷麗的面龐,看著就像是為得寵的妾。
否則真會教人誤認是個丫鬟。
Advertisement
打扮妥當后,推開窗戶,想讓屋子里敞亮些,好繼續做手爐套子。
一推開窗子,外面銀裝素裹,滿目雪白。
屋檐存雪,地上積雪,就是連欄桿上,也攢了厚厚一層的皚皚白雪。
撲面涌來的空氣清冷漉,深呼吸一口氣,冷氣灌肺腑,通涼意,但卻舒暢。
的小院積雪后也甚。
但比不過將軍府。
顯赫貴氣。
大約是起來了,院子里進來了兩三個下人開始掃雪,掃把拉著白雪,從地上劃過,發出刺啦—刺啦—的聲音。
小貓還窩在床腳睡回籠覺。
聽見掃雪的聲音,來了興趣。
呲溜著跑到夏寧的腳邊,兩只前爪抱著的大,閃爍著眼睛,喵喵。
夏寧一把將它撈起。
第一次見到這麼厚積雪的小貓的更喚了。
夏寧笑土包子,一邊又雪音,裝一盆雪進來。
雪音裝了滿滿一銅盆,堆小山似的端進來。
小東西圍繞著銅盆里的雪堆,慢慢靠近,又被凍的哆嗦。
出爪子了下,寒得它抖了抖子,立馬收回來,手著自己被凍到的小爪子。
那委屈又無辜的模樣,逗得夏寧哈哈笑。
夏寧心來,抓了一把白雪攥在手里,了一條小黃魚的模樣,隨后放在小貓跟前。
這下小東西的眼睛都直了。
先是喵嗚了些,有些懷疑與味道。
但看著樣子就是它吃的小黃魚,它仍是嗷嗚著張開咬了上去,結果凍的刺痛,立馬后跳三步遠,渾發豎起,喵的一聲得犀利。
完后,發現‘小黃魚’開始融化,它又急的繞著團團轉。
小眼睛里都是焦急,不停的用手把化開的水往回推。
還用爪子扯著夏寧的擺,讓看。
Advertisement
屋子里都是小貓可憐兮兮的喵聲,還有夏寧的笑聲。
捧腹大笑。
傳的整個前院都能聽見一兩聲。
離得不遠的書房里自然也聽見了,且聽得格外清晰。
耶律肅聽著夏氏4無忌憚的笑聲,掀起眼瞼往窗外看了眼,看見雪音又端了一盆雪進屋去。
冷哼了聲,這夏氏過得倒是舒坦。
昨兒個還嫌他上寒氣人,今日玩起雪來倒是不怕。
心中雖為不滿,但清冷的面龐上眉眼卻也舒展了。
偶爾聽之,雖然呱噪,但也能讓前院有些生氣。
他收回視線,目再一次落在手邊厚厚一疊的書信上。
是副將傅安寄來的私人信件,走的暗衛營的路子快馬加鞭送到他手上。
換防軍一行已達南延與西疆的邊境,抵達后邊境西疆突襲一次,但此次突襲為佯攻,驚人后就撤,南延軍并無死亡,只一人傷。
傷者就是此次換防軍的主帥——兵部尚書的嫡長子蕭齊風。
他出發時上傷尚未痊愈,再加上前往邊境日夜趕路,舊傷遲遲不見好,再加上疲勞所致,遇襲應急時不慎墜馬,還被馬給踩了一蹄子——
看到這兒,信件已至結尾。
耶律肅恨鐵不鋼的罵了句蠢貨。
就因他被馬踩斷了大骨,換防軍需在邊境多停留一個月才能回京復命。
這消息,大概明日早朝之前,就能遞到淵帝與兵部尚書跟前。
到時朝廷上又要一片混。
耶律肅取了紙,提筆正要回信時,夏氏的笑聲戛然而止。
停地倉促。
他皺了下眉,來何青,命他去看看。
正室里,謝安背著藥箱,緩緩踱步進來了。
夏寧又了許多小哄小貓玩,連雪音看著也甚是新鮮,對出來外形形象可的小很是喜歡。
Advertisement
正笑的歡樂時,聽見腳步聲從院子里走來。
探頭,在敞開的窗子里就瞧見了謝安。
笑聲瞬止。
臉苦悶。
變臉之快,惹得雪音忍不住要笑出來。
人見著自己這一副苦兮兮的臉,之前換藥就是再疼也不見哼唧一聲,現在這般可憐,謝安這老大夫也忍不住安道:“今日換藥不會像前兩次那麼疼的,姑娘莫怕。”
倒不是夏寧真的怕疼。
是方才玩得太快樂,冷不丁府醫出現,提醒遭何事,頓時就有些不快樂。
收起苦悶,淺笑著道:“勞煩謝先生了。”
謝安客氣了一聲,開始換藥。
這一回手腳更為迅速。
夏寧都沒覺到什麼痛就換完了。
想來是用了好藥。
雪音端水來,伺候謝安凈手。
凈完手后,謝安不急著離開,詢問道:“姑娘額上的傷口開始愈合長新,用的雖是上好的生止膏,但傷口較大,怕會留疤。姑娘殘留的香料過了這麼些日子已然排干凈,是否愿意繼續用那藥,方能確保不留疤痕。”
夏寧口而出:奴家怕死,一條疤痕保一條命,這買賣劃算的很。
謝安被拒絕了個猝不及防。
他都以為這夏姑娘會立刻答應。
萬萬沒想到會拒絕的如此直白。
畢竟事關子容貌,他看了眼雪音,見也微微搖頭,便知道做不了這夏姑娘的主,他只得再說多兩句。
一再保證再無那害人的香料,但夏寧仍是不松口。
謝恩也不再堅持,出了正室,就往書房去報告。
將夏氏不愿意用藥之事轉達。
表明若是將來留疤可不管他的事,自己磨破了皮子,也是將軍您那外室不肯用藥的。
Advertisement
男主看著站在跟前謝恩,劍眉皺起:“除了東羅的藥,你就沒其他藥方能祛疤的?”
謝安折腰,恭敬仔細的回稟:“夏姑娘額上不單是裂開,而是連皮帶破了一個大口子,除了東羅的生藥,沒有一個藥方能確保傷口生無痕。”
謝安上是有幾分本事的。
不然耶律肅也不會留他在府中當府醫。
但這人雖為大夫,卻更通毒醫之道。
他既然提出要再次用藥,把握定有九。
可那夏氏——
耶律肅眼底劃過一抹暗。
兩日之約就要到了。
耶律肅眉頭皺,將手中的筆桿重重擱下,起朝外走去,口中卻與府醫道:“為外室不惜容貌,不信府醫、任妄為,看來是我這些日子顧忌有傷在,才縱容如此放4!”
語氣已然帶著怒意。
在院子里掃雪的下人見他怒,慌忙下跪。
連大氣都不敢出一聲。
直至耶律肅攜著一怒氣,進了正室。
下人間互相低語,都在說,怕是這夏姑娘的恩寵要到頭了,惹得將軍生了這麼大的怒氣。
推門進屋時,夏寧已然聽見了靜。
彼時,正在教雪音繡帕子。
兩人湊在一起,白絨絨的小貓蹲在腳邊,屋子里暖烘烘的。
看著一派安逸舒適。
而他的暗衛之一,卻認真的連他進屋都沒發現。
直到開了門,才驚醒似的站起來行禮見安。
看的耶律肅臉更添了一分寒意。
一個暗衛,學著繡花織布忘了本事,留著還有什麼用。
他步走到屏風后,眼風帶過雪音,聲音冷似寒冰:“雪音,別忘了你的份。”
雪音臉霎時慘白。
攥著的手收,說了句‘將軍恕罪’后,匆匆退下。
夏寧對子一向偏心。
看著雪音放在桌上,繡的歪歪扭扭卻每一針都極為認真的花樣,想起心氣歡喜的眼神,又想起剛才蒼白著臉離開的模樣。
知雪音份特殊,并非普通侍。
但心中不免憋悶,手將雪音繡的花樣翻了過去。
作里加了些不耐煩的態度。
皆被耶律肅看眼中。
且自他進屋后,這夏氏到現在還不起,向他行禮問安,甚至連規矩都疏懶至此!
耶律肅皺著眉,著怒氣責問:“夏氏,你這是什麼態度!”
他了怒氣,夏寧說跪就跪,姿態放的極低,無辜道:“奴不知做錯了什麼,才惹得大人生這麼大氣……”
又是那副故作的腔調。
一揮之不去的勾欄瓦舍做派!
耶律肅最是厭這些。
此時心中帶了怒氣,更是看不順眼,上前一步,糲的手指直接住的下顎,用力將的臉抬起,垂下的視線犀利:“你會不知?我看你是心里清楚,仗著我縱容你幾分,徹底忘了自己的份!”
隨著他說每一個字,夏寧臉的惶恐之意就添一分。
杏眸含淚,囁嚅。
著嗓音道:“奴時刻不敢忘了自己是何——”
耶律肅甩開的臉,一臉厭惡:“收起你這些秦樓楚館里學來的下作手段!”
夏寧被摔得子歪倒在地上,垂淚哭訴,萬般可憐:“奴真不知做了什麼惹得大人如此怒啊……”
連哭音都是招人心疼的無辜。
耶律肅再一次近,卻未抬起的臉,只用手指過額角的傷,微微用力,夏寧疼的嘶了一聲。
才明白過來。
他竟是為這這事生這麼大的氣。
不等夏寧深思,聽見耶律肅用著嘲諷、厭惡的語氣說道:“你以為仗著有一分寵,我就會容忍你殘缺不全?”QQ閲讀蛧
夏寧哭著解釋:“奴怕……上一回就險些要了奴家的命,這一次便是有謝先生說了,可奴——”
耶律肅再一次打斷,語氣更添了不耐煩:“看來是我收留你在府中養傷,反而讓你生了野心!給我明日就滾回小院,待你想清楚再來與我請罪!”
這會兒,夏寧早就顧不上不和諧之意。
滿腦子都是能回小院了。
哭的噎,抱著他的大苦苦哀求:“大人……”
心卻歡喜的雀躍。
愈發纏他,耶律肅就愈發惱。
最后撥開的手,甩袖子離去。
夏寧演戲演足,從地上爬將起來,坐到床邊,哭哭啼啼的收拾包裹,恨不得立刻就回小院去。
在小院里,好歹能做幾日自己。
在將軍府里呆著,被關在一間屋子里,外面到都是耶律肅的眼線。
束縛著自己,盡職盡責扮演‘外室夏氏’,也有些厭煩,想要一口氣。
雪音聽見了下人議論的靜后,急忙回了正室,看見夏寧坐在床邊垂淚,手邊是一個收拾妥當的包袱,哭的子都在聳。
抬頭看見雪音進來后,哭的紅腫的眼睛里又涌出兩道眼淚來。
咬著下,哭的無端惹人心疼。
雪音跟了這幾日,對頗有幾分好。
見人哭的這麼傷心,忍不住上前安道:“姑娘快別哭了,你整日著屋子里,回去后就不冷了。”
夏寧:……真是個實心的姑娘。
夏寧用帕子干眼淚,手去抓的雙手,哭的連聲音都沙啞了,“這些日子多謝雪音姑娘照顧……我曉得……這將軍府里人人瞧不起我這外室……只有你待我這般好……可我一清貧,沒什麼能送得了你……”
嗓音低啞,杏眸浮著淚,眼神真摯。
似是極為不舍。
猜你喜歡
-
連載3575 章

錦鯉棄婦:隨身空間養萌娃
一覺醒來,安玖月穿成了帶著兩個拖油瓶的山野棄婦,頭上摔出個血窟窿。米袋裡只剩一把米;每天靠挖野菜裹腹;孩子餓得皮包骨頭;這還不算,竟還有極品惡婦騙她賣兒子,不賣就要上手搶!安玖月深吸一口氣,伸出魔爪,暴揍一頓丟出門,再來砍刀侍候!沒米沒菜也不怕,咱有空間在手,糧食還不只需勾勾手?且看她一手空間學識無限,一手醫毒功夫不減,掙錢養娃兩不誤!至於那個某某前夫……某王爺邪痞一笑:愛妃且息怒,咱可不是前夫,是『錢』夫。
322.4萬字8.08 312722 -
完結8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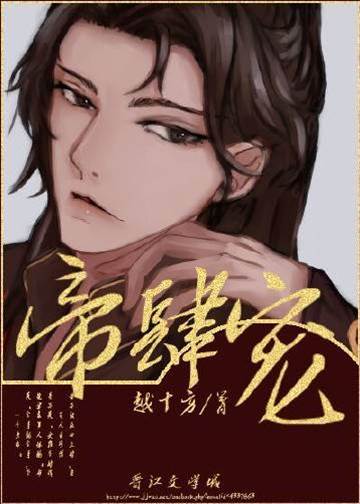
帝肆寵(臣妻)
從軍六年渺無音訊的夫君霍岐突然回來了,還從無名小卒一躍成為戰功赫赫的開國將軍。姜肆以為自己終于苦盡甘來,帶著孩子隨他入京。到了京城才知道,將軍府上已有一位將軍夫人。將軍夫人溫良淑婉,戰場上救了霍岐一命,還是當今尚書府的千金,與現在的霍岐正當…
28.8萬字8 26468 -
完結451 章

歡恬喜嫁
前麵七世,徐玉見都走了同一條路。這一次,她想試試另一條路。活了七世,成了七次親,卻從來沒洞過房的徐玉見又重生了!後來,她怎麼都沒想明白,難道她這八世為人,就是為了遇到這麼一個二痞子?這是一個嫁不到對的人,一言不合就重生的故事。
81.3萬字8 15673 -
完結532 章
醫庶無雙
原主唐夢是相爺府中最不受待見的庶女,即便是嫁了個王爺也難逃守活寡的生活,這一輩子唐夢註定是個被隨意捨棄的棋子,哪有人會在意她的生死冷暖。 可這幅身體里忽然注入了一個新的靈魂……一切怎麼大變樣了?相爺求女? 王爺追妻?就連陰狠的大娘都......乖乖跪了?這事兒有貓膩!
103.5萬字8 19340 -
完結206 章

賠罪
施綿九歲那年,小疊池來了個桀驁不馴的少年,第一次碰面就把她的救命藥打翻了。 爲了賠罪,少年成了施綿的跟班,做牛做馬。 一賠六年,兩人成了親。 施綿在小疊池養病到十六歲,時值宮中皇子選妃,被接回了家。 中秋宮宴,施綿跟在最後面,低着頭努力做個最不起眼的姑娘,可偏偏有人朝她撞了過來,扯掉了她腰間的白玉銀環禁步。 祖母面色大變,推着她跪下賠禮。 施綿踉蹌了一下,被人扶住,頭頂有人道:“你這小姑娘,怎麼弱不禁風的?” 施綿愕然,這聲音,怎麼這樣像那個與她拜堂第二日就不見蹤影的夫婿?
33.9萬字8.18 406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