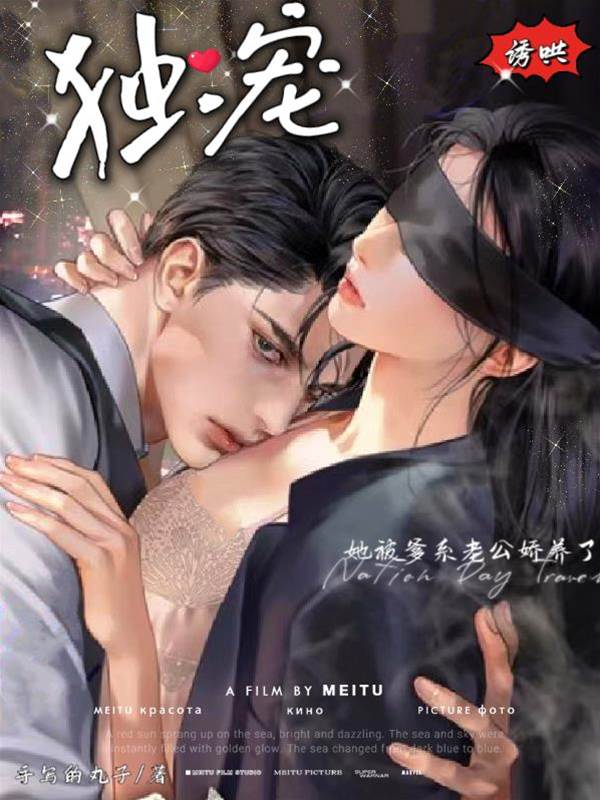《誘餌》 第90章 一直停留這一刻
黃章的書取了文件返回包廂,沈楨推搡他,“坐好。”
陳淵不笑出聲,直脊背。
書打開,“按照長齊5%富誠7%的利潤比,擬定的合同。”
黃章確認后,簽了字,到陳淵手邊,“陳總,以后我去富誠的地盤,您可要關照我。”
“一定。”他含笑了一眼沈楨,“承諾了,我絕不食言。”
黃章意味深長,“陳總很重小沈啊。”
陳淵重新審閱一遍,簽名,雙方互敬了一杯酒,“合作愉快。”
他旋即撂下酒杯,“我有耳聞,陳總要娶萬董的獨生,萬嬉皮?”
陳淵靜默一秒,“萬喜喜。”
“嘻嘻,很呱噪。”黃章掃過沈楨,“我聽凱悅的老總說,你也離婚了。”
吐出蝦殼,“離了。”
“前夫進監獄了。”
“黃總。”沈楨詫異,“您消息靈通啊。”
“我有一個表侄,哈佛畢業,開了一家律師事務所。”黃章笑得眉飛舞,“見一面嗎。”
陳淵面容略沉,兀自飲酒。
似乎看出沈楨的顧慮,“他不介意,歐民風開放,離過婚怕什麼。”
“我...”
“黃總,時候不早了。”陳淵起,“工程落實后,我們再聊。”
黃章也站起,“好。”越過他,提醒沈楨,“有想法聯系我,我表侄和我眼相似,我滿意的人,他基本滿意。”
陳淵拿起桌上的車鑰匙,離去。
沈楨立馬跟上,進電梯,門一關,他沒頭沒尾開口,“見嗎。”
“見誰?”
他凝視門壁的投影,“黃總的侄子。”
“門當戶對嗎?”反問。
陳淵發笑,“男人了,所有預設的條件和底線會改變。”
沈楨不吭聲。
明白,黃章是瞧出不對勁,拉一把,名利漩渦,男人最了解男人。
Advertisement
沒背景的人,膩了,肆無忌憚踹開,再不,落到正室手里,更沒好下場。
陳淵也明白黃章的弦外之音,氣氛才急轉直下僵住。
走出酒樓大堂,外面茫白一片,沈楨回頭,一臉興,“下雪了!”
陳淵解了大扣,從后面裹住,“沒見過雪嗎。”
“這是今年第一場大雪。”沖下臺階,又被陳淵拽住,一顆顆系好紐扣,“著涼。”
雪清幽,像一只熱烈火紅的小狐貍,徘徊在霧蒙蒙的長街,城市灰暗衰敗,唯獨,這樣氣,明。
“你喜歡雪?”
地上積了一層薄薄的白霜,沈楨蹦跳著踩過,“我告訴你了呀,雪干凈。”
陳淵長,步伐大,饒是刻意放緩,也超出許多,他停在路燈下,等。
“后半夜,雪積厚了,可以打雪仗。”
他悶笑,“你不困?”
“每年第一場雪,小區里的孩子都鬧一宿——”沈楨只顧講話,沒留意腳底,猛地一摔,陳淵扶,卻仰著姿勢倒下,摔得狼狽要命。
他彎腰抱起,“痛嗎?”
點頭,嘲弄他,“你胳膊那麼長,竟然沒扶。”
“不扶。”陳淵清理后背的水漬,“痛了長記,下次知道老實走。”
巷子口,漫開稀疏昏黃的,鋪天蓋地的初雪,熙熙攘攘在盡頭飛揚。
飄落他肩上,短發間。
沈楨手拂了拂,“你了。”
“你也了。”
四目相視,一愣。
陳淵率先移開,握拳抵,“你頭頂了。”
“你服了。”不自在,攪著擺。
雪刮得更大,席間都喝了酒,沈楨買完最后一班車票,雇代駕去高鐵站。
陳淵一手兜,一手點煙,“幾點。”
Advertisement
“10點07。”
他看腕表,“來得及嗎。”
“應該能趕上。”
他垂眸吸煙,掏手機,索許久,屏幕陷漆黑,陳淵看向,“沒電了。”
“我有。”沈楨在網上約了同城代駕,對方打來電話,詢問在哪。
不悉環境,遞給他,“長橋路。”
那人不知說什麼,陳淵回了一句不必,便掛斷,“不接單。”
一連雇三個代駕,全拒了。
沈楨轉手機,“長江大橋距離車站半小時的路程而已。”
陳淵把大給了,穿著西裝襯,與此刻的寒冷格格不,他著手,角攏著一團白汽,“地面結冰,容易出事故。”
“雪融了,哪結冰啊。”沈楨踢了踢路邊的樹樁,“那我回不去了嗎。”
陳淵抿,“要不,留宿一晚,明早我送你。”
踏著雪地的影子,四周空曠,沒有一輛出租,偶爾疾馳,也不載客。
沈楨沉默,他也沉默。
越往南,樓廈越開闊,霓虹迷離,風雪相纏,陳淵始終在前面,擋住風口。
他上的煙酒氣混合著似有若無的男香,不斷向后吹,蕭瑟狂中,鼻息間盡是他的味道。
抵達酒店,已經深夜。
沈楨的房間和他同層,位于11樓一南一北。
刷房卡時,突然喊住陳淵,“陳總。”
他駐足,側過,“怎麼。”
“代駕接單了,你故意不答應。”
陳淵怔住。
“馬路那樣安靜,我聽得清。而且——”晃了晃手機,“你無理由取消三單,記錄會顯示。”
沈楨破后,進屋,反鎖門。
好半晌,陳淵在原地笑了一聲,“那你為什麼不離開。”
隔著一扇門,沒聲響。
他回到自己房間,啟開一瓶尾酒,走向落地窗,俯瞰雪中燈火。
Advertisement
轉天早晨,陳淵在房外敲門,兩三下沒回應,便止住。
片刻,沈楨收到短信。
——我在工地,你想走,可以走,不走,傍晚我回去。
已讀,刪除。
這男人,把控分寸的功力,厲害到極致。
其實昨晚沒睡,熬到幾乎天亮。
以為陳淵會過來,倒不是等他,出于上下級,或者私人關系,他來,總要接待。
好在,都沒醉,不會像那幾回一樣,難以控制逾越。
但陳淵沒出現。
換另一個男人,必然千方百計登門獨。
這種行為,在人的心里,也徹底擊潰了好。
男人也清楚,可僥幸,不肯錯過良機。
若非絕頂高手,懂得在場上先抑后揚,絕對營造不出這種進不進、而不的氛圍。
臨近中午,沈楨去了一趟工地。
在烏泱泱的工人堆里,一眼看到陳淵。
他個子最高,氣度也好,戴了一頂黃頭盔,亞麻灰的厚外套,很普通的棉布,毫無質版型。
偏偏如此平庸簡約的款式,襯得他英武,筆,結實。
暴在中的每一寸棱角、皮與筋骨,釋放最純正剛烈的男人味。
塵土,砂礫,生銹的鋼架,這里的一切糙至極。
大約燥熱,陳淵掉外套,綁在腰間,只一件單薄的打底衫,箍住他軀,流暢堅的壑起伏,壁壘叢生,一強勁的力量從他鼓脹的膛蔓延至腹部。
靈與的邊緣,執著的沖擊力,這些并無關聯的,占據他整個人。
工頭發現陳淵,嚇得變了臉,“陳總!”當即搶過他手中的鋼筋板,“您金貴,這不是您干的活!”
“我不是陳總了。”陳淵笑容溫雅,“和你們同樣的份,做基層。”
Advertisement
工頭不敢撒手,“您不是陳總,那也是陳董的大公子啊,總部安排您監工,萬一砸傷了,我沒法待。”
陳淵挽起袖子,去土壩上,“沒必要搞特殊化,傷我自己解決。”
沈楨下車,邁過施工線,靠近地基中央,二樓在鉆孔澆筑鐵架,周圍火花四濺。
陳淵蹲下搬工時,目無意掠過背后,他緩緩直起,雪刺目,眼睛亦是無邊無際的灼白,“你沒走。”
沙啞,意外。
拎著餐盒過去,“吃飯了嗎?我借酒店餐廳的廚房燒了菜,油鹽,很清淡。”
角落掛著破舊的工服,他蹭掉手上的土,接過保溫袋,帶去帳篷里,“何必麻煩。”
“你這麼落魄,再吃不飽。”沈楨沒繼續說。
陳淵笑聲愈發大,逗逗得上癮了,“你今天照顧我,那明天呢?我照樣吃苦頭。”
坐在一塊青石板上,“我讓安書來。”
“我沒有職務了。”他捧著飯盒,也坐下,“沒資格用。”
晃悠著雙腳,向對面車水馬龍的街道,“我記得初次遇見你,在市人民醫院,你的襯衫扣割了我額頭。”開劉海,“留疤了,不過很小。”
沈楨緒低落,“現在是人非,你淪落當工頭,還是副的,我上學當過副班長,除非正班長請假,否則純粹是擺設,哪個工地的工頭會請假啊,你本就是工人。”
陳淵忽然有些不忍心,當真可憐他這副樣子。
遠的廢墟這時開始破,震耳聾的悶響,黃沙噴發的剎那,嗅到無數氣息,翻騰在空氣里,陳淵的汗明而滾燙,散發濃重的味,不清冽,更不難聞,沿著他短利的發茬一滴滴淌落,匯聚一縷水痕,沒脖頸。
恍惚中,陳淵在說話,被炸得斷斷續續,沈楨沒聽完整,“你希什麼?”
他湊到耳畔,“希一直停留這一刻。”
線照在陳淵的眼尾,那是尤為的皺紋,弧度淺,韻味卻而深刻。
***
老宅那邊,張理在書房向陳政匯報況,陳崇州在一旁默不作聲。
“大公子不擺排場,深工地,和工人們同吃同工。”
“同工?”
張理說,“推土車,扛沙袋,什麼都干。”
陳政蹙眉,“安全為重,他又沒干過那些。罰他流放,例行巡視就行。”
張理笑,“大公子正直,這點也像您。”
陳崇州不疾不徐整理領帶,試探問,“大哥態度良好,父親是否召回他。”
陳政沒立刻答復,隨手翻閱報表,“資金缺口大,有法子填補嗎?”
“大哥放出的款,現階段十有八九收不回,其他公司欠晟和的款,大哥也同意延期了。”他清明的眉目浮出幾分犀利,“父親知嗎。”
陳政依然避而不答,“再拖下去,對公司不利。你如果實在為難,我調你大哥回公司,自己收拾爛攤子。”
“我沒意見。”陳崇州筆直立在那,“只要您說服母親,原諒大哥的過失,我隨時讓位。”
陳政瞇起眼,“你母親那頭,心不錯。”
“洗清冤屈,心自然好。”陳崇州語氣耐人尋味,“可大哥剛調去外地,貿然召回,如同走過場,母親的月份大了,憂思多慮,安危無法保證。”
“也罷。”陳政合住文件,“富誠的賬戶有幾億余款,你先拿去救急。”
“我在急籌資,不準備挪用總部的錢,大哥造的窟窿,我盡量填。”
陳政倚著靠背,打量他。
業,早有傳言,陳家的二公子是全才。
談不上通,各行掌握一點皮。
金融,風投,算,醫學,戲劇,據說在武館,也學點功夫,陳政雖然寵二房,事實上,大多是寵何佩瑜,待這小兒子,一般。
越有錢有勢,謀利寡,越淡薄。
對于傳言,他沒擱心上。
畢竟陳淵的資質,足夠挑大梁。
經過接二連三的風波,陳政意識到,陳崇州比陳淵手黑,也。
他有膽量算計任何人,在老狐貍的眼皮底下耍,即使墻倒眾人推的關頭,也波瀾不驚,相當沉得住氣。
商場如戰場,詭計層出不窮,陳淵的城府再深,再毒辣,謀略手段太正。
擺在臺面上的正經玩法,與同僚斗起來,能清他的底,五五勝負率。
陳崇州是野招,上不得臺面,卻防不勝防,同行琢磨不他,博弈到白熱化,能保六勝算。
可惜,心不正。
陳政拾起一雪茄,斜叼住,“你有門道,哪來的錢。”
陳崇州表面謙遜,實則暗藏玄機,“比不了大哥的手腕高明,論經商,您尚且不是他對手,何況我。”
“陳翎馬上升正局級了,在考核的關鍵期,生意財路上,你務必謹慎些。”陳政叩擊著桌面,“何鵬坤對親事不太熱了,也許顧忌你母親和喜喜的過節,不愿同萬家為敵。萬宥良對陳家有怨氣,你平時注意他,你大哥管理晟和,他不手,到你這,他大概率會刁難。”
說完,又問,“你跟那姓沈的呢。”
陳崇州沒應聲。
【作者有話說】
謝+1+1??打賞牛氣沖天、妙筆生花和金幣,破費了
謝以馬利打賞催更符和金幣、lemon陳崇州的人打賞催更符,SweetTea打賞鮮花、向車前進打賞新春紅包
謝書友54991、林深時見鹿、min、小倩、ioumylovery、我想屬魚、深夏私季、藍桉、陳佳雪、念想.打賞金幣
謝大家投票支持~
猜你喜歡
-
完結555 章

破案大佬線上追妻
五年一別,前男友竟搖身一變成為了自己的同事。桑雨萌:???桑雨萌安慰自己,工作就工作,咱不談感情。於是,在見到前男友的時候,桑雨萌麵不改色,一臉淡然。但……誰能告訴她,一向孤高冷傲的前男友,怎麼變得如此粘人奶狗?***後來,桑雨萌漸漸發現,不管自己置身何處,身邊都會有個叫厲瀚璟的男人。本想縮起頭來做烏龜,卻不想他變本加厲,根本不允許她逃脫。後來,娛樂圈當紅小花的戀情被曝,全網一片嘩然。曝光的視訊中,女人吃完零食,舉著一雙柔荑,委屈巴巴:「手髒了。」
76.5萬字8 8193 -
完結1451 章
席少的嬌妻又颯又甜
她被迫代妹出嫁,成為席家二少的新婚妻子。怎料婚禮當天,對方直接缺席,留她一人獨守空房,婚後更是風流成性,夜不歸宿。就在她以為人生就要這樣死水一潭的時候,一個英俊冷傲的男人意外闖入她的生活。男人脾氣惡劣林淺席璟小說*:
246.4萬字8 17187 -
完結809 章

替嫁傻妻:厲少寵爆全球
蘇甯暖,蘇家隱形大小姐,智商只有5歲的小傻子!傻乎乎滴代替妹妹嫁給了厲家二少爺——個醜陋,殘廢,還暴虐成性的短命鬼。 小傻子配短命鬼,絕配! 可是,這傻子少夫人怎麽畫風怎麽不對? 氣翻心機繼母,碾壓綠茶妹妹,巧削惡毒傭人,狂扁腹黑反派! 反派們壹個個痛心疾首:說扮豬吃老虎那是侮辱了蘇甯暖,她是壹個小傻子攆著壹圈反派大佬無處可逃! 厲景沈壹把把小嬌妻擁入懷中:我慣的,怎麽了?
145.3萬字8.18 226708 -
完結87 章

明天去看雪好嗎
新婚不久,朋友們來暖房。有人喝多了,問新郎:“喜歡一個人喜歡了那麼久,就這麼放棄了,甘心嗎?”正要進門的顧南嘉呼吸一滯。門縫裡,孟寒舟慵懶浸在月光之下,俊朗的半張臉風輕雲淡,半晌沒應聲。顧南嘉心寒,回想在一起的諸多細節,通通都是她主動。他從來都只是一個字:“好。”溫柔的背後竟是隱情。顧南嘉學不會矯情,瀟灑轉身。算了,人先到手,來日方長。-結婚幾個月後,某一天,孟寒舟忘記了她大姨媽時間。顧南嘉默默掉眼淚:“你果真愛的不是我。”她把準備好的離婚協議推到他面前。孟寒舟放下手中的杯子:“想清楚了嗎,小哭包。”小哭包?“除了昨天,我還有什麼時候哭過?”顧南嘉跳腳。某人溫柔地撕掉離婚協議:“暖房酒那天。”朋友醉話而已,他根本不走心。她卻站在門口哭了。於是他認真回答:“沒放棄,就是南嘉。”可惜她轉身了,沒聽到。
12.1萬字8 14097 -
連載1021 章
誘她情深
【雙c×始于欲望×先婚后愛×追妻火葬場×土狗愛看專場】【情緒穩定溫柔克制女航醫×前期傲嬌狗后期瘋狗男機長】沈瑤初和高禹川的開始就是一個錯誤。他只是喜歡她的身,她卻妄想得到他的心。因為意外來的孩子,他把她娶回了家,把一個小錯誤變成了大錯誤。在這段婚姻里,她失去了一切,最后離開的時候,甚至沒有一個像樣的告別。**高禹川一直覺得,沈瑤初聽話不麻煩,呼之則來揮之則去。他以為,只要他不準,她這輩子都不可能離開他。直到她真的走了,走得那麼徹底,讓他用盡辦法都找不到。**多年后,兩人重遇。她正言笑晏晏與人相親。別人問她:“你的第一段婚姻是為什麼結束呢?”她回答:“喪偶。”等了許久,他終于忍不住將人堵了,抵在墻上:“沈瑤初,你真當我死了?”
187.3萬字8.18 109148 -
完結9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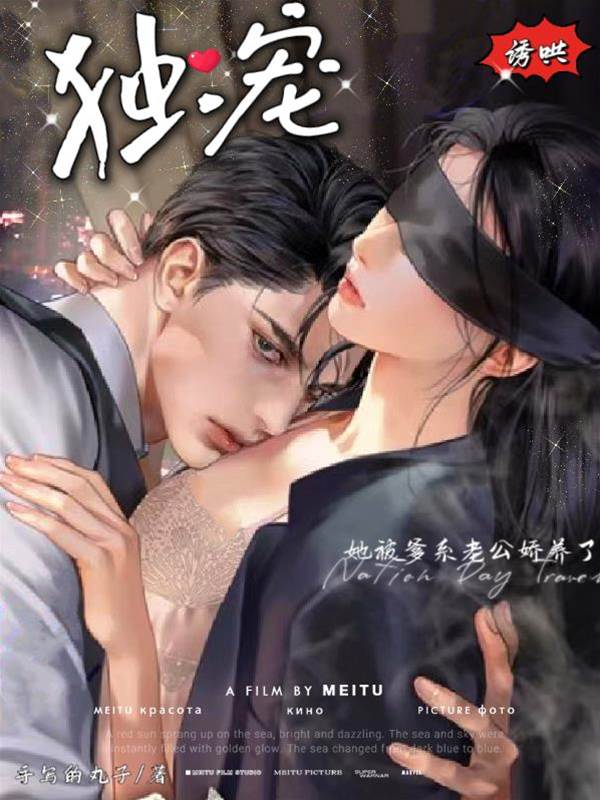
獨寵!誘哄!她被爹係老公嬌養了
1v1雙潔,步步為營的大灰狼爹係老公vs清純乖軟小嬌妻 段硯行惦記那個被他撿回來的小可憐整整十年,他處心積慮,步步為營,設下圈套,善於偽裝人前他是道上陰狠殘暴,千呼萬喚的“段爺”人後他卻是小姑娘隨叫隨到的爹係老公。被揭穿前,他們的日常是——“寶寶,我在。”“乖,一切交給老公。”“寶寶…別哭了,你不願意,老公不會勉強的,好不好。”“乖,一切以寶寶為主。”而實際隱藏在這層麵具下的背後——是男人的隱忍和克製直到本性暴露的那天——“昨晚是誰家小姑娘躲在我懷裏哭著求饒的?嗯?”男人步步逼近,把她摁在角落裏。少女眼眶紅通通的瞪著他:“你…你無恥!你欺騙我。”“寶貝,這怎麼能是騙呢,這明明是勾引…而且是寶貝自己上的勾。”少女氣惱又羞憤:“我,我才沒有!你休想在誘騙我。”“嘖,需要我幫寶寶回憶一下嗎?”說完男人俯首靠在少女的耳邊:“比如……”“嗚嗚嗚嗚……你,你別說了……”再後來——她逃他追,她插翅難飛“老婆…還不想承認嗎?你愛上我了。”“嗚嗚嗚…你、流氓!無恥!大灰狼!”“恩,做你的大灰狼老公,我很樂意。
15.9萬字8 1117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