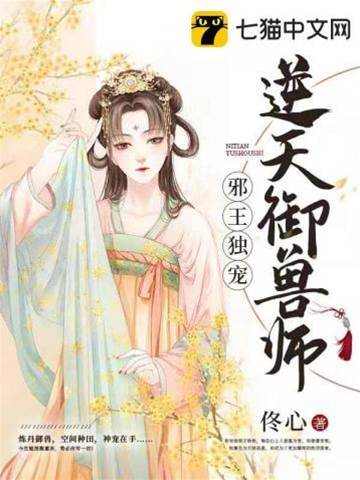《謫仙》 第150章 幕后
門外站著一個披著黑斗篷的人,他低著頭,聲音從面后傳出來沙沙作響,仿佛某種砂礫:“人解決了嗎?”
“絕對死了。”李貞點頭,“我親眼看著他將一杯酒喝下去,之后特意等了許久,他完全沒有呼吸了。”
“那就好。”黑人拿出一個紙疊的花轎,吹了一口氣,那張紙漸漸變大,最后竟了一個真正的轎子。李貞驚訝地瞪大眼睛,撒豆兵,點石金,這就是兄長所說的仙家手段?
黑人讓開一步,對著李貞比了比花轎。李貞不可思議地指了下自己:“我?”
“是。”黑人說,“義安公主放心登轎,之后這頂轎子自會送你到吳王邊。”
李貞接到了李許的書信,現在又親眼看到了黑人的神通,當下再無懷疑,提著子登轎。是公主,就算被囚于宮中,不待見,那也終究是皇,從來不用自己走路、自己洗臉。習慣了用轎子代步,但是這次上轎前,形頓了頓。
突然想起病床前扶著自己喝藥的男人,他高大沉默,舉止鄙,但對確實盡心盡力。李貞忍不住問:“那這個宅子要怎麼辦?”
黑人以為李貞不放心權達的尸,說:“義安公主放心,那個男人的尸我會用火煉化,保證不留一點痕跡。之后我會用傀儡假冒他出門,短期,王都不會發現這里有異。”
李貞想要說什麼,張了張,最終什麼也沒說,掀開轎簾進去了。人已經死了,說再多又有何用,斷就斷的干脆一點,拉拉扯扯才是難看。
李貞坐好后,沒覺外面有人,轎子忽然四面浮空,隨后,就飛快朝東北方馳去。李貞嚇了一跳,慌忙扶住窗戶。過搖晃的簾子,發現自己完全飛了起來,僅憑一臺紙做的轎子,竟然在空中無驅自。
Advertisement
本來是很神奇的事,但是李貞心里忽的一突,不由想起多年前那場慘案。
朔方兵變……不就是紙兵紙將變真人嗎?
天邊炸響煙花,地上放鞭炮的孩子了眼睛,指著天空對父親說道:“阿爹,天上有花轎在飛。”
他的父親抬頭,黑藍的蒼穹如一只張大的巨,靜默無聲,唯獨竹在天邊留下些許煙跡。父親拍了兒子的腦袋一掌,說道:“別胡說八道。再不聽話,小心妖怪把你抓走!”
小孩著自己后腦,不滿地嘟囔:“剛才我明明看到了……”
冬日天空極黑,李貞又飛的高,除了剛才那個意外,再沒有人注意到天上飛著一頂無人花轎。轎子看起來不堪一擊,但速度卻很快,李貞在轎中瞇了一小會,被突然的落地驚醒。
李貞迷迷糊糊掀開簾子,外面的人看到,三步并做兩步跑過來:“阿貞,是你嗎?”
李貞一下子清醒了,看向來人,眼淚洶涌而出:“阿兄。”
李貞和李許抱在一起,抱頭痛哭。高宗在世時他們兄妹兩人日子就不好過,李貞被著剃了頭,李許被囚在吳王府,終生不得外出。他們以為這就是最糟了,沒想到,更糟糕的事遠在后面。
天后竟然登基了,連自己的兒子都能廢,何況對于他們這些庶子庶。李貞被一貶再貶,但好歹留了一條命在,李許卻是差點進了鬼門關。
他們兄妹倆盡苦楚,如今再見面,真是又悲又痛。李貞哭得正力,忽然聽到旁邊傳來一聲咳嗽。李貞嚇了一跳,趕抬眼去看,發現影里竟然站著一個人。
他罩著純黑披風,站在角落里一言不發,幾乎和黑暗融為一。要不是他主出聲,李貞還真沒有發現這里有人。
Advertisement
穿著斗篷的人靜靜站著,聲音和方才那個人一樣低沉沙啞:“吳王,義安公主,隔墻有耳,有什麼話不妨到里面說。”
李許似乎很聽這些黑人的話,斗篷人一說,他就收起眼淚,拉著李貞進屋。兄妹兩人近四年未見,坐下后,免不了相互問詢:“兄長,你這些年過得怎麼樣?”
李許嘆了一聲,說:“前兩年雖然無法自由行,但好歹還算安穩。但是從永徽二十四年起,日子就一天賽一天艱難。”
永徽二十四年,高帝病逝,天下徹底落天后之手。天后睚眥必報,稱帝后一方面控制李懷,一方面也要防備別人用李許的名義造反。李許過得可不止是艱難。
“對我們的看管一日比一日嚴,最后,連出殿都不行了。我已經忍讓到這種程度,沒想到竟然還不滿意。十月,給我送來了毒酒。”
李貞驚恐地捂:“毒酒?阿兄,那你……”
李許嘆氣:“當時我本以為此命休矣,我都做好準備去地下和父皇、祖父告狀,沒想到,遇到了諸位仙師。仙師救走了我,并用一個傀儡替我喝下毒酒。幸而東都的人沒有發現異常,很快就收拾東西離開了。他們走后,仙師說壽州不安全,帶我來了這里。”
剛才在轎子中的時候李貞睡著了,沒留意路線,但是通過呼吸間冷的空氣,四周巧的園林,不難猜出這是哪里。
應當是江南某座城池,是哪里,李貞就認不出來了。
李貞聽到兄長被仙師救下,長長舒氣,本能追問道:“阿兄,那嫂嫂呢?”
李許頓了一下,沒有接話。李貞看著沉默的兄長,很快聯想到權達,慢慢明白了。
李許見妹妹已經猜出來,沉甸甸開口:“你嫂嫂……沒有逃過。”
Advertisement
李貞睜大眼睛,那一瞬間想問,真的是吳王妃沒有逃過嗎?仙師能救李許,看今夜他們轉移的樣子,行事也十分游刃有余,那為什麼不能再多救一個人?
或許,是仙師不愿意,也或許,是李許不想冒險。真假摻半才是最好的掩護,如果兩個人都是假的,很容易被人發現破綻。到時候,李許也要跟著死。
李許不想再提吳王妃。雖為王妃,卻沒過幾天好日子,陪他度過了漫長的圈生涯,很多年都是他們兩人相依為命。沒想到,最后卻替他死了。
李許問妹妹:“阿貞,你呢?當年我被那個毒婦圈,無法帶你離開,這些年,你在東都委屈了吧。”
李貞默然,很認真地想了想,發現除了行不自由,每天照鏡子會挫傷自尊心外,在東都似乎沒多罪。就連被流放,也是躺在床上,被別人照顧。
李貞低聲說:“我還好。”
李許依然很生氣,說:“你堂堂皇,尊貴的金枝玉葉,竟然被指給一個守門侍衛,簡直豈有此理!那個人呢?”
“他已經死了。”李貞垂著眼睛,聲音輕到聽不見,“我勸過他,但是他一心向著武氏,還勸我安貧樂道、自力更生,勿要說武氏的壞話。我沒辦法,只能用仙師的酒將他毒死。”
李許聽到權達已經死了,可算出了口惡氣。他用力握著李貞的手,說:“一介莽夫,死不足惜。本來以他的資質,這輩子連給你提鞋都不配。要不是武氏惡毒,豈能得到他尚公主?阿貞你放心,下一門婚事為兄必親自為你把關,一定要挑一個十全十的世家公子。”
李貞聽到李許說世家公子,終于打起神。是啊,終究是一個莽夫罷了,是公主,只要的兄長有權勢,天底下有的是男人前赴后繼對好。若是兄長沒權勢,堂堂皇,難道下半輩子還指一個男人的好過活?
Advertisement
李貞在深宮中長大,最是知道那個位置有多麼目眩神迷,引人心折。當初武氏握有大權,只是一個眼神,就能讓闔宮上下對李貞視而不見。李貞恨武氏,但更想為武氏。
權達勸知足常樂,小富即安,呵,窮人沒吃過山珍海味,所以能日復一日嚼糠咽菜;商人沒當過,所以能小掙一筆就心滿意足;權達沒見識過皇權巔峰,所以能說出平淡是真。但是李貞見識過,知道權勢是多麼無所不能,寧愿為了爭奪權勢而死,也不要像個市井俗婦一樣,一輩子數著銅板過日子。
李貞說:“兄長,婚事不必急,你先做大事為要。”
李許以為李貞對權達有愧疚,當即說道:“那怎麼行!你本來婚就晚,再過幾年,你年紀都大了……”
“阿兄。”李貞止住李許的話,說,“如今你雖然騙過了武氏,但那個人多疑,你假死的消息瞞不了多久。我們當務之急是趕快招攬力量,反周復唐。等你大權在握,天下男人任我挑選,還有人敢在乎我的年齡嗎?”
“說得好。”
李貞和李許都嚇了一跳,紛紛站起。然而兩邊的黑人看起來反應更大,他們慌忙站好,對著門口的方向長長下拜:“主上,您怎麼來了?”
來人罩在一個寬大的斗篷中,臉上帶著銀面。雖然同是黑,但這個男子的斗篷明顯華貴許多,裁剪十分講究,邊緣還繡著致的暗紋。他緩慢走屋宇,舉止間行云流水,雖然看不到臉,但不難猜到,面后必然是一張極俊的臉。
來人進屋后輕輕抬手,兩邊的黑人這才敢直起。有人慌忙去吹屋角的燈,被來人攔住:“不必了,這點本尊得住。”
李許和李貞從周圍人的反應上到來人不同尋常,他們兩人為皇子皇,面對來人竟到一不自在。
李許比李貞早來兩個月,這些日子他住在這個別院中,除了不能出門,再沒有其他不適。李許來來回回見了好些黑人,但還是第一次見此人。
看起來,這像是他們的首領。
李許問:“不知閣下是何人?是你救了我們兄妹嗎?”
“不敢當,略盡些綿薄之力罷了。”來人在眾多黑人的侍奉下坐好,黑廣袖靜靜搭在膝上,一舉一自帶貴氣,“鄙人姓秦,家中行長。”
李許在心里想了一下,姓秦?似乎沒聽說哪個族信秦。或許這是他的托辭吧,李許沒有在意,拱手道:“秦大公子。”
李許想要拉關系,特意用了客氣的稱呼,其實他還差錯對了。古時諸侯之子才能公子,后來這個尊稱泛化,民間也可以相互敬稱公子。
秦惟聽到這個稱謂,角輕輕一勾。秦大公子……這個稱號,實在許久沒有聽過了。
秦惟比手,對李許李貞說道:“吳王,義安公主,請坐。”
李貞立馬注意到他的手掌極其漂亮,似乎許久不見,他皮冷白,不見,致完的如同玉雕。他的聲音也很好聽,語調不疾不徐,說話自帶三份笑意,聽著就讓人心生親近。
原來真的有人,僅聽聲音就能判定為男子。
李貞走神的功夫,秦惟已經和李許說起外事。朝廷最大的事就是主天下,李許氣得不行,不斷罵武氏牝司晨。
相比之下,秦惟就優雅從容多了。他等李許發泄的差不多,才悠然截斷他的話:“太后篡位,吳王意如何?”
“自然是招兵買馬,攻,清君側,復李唐江山。”
秦惟輕輕點了下頭,問:“清君側不難,但是,哪一位是君?”
李貞和李許都沉默了。過了片刻,李許說道:“自然是太子李懷。他是父皇親封的太子,景明元年亦登基稱帝。他才是真正的皇帝。”
李許說完,不知為何,有些張地看向秦惟。秦惟的臉沒在面后,他許久未言,忽然輕輕笑了一聲:“鹿失其野,群雄逐之。我以為,吳王是個英雄。”
李許不由屏住呼吸,問:“你這是何意?”
猜你喜歡
-
完結169 章

女法醫穿書后和男二he了
法醫謝箐穿到了一本年代文里,成了那個為襯托女主而存在的對照組妹妹。為避免被狗血的主劇情波及,她火速離開家庭,住進宿舍,一頭扎進刑偵事業中。女主忙于戀愛時,她在解剖尸體。女主忙于親情時,她在解剖尸體。女主忙于賺錢時,嗯,她也悄默聲地跟著賺了一…
52.1萬字8.18 15445 -
完結114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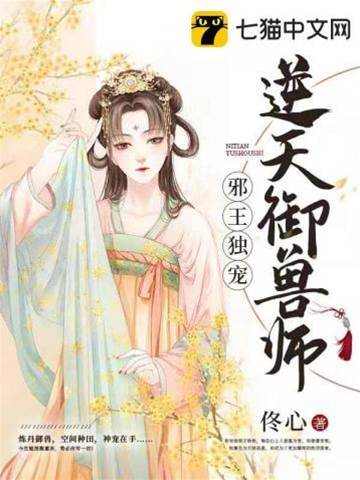
邪王獨寵逆天御獸師
前世她傾盡一切,輔佐心上人登基為帝,卻慘遭背叛,封印神魂。重生后她御獸煉丹,空間種田,一步步重回巔峰!惹她,收拾的你們哭爹叫娘,坑的你們傾家蕩產!只有那個男人,死纏爛打,甩都甩不掉。她說:“我貌丑脾氣壞,事多沒空談戀愛!”他笑:“本王有錢有…
215.2萬字8 2364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