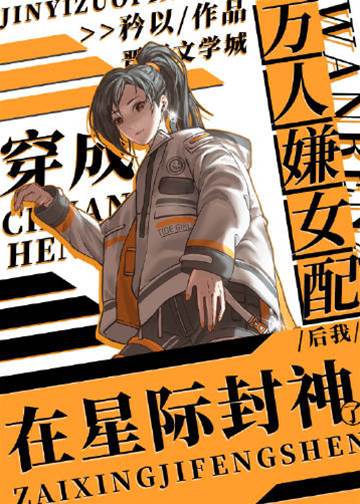《謫仙》 第81章 明珠
“不是我舉辦。”李朝歌糾正道,“是你來牽頭,趁著過年舉辦一場宴會。相關花費我可以承擔,但我不認識多人,所以宴飲場地、邀請客人等,需得請你幫忙。”
高子菡挑眉,手里握著團扇,慢慢倚靠在憑幾上,頗為意味深長地看著李朝歌:“你之前不是從不關心宴會嗎,今日怎麼想起辦宴會了?”
李朝歌對此只是淡淡一笑,并不多談:“突然想了。”
高子菡熱衷于吃喝玩樂、結才俊,對于宮廷朝堂的向多有耳聞。高子菡想起前段時間吐蕃的國寶似乎出了些差錯,聽當值的近臣說,這樁事分配給了李朝歌。
李朝歌突然要辦宴會,莫非是為了吐蕃國寶一事?
高子菡不太懂這些朝事,但是有人花錢請主持宴會,高子菡還是很樂意應承的。尤其這個人是李朝歌,李朝歌可難得求人一次,高子菡想到這里,越發上心:“好,你放心,我保證給你辦的風風。朝廷馬上就要放假了,這段時間該閑的都閑下來,邀人并不麻煩。你看場地定在芙蓉園如何?”
芙蓉園是一皇家園林,專門給達貴人宴飲的。李朝歌是一個外行人,對宴會沒有任何要求,唯獨提了兩點:“你請人時,不必說明是我,以你自己的名義下請帖就好。我聽說最近來樓的西域舞姬名聲正盛,你派長公主府的家丁去,把那位舞姬請來,若賓客中誰家有擅舞的人,不妨一起帶來,讓們好生切磋切磋。”
后一點對于高子菡來說不難,但是前一點……高子菡仔細看著李朝歌,問:“你是不是有什麼打算?”
“沒有。”李朝歌微微笑著,說道,“你也知道我在東都中名聲兇惡,若是客人得知我開宴會,誰還敢來?錢你不必擔心,無論花多都我來出,你只管放手籌辦,以你的名義廣邀賓客即可。”
Advertisement
高子菡第一次遇到這種出錢還不要名的傻大頭,盯著李朝歌,最終沒有再問,半開玩笑說:“好,我明白了。我聽聞盛元公主食邑千戶,家厚,圣人和天后的賞賜如流水一樣抬到德昌殿里,今日,總算能見識一二了。”
李朝歌如今確實不缺錢,六歲走丟,之后圣人和天后為了補償,第二年就給封了公主,劃了最沃的地方給做封地。李朝歌的封邑和食俸年年漲,雖然不在京城,但這些年的公主俸祿卻一直積攢著。等李朝歌回京,一恢復份就接手了一大筆財富。
的公主府也修葺得差不多了,等明年,就能搬到公主府去。到時候自己開門立戶,當家做主,錢財只會更多。李朝歌如今的眼界遠非錢財富貴能滿足,對這些外之并不在意,說:“無妨,你放手去辦吧。”
高子菡不愧是東都際花,李朝歌廿四那日去找,到了廿六,高子菡就將宴會張羅好了。朝廷元日給假七天,廿七只需要當值半日,就徹底迎來放假。朝廷忙了一年,終于到了歇息的時候,家家戶戶都非常歡喜。高子菡在假期前一天設宴,各家郎君娘子都很給面子,興高采烈地來了。
芙蓉園前香車寶馬,香鬢影。因為是高子菡設宴,李常樂被皇帝放出宮,歡歡喜喜地帶著公主儀仗來了。裴楚月和李常樂早就約好了,裴楚月站在自家馬車前等,一看到李常樂,立刻揮手道:“廣寧公主!”
李常樂跳下馬車,也高興地撲到裴楚月邊:“阿月,你的病好了?”
裴楚月年中撞鬼,原因外面不得而知,但為此卻大病一場,半年都沒怎麼在外走。今日年節,裴家大夫人想掃一掃裴楚月上的病氣,便讓裴紀安送裴楚月出來了。
Advertisement
半年不見,裴楚月瘦了很多,眉宇間雖然還是模樣,眼睛卻黯淡許多,仿佛籠上了一層看不見的哀愁。裴楚月聽到李常樂的話,淡淡笑了笑,說:“是。”
裴楚月回想半年前的事,依然覺得恍如大夢一場。祖母和母親對此一字不提,裴家也沒人敢談撞鬼。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避開那件事,可是裴楚月自己卻記得,和人結了冥婚。
那個人是心頭最的妄想,整個時期無法宣諸于口的傷。清醒時不敢,沒想到被鬼附后,卻大膽和表兄婚。
然而,冥婚未,若是了,就無法活著站在這里了。裴楚月不知道顧表兄知不知道那件事,但是之后顧表兄早出晚歸,每天大部分的時間都待在大理寺,偶有休沐,也錯開時間去給祖母請安。裴楚月心里不知道是酸還是苦,看他的表現,無論他知不知道冥婚一事,他們都不可能了。
裴楚月這一場病不只是,更是心病。
李常樂看出來裴楚月興致不高,只當裴楚月虛弱,不放在心上,說:“沒事,病好了就行。今日高表姐請來了西域舞姬呢,我們一起去看舞,說不定你一高興,病就好了呢。”
裴楚月勉強笑笑,蒼白著臉應話。李常樂和裴楚月說完話后,守在一邊的裴紀安才上前,給李常樂行禮:“廣寧公主。”
李常樂早就看到裴紀安了,歡歡喜喜跑到裴家的馬車前,裴楚月是一小部分因素,裴紀安才占了大頭。李常樂如愿聽到裴紀安的聲音,端著的矜持,回頭對裴紀安微微一笑:“裴阿兄。聽阿父說,裴阿兄辦事十分得力。今日,裴阿兄不在阿父邊跟著?”
Advertisement
“今日是同僚當值,圣人得知高娘子設宴,便讓臣先出宮了。”
李常樂哦了一聲,臉上的笑都不下去。高子菡在門口迎客,看到裴家和廣寧公主來了,連忙迎接過來,笑道:“楚月,廣寧公主,你們來了怎麼不進去?外面冷,有什麼話進去說。”
高子菡是今日東道主,李常樂應了一聲,拉著裴楚月就往芙蓉園里走。李常樂和裴楚月都是十四五的,帶著天然的青春稚氣,兩個人手拉著手小跑在芙蓉園門口,頓時吸引了不視線。
裴紀安跟在后面,看著妹妹和廣寧公主提著子小跑,一路笑臉洋溢,無憂無慮,目中浮出慨。他多麼希妹妹和廣寧公主一直這樣天真無邪,裴家和長孫家永遠枝繁葉茂,和樂安康,永遠不必擔心朝廷的風波打到裴家和長孫家上。
可是,這是不可能的。沒有家族可以一直高枕無憂,裴紀安這幾個月跟在圣人邊,最明白皇帝的已經糟糕什麼程度。如今政務已經全部出于天后之手,裴紀安曾試著提醒過皇帝,政務應該讓太子接手,但是他看到太子比皇帝還不如的,也唯有嘆氣。
裴紀安前世一度覺得天后和李朝歌上位是小人得志,倒行逆施,天后能稱帝,不過是靠母親的份拿住了李懷而已。現在裴紀安回到一切變故發生之前,他越接近權力核心,越發覺武后上位,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寒門崛起,科舉逐漸為民心所向是天時,皇帝頭疾、太子弱是地利,而天后出的政治天賦就了人和,這幾個條件,但凡缺一個就無法造就古往今來第一位皇帝。歷史的浪洶涌而來,李朝歌是這流中抓住了機遇的幸運兒,而裴家,是和流對抗的犧牲品。
Advertisement
裴紀安重生后,越努力越覺得無力。以一己之力對抗歷史浪,何其渺小,何況,天后是皇帝的妻子,李朝歌是皇帝的兒,而裴紀安只是一個臣子。一邊是外臣,一邊是妻子兒,皇帝會信誰呢?
這是一個毫無懸念的賭局。
裴紀安往臺階上走去,兩邊傳來眾人笑的問好聲,這些世家名流沉浸在五十的宴會中,完全不知道兩年后他們將要面臨什麼。從魏晉時便是世家巋然不,皇帝番換人,這些大族養尊優太久了,多年來已然習慣世家與皇權共天下,完全忘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沒人能想到,下一位皇帝竟然是出小門小戶,最為世家看不上的天后武氏。也沒人能想到,世家引以為傲的門第和聲,如果皇帝愿意給面,那就是世家清貴,如果皇帝撕破臉,那些清高,在武力面前一文不值。
裴紀安心嘆氣,越發覺得無力。高子菡剛才送李常樂和裴楚月進門,轉看到裴紀安走上臺階,蹲問好。
裴紀安如今是東都里的大名人,家世好長得好,還在皇帝邊任職,可謂是世家眼里最熱門的婿人選。可惜裴紀安和廣寧公主青梅竹馬,早就對公主一往深,若不然,世家和皇帝爭上一爭,也未嘗不可。
高子菡知道裴紀安是皇帝邊的紅人,日后定的卿相人選。高子菡不想得罪這條潛龍,對裴紀安非常客氣:“裴郎君安好。郎君里面請。”
裴紀安回禮,正要進門,背后傳來噠噠的馬蹄聲。今日是高子菡設宴,芙蓉園前人來人往,客流不斷,裴紀安沒把后面的人當回事,東都里需要他親自相迎的人本沒多。裴紀安走了兩步,突然聽到一個悉的聲音:“高表姐。”
“呦,盛元公主。”高子菡笑著迎上去,“我千盼萬盼,總算把你盼來了。你這主人當得真是省心,說不管,當真撒手一點都不管。”
裴紀安霍得回頭。他看到臺階下,李朝歌穿著一紅束腰制服,肩上系著黑斗篷,對高子菡說:“鎮妖司有事,我不得,現在才來。今日有勞你了。”
高子菡嗔怪地瞪了一眼,說:“我明白,盛元公主是大忙人,每日忙得很。誰我當初應承了你呢,活該在這里替你勞碌。”
李朝歌后還跟著一個人,察覺到高子菡的視線,隨口介紹道:“這是我的侍。”
莫琳瑯低頭,老實地跟在李朝歌后,如同一個小心翼翼的侍。高子菡掃了一眼就收回視線,一個侍而已,不到高子菡注意。高子菡引著李朝歌往芙蓉園里走:“客人已來了許多,來樓的舞姬馬上就到。哎,裴郎君,你怎麼還站在這里,為什麼沒進去?”
說著,高子菡瞇著眼看向旁邊的引路丫鬟,丫鬟連忙叉手,面懼。裴紀安開口道:“沒事,是我走得慢,和們無關。”
說完,裴紀安看向李朝歌,拱手行禮:“盛元公主。”
李朝歌冷淡點頭:“裴拾。”
出了場,依然他的職,客氣的近乎生疏。裴紀安苦笑,大概這就是報應吧,前世是他不屑一顧,今生,到他小心翼翼,卻得不到一個正眼。
高子菡眼看這兩個人僵下來,不知為何,趕圓場道:“好了,門口還有客人呢,你們兩位快到里面坐著,勿要耽誤我迎客。”
李朝歌正要借機,后乍然傳來一道清清冷冷的聲音。
“盛元公主。”
李朝歌一聽這個聲音,二話不說提著擺就走:“我還有事,先走了,失陪。”
高子菡一回頭見是顧卿,驚訝地眼睛都瞪大了。裴紀安也殊為吃驚:“表兄?你不是說大理寺忙著結案,沒時間來參宴嗎?”
顧明恪看著李朝歌,輕輕一笑:“本來沒時間,但是得知盛元公主也在,就想過來和公主談些事。”
樊勇走私的夜明珠還在李朝歌手里,沒有證,大理寺沒法結案。而夜明珠牽涉到李朝歌自己的案子,沒找回飛天前,李朝歌肯定不愿意出東西。
這就了一個死循環。顧明恪心道真是報應,之前李朝歌為了莫琳瑯的案子追他到宴會上,現在李朝歌天在外面忙,顧明恪在鎮妖司等不到李朝歌,也只能追到別人的宴會上。
風水流轉,蒼天饒過誰。
作者有話要說:留言30個紅包。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