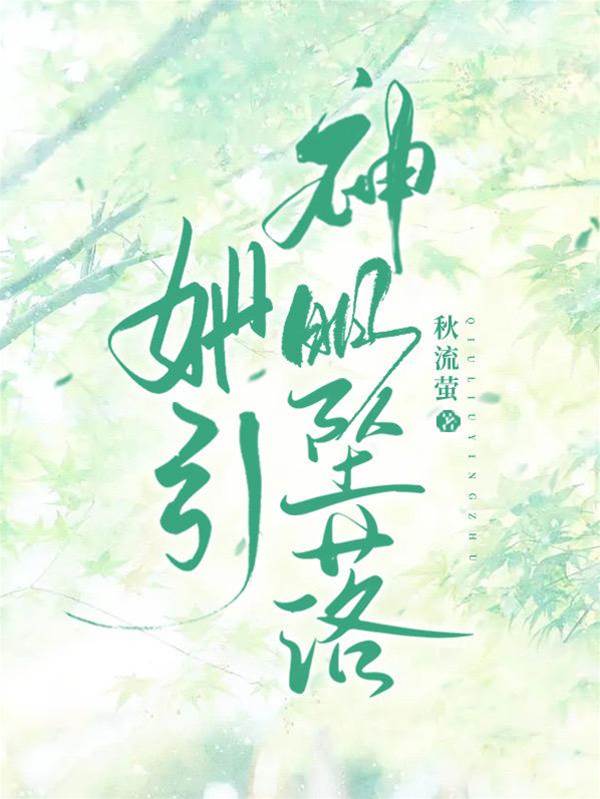《漸漸》 第25章 夏蟬
“他不是,”徐未然很快否認:“就是我同學而已。”
“哦。”
谷真掏出一煙點燃,不知道煙是什麼牌子的,味道很嗆人,徐未然忍不住咳了兩聲。
“這事是我沒看好,以后像他那種流氓我不會再讓他進店的。”谷真一邊煙一邊說:“不過你這同學下手也太狠了,”看向一邊斜倚在墻上的邢況,說:“小伙子,有話跟人好好說,別一來就手啊。這要是被人舉報斗毆,我這店還開不開了。”
邢況有些不耐:“您能先把煙掐了嗎?”
“啊?哦!”谷真把煙碾滅:“然然同學是吧,你今天不管消費多都是我買單,盡管玩啊。”
邢況嚨里冷笑了聲,再抬起頭時目里有了威脅的意思:“你跟很?”
“不怎麼,”谷真從煙盒里又掏了煙,忍著沒點燃:“可跟我侄子啊,他們倆可是青梅竹馬呢。”扭頭看向徐未然:“是不是啊然然?”
這話其實并沒什麼,但徐未然還是聽得別扭,并不想讓邢況有一分一毫的誤會。
“就是初中的時候認識而已,”也不明白自己怎麼這麼急于解釋:“不是什麼青梅竹馬。”
“初中認識怎麼就不算青梅竹馬了,”谷真還在拱火:“我那侄子對你多好啊,特地把你介紹過來,還讓我要時刻關照你,說不能讓人欺負你,你這可倒好,連個青梅竹馬都不認,他知道了得多傷心。”
徐未然更尷尬,了耳垂,著頭皮繼續補充:“真的只是普通朋友。”
“行了,你們都回去吧。”谷真的煙癮是真忍不住了,開始往外面趕人。
徐未然跟在邢況后走了出去。
到了外面,邢況轉看:“你在這上班?”
Advertisement
“是。”
“幾點下班?”
“十……”徐未然卡了會兒殼,想不明白他為什麼要問這個,過了會兒才說:“十點。”
邢況沒再說什麼,回去帶著李章和錢蒙走了。
臨出門前,李章頻頻扭頭看。
后面一直風平浪靜,并沒有醉酒的客人再來找徐未然麻煩。差不多悉了一遍工作流程,到十點后準時去接。
谷真知道一個人住,沒有經濟來源,平時吃飯都是問題,破例把的工資日結,給了現金。
徐未然腦子里一直回旋著剛才那個醉鬼的話,擔心他會過來尋仇。
天已經很黑,雖然這一片是商業區,有尋歡作樂的男男不時來往,還是有些怕,不時往后看一眼。
前面路口有個公車站,能搭到回家的末班車。
往前跑了兩步。路過一個水果攤時,看見攤主彎著腰收拾地上的脆桃,一邊撿一邊抹眼淚。
走過去幫忙撿了幾個,攤主從手里接過桃子,哽咽著說謝謝。
路旁邊有個騎電車的中年人,好像是剛才沒有及時剎車,把水果攤撞倒了。怕自己會被訛,極力地數落攤主不該在這個路段擺攤,還威脅說要去找城管。
扯著嗓子說了幾句,中年人騎上車跑了。
攤主看著自己袋子里幾乎壞了一半的脆桃,有些不知道該怎麼辦。兒給打了個電話,接起來,跟那邊說:“乖寶兒啊,媽媽很快就回家了啊。今天生意可好了,我這就去給你買蛋糕,你在家等著媽媽啊。”
攤主把袋子扎上,背著往前走,軀被得快了一座橋。
徐未然了口袋里的一百塊錢,朝跑過去:“阿姨,您這些桃子能賣嗎?我剛好想吃了,您能把這些都賣給我嗎?”
Advertisement
攤主詫異地看著:“小姑娘,這些桃子都摔壞了。”
“沒有啊,我剛才看見了,還是好的。您這賣的不是脆桃嗎,不會容易摔壞的。”
徐未然幫忙把袋子從背上拿下來,打開看了看,從里面拿出一個完好的:“您看,還是好的。哇,這些桃子看起來就很好吃,一定很甜,我逛了好幾個超市都沒看見過這麼大這麼紅的桃。阿姨,您可以把這些都賣給我嗎?這樣我就不用再跑超市了。”
攤主像是遇見了救星一樣,死氣沉沉的眼睛立馬亮了些:“那我把沒壞的給你撿出來,壞了的你就別要了。”
“不用了阿姨,您直接一起稱就好了。我還趕時間的,再晚就坐不上末班車了。”
“好,好,那我現在就給你稱。”
攤主把剩下的桃子稱了一遍,算了算:“一百零三塊,你給我七十就好了。”
“這是錢,您拿著。”徐未然把一百塊放到手里,拎著一大袋桃子就跑:“阿姨我走啦,您也快回去吧。”
攤主想給找錢,追了幾步沒追上。那姑娘看上去瘦瘦小小的,跑起來卻很有勁,像是要扛著桃子去拯救世界一樣。
攤主停下來,看了看手里的一百元錢。
并不是假的,而是一張真鈔票,貨真價實的一百元。
徐未然過了十字路口,把桃子放下來,累得了幾口氣。
在路邊找了個長椅坐下。跑得有點,很想從蛇皮袋里拿個桃出來吃。
這麼想著的時候,面前出現了一瓶水。
抬起頭,在滿天繁星下,看到了邢況。
男生骨節分明的手指握著礦泉水瓶,瓶口朝上,朝那里又送了送。
愣愣地接過來:“謝謝。”
瓶蓋已經被人擰松,毫不費力就旋轉開,咕嘟咕嘟一口氣喝了大半瓶。
Advertisement
邢況在旁邊坐下,看了看兩人中間擱著的蛇皮袋。
覺袋子里的東西都要比重,不知道剛才是怎麼拎得的。
徐未然了角的水痕,問他:“你怎麼還沒走啊?”
邢況并沒回答,只是問:“袋子里是什麼?”
“脆桃。”打開袋子給他看:“是不是又大又紅?我真的賺到了,一百塊買這麼多。以后應該能有半個月不用買水果了。”
邢況心里被人絨絨地抓了一把,涌出一些古怪的,他看不懂的緒。
“不會壞?”他說。
“應該不會吧,脆桃保質期是不是要長一點兒?”認真琢磨:“要是撐不了那麼久我就給朋友送點兒好了。”
邢況結了,明知道很無聊,可還是意味深長地問:“朋友是谷睿?”
“啊?”
“青梅竹馬算朋友嗎?”他側頭看,一雙眼睛在夜下黑得像化不開的墨。
徐未然不自在地了耳朵,覺得他有點兒奇怪:“青梅竹馬的意思不就是朋友嗎?不然還會是什麼?”
邢況扭回頭,半晌,突然說:“行。”
徐未然不知道他這個字是什麼意思,總覺自己被威脅了一樣。
尷尬地又去喝水。
或許是因為自己已經不再花相倪的錢,就相當于不再欠任何人的了,有了些底氣,這些底氣讓可以平等地跟邢況相。
問了一句以前的自己絕對不會問的。
“那俞筱是你的青梅竹馬嗎?”
空氣有了兩秒鐘的靜止,就連遠路上奔跑的車輛都沒有聲音,車燈無聲地穿在這個黑夜。
兩秒后,聽到了回答。
“只是普通朋友。”
他說,只是普通朋友。不僅用朋友來形容,還在朋友前加了普通兩個字。結合上次他說的,他沒有朋友,所以他跟俞筱并不是別人傳的那種關系,而是可以用普通朋友來定義的普通關系。
Advertisement
心里像漲了,水是過載的,一下一下地漫過心田。
徐未然并不想承認,但不得不正視,當得到這個答案的時候,心里是開心的、雀躍的。
懷總是詩。喜歡上一個人,因為他好看,格冷淡但迷人。因為看時的目幽沉深邃,像黑,捉不到底地把吸引進去。更或者只因為第一次見到他的那天下了雨,而他在風雨來前,像是從天而降的神祇般,把從泥濘里救了出去。
喜歡他。很喜歡很喜歡。但又不敢喜歡,所以一直抑著自己的,不敢讓任何人發覺,甚至不敢讓自己發覺。愫無數次冒出來,又被不容地斬斷,告訴自己,你跟他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地方在與,你跟他不僅要用不僅份懸殊,而且要用而且他有可能在討厭你,覺得你是小三的兒,傷害了俞筱的。
不僅與而且像是一條鴻,把牢牢地攔在喜歡他的條件之外。
可是現在,仍舊會因為他的一句話而開心,會越來越清楚地覺到是喜歡他的。從沒有過心的覺,因為一些小說和偶像劇的啟蒙,曾幻想過心會是什麼樣子。但真正發生的時候,發現心比自己想象得更要矛盾,既好又折磨人,一邊因他而小鹿撞,一邊怕自己沒辦法跟他在一起。
而現在來看,跟他能在一起的幾率,好像也并不是很大。
但不想再管了,任憑自己先麻痹在今晚短暫的相中。
思緒紛地想著,聽到邢況問:“為什麼染發?”
“因為,我想去沒趣打個零工,可是老板說我看起來年紀有點兒小,他就讓我去染頭發。”一五一十地告訴他,好奇地問:“你看我現在有沒有一點兒?”
無意識地朝他那邊靠近了些,有又香又甜的氣息地過去。偏還一臉無辜干凈的樣子,很認真地想讓他看,到底有沒有一些。
他的目從孩圓圓的杏眼上往下,看直秀氣的鼻梁,白皙的臉頰,殷紅的。
的兩瓣微微張開,像在不自知地勾引著誰。
邢況目往上,重新與孩對視。
他朝那里近了些,距離鼻尖只有一指的時候停下。
開口時嗓音有點兒啞:“太暗看不清楚,你再離近點兒,我好好看看。”
“……”
猜你喜歡
-
完結428 章

年代甜炸了:寡婦她男人回來啦
(全文架空)【空間+年代+甜爽】一覺醒來,白玖穿越到了爺爺奶奶小時候講的那個缺衣少食,物資稀缺的年代。好在白玖在穿越前得了一個空間,她雖不知空間為何而來,但得到空間的第一時間她就開始囤貨,手有余糧心不慌嘛,空間里她可沒少往里囤放東西。穿越后…
97.7萬字8 28516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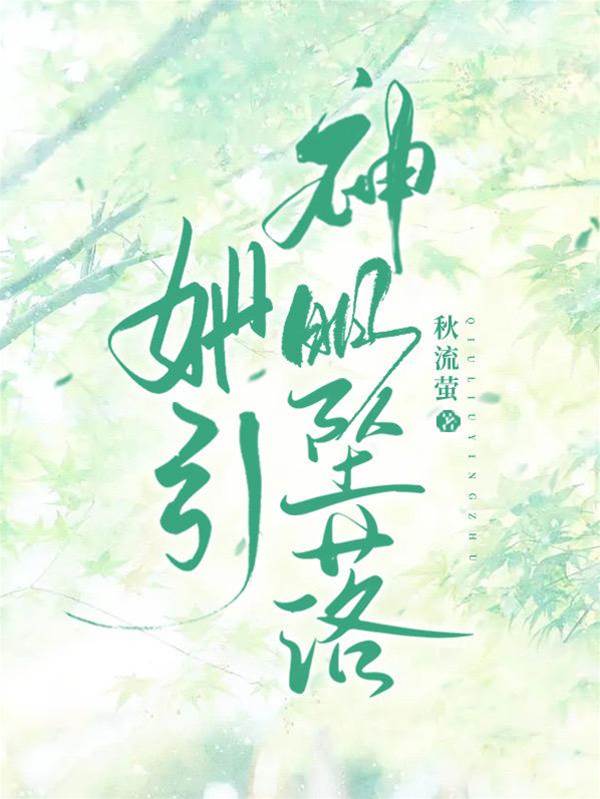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509 -
完結221 章

春意入我懷
【大學校園 男二上位 浪子回頭 男追女 單向救贖】【痞壞浪拽vs倔強清冷】虞惜從中學開始就是遠近聞名的冰美人,向來孤僻,沒什麼朋友,對前仆後繼的追求者更是不屑一顧。直到大學,她碰上個硬茬,一個花名在外的紈絝公子哥———靳灼霄。靳灼霄這人,家世好、長得帥,唯二的缺點就是性格極壞和浪得沒邊。兩人在一起如同冰火,勢必馴服一方。*“寶貝,按照現在的遊戲規則,進來的人可得先親我一口。”男人眉眼桀驁,聲音跟長相一樣,帶著濃重的荷爾蒙和侵略性,讓人無法忽視。初見,虞惜便知道靳灼霄是個什麼樣的男人,魅力十足又危險,像個玩弄人心的惡魔,躲不過隻能妥協。*兩廂情願的曖昧無關愛情,隻有各取所需,可關係如履薄冰,一觸就碎。放假後,虞惜單方麵斷絕所有聯係,消失的無影無蹤。再次碰麵,靳灼霄把她抵在牆邊,低沉的嗓音像在醞釀一場風暴:“看見我就跑?”*虞惜是凜冬的獨行客,她在等有人破寒而來,對她說:“虞惜,春天來了。”
39.6萬字8.18 627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