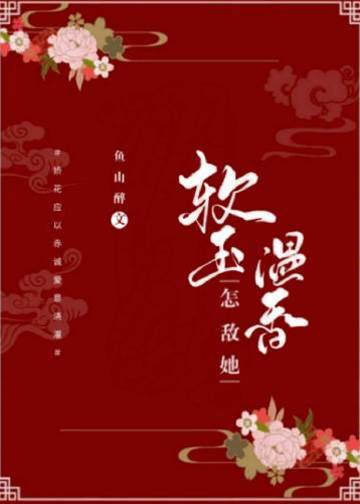《拯救偏執首輔后》 我應該贖罪
沈芷甯将秦北霄拉到一暗巷。
臨近各大酒樓夜市,雖看似安靜沉寂,但總有遙遙傳來的喧嘩熱鬧聲,昏暗中也夾雜着幾分亮,那是近酒樓華燈通明。
停下來後,那攥秦北霄袖的手一松,轉看他的面容淡漠,似是毫無的目掃過還抓着袖的手,再與對視。
這神、這眼神。
他應該很不高興了,也是,見都不想見到、以後不想有任何牽扯的人就這麽一點分寸都沒有的拉他過來,正常人都不會高興吧,更何況是秦北霄呢。
沈芷甯蜷了蜷手指,徹底将手收回了袖内:“抱歉,秦大人,是我莽撞了。”
“還知道莽撞?沈小姐這舉怕是會讓人誤會,”他的聲音平靜,平靜得沒有任何波瀾,沉着聲道,“罷了,你想說什麽?”
沈芷甯擡眸看他。
他似乎沒有在看自己,僅留了個側臉,照進昏暗小巷中的微弱燈火映着他棱角分明的下,就算在如此溫和平靜的環境内,還存着那分迫與侵略。
說他變化大呢,也不能說大,畢竟五都長在那兒,與在吳州時沒差,可說他變化不大,卻是大的,無論樣貌個子還是整氣勢,若說之前還有點年的氣息,如今是個真正的男人了。
但不管是之前的他還是現在的他,這三年來,想的都是秦北霄。
想說什麽,想說的實在是太多太多了。
可知道他不會喜歡聽的,他都不喜歡見到,許是恨極了。
更何況,也不能與他過于親近。
下心中一切波瀾,沈芷甯道:“方才在如意樓,多謝秦大人相助——”
秦北霄暗沉的眼神掃過來、徑直斷了的話:“你就隻想說這個?”
沈芷甯一愣,随後點了點頭:“是,畢竟如果沒有你的幫忙,那二人也不會說那些話來,我還是要謝謝你的……”
Advertisement
秦北霄的臉越來越沉,用着肯定的口氣:“你把我拉來,就隻是爲了剛才的事是嗎。”
随後,他頓了頓,語氣寒:“那大可不必這般隆重地拉我過來,你也誤會了,我沒有任何要幫你的意思,若真要幫,何必等到後來,早在他們前面辱你之時就出面了。”
這句話的意思,你不要自作多了。
沈芷甯低頭垂眸,輕輕哦了聲:“也是,那确實是我誤會了。”
其實今日是很高興的,特别是他後來出現的時候,就算不能對他說,更不能對任何人承認,但心裏還是極爲清楚明白,那一刻有着無法掩蓋的欣喜。
欣喜他或許就是在幫,可他的話将暗存的喜悅一下子澆滅了。
說得沒錯,以他的子真要幫,又怎麽會等到後來,那些人不是早就開始對出言不遜了?他的子,圈在地盤裏保護的人又怎麽會容許别人說上一個字。
除非已經不在他圈的地裏了,他毫不在乎了。
沈芷甯忍着間翻湧上來的意:“真是不該的,擾着秦大人了,先告退了。”說罷,轉就想走。
想快點走。
不要再在秦北霄面前丢人了。
再待下去,恐怕還會再丢人。
然而轉的那一刻,人被生生拉了回來,手腕被他給鉗制,他似乎借着燈火在認真看,可那眼神還是冷的:“沈芷甯,你在哭嗎?”
這句問話一出,那本就翻湧的酸之意更爲洶湧襲來。
沈芷甯拼命推開秦北霄,想離開,不想讓他看到自己的面容,更不想讓他看到即将要泛紅的眼眶。
可秦北霄就是沒放開,甚至抓手腕的力氣越來越大,聲音極沉:“沈芷甯,你哭什麽?”
“我沒哭。”沈芷甯穩着自己的聲音,盡力将自己隐在黑暗中,不讓他發現自己緒的波,“我不會哭的,秦北霄,你放開我。”
Advertisement
許是真的隐藏得太過于冷靜,使秦北霄一時愣了,趁這個發愣時機,沈芷甯掙開了他。
秦北霄回過神後,面從方才的神不明恢複到了淡漠,好像就從未做過拉住沈芷甯的事一樣:“我看錯了,也是,沈小姐又怎麽會是耽于小小的人。”
說到這兒,他的語氣似帶了幾分嘲諷,随後繼續慢聲道:“莫急着走,你沒有其他的話要說,我可還有。”
沈芷甯立刻擡眸。
可他未馬上開口,昏暗中的男人似乎沉默了許久,最後歎了口氣,膛發出了一聲自嘲似的輕笑:“沒有其他,是想問問沈小姐,若沒有餘氏的反對、沒有顧家的親事,還會遵守當年許下的諾言嗎?”
沈芷甯子頓時一僵,渾的湧上心頭。
張了張,好多好多話堵在嚨間,卻不知道該說哪一句:“……你知道了,不同意……顧家的婚事,實際上也不是你想的那樣,不對……可沒有假如啊,秦北霄——”
“行了,别說了。”他冷厲打斷了的話,眼神中似乎在瘋狂着什麽,“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沈芷甯不明白秦北霄明白什麽了,實則都不知道自己說了些什麽,他的那句話給的沖擊太大了,以至于都靜不下心思考怎麽回答他。
若真的沒有那些事,怎麽不會去遵守呢,可說了沒有任何意義,難道隻是給互相一個安嗎?可這他不應該早就知道的事嗎?
爲何還要問?
“秦北霄,我不太明白你。”沈芷甯輕聲道。
“可我明白你,就算沒有那些事,你也不會遵守與我的諾言。”
并沒有那麽他,他就是眼中那個可以随時抛棄的人。
秦北霄的聲音沙啞低沉,着極其複雜的緒:“你他媽就是個騙子,是個戲子,從認識的剛開始就耍弄欺騙我,接近我,演出一副心的樣子,真他媽演得好啊,你自己都要信了吧沈芷甯,我圈、騙我進套,被你耍得團團轉,你是不是也要這麽騙顧熙載?是不是也要端着這幅樣子嫁去顧家?你現在還與我在這兒私會,顧熙載知道會——嘶!”
Advertisement
膛傳來一陣鑽心的疼痛。
沈芷甯要被秦北霄的話弄瘋了,方才死命憋住的緒與眼淚大發了出來,像個發怒的小、徑直咬上他的膛。
他說的什麽話?
恨不得就這麽咬死他。
裏腥味與鹹味混合了一起。
秦北霄忍着疼,未推開,等牙齒的力度小了,發洩夠了,才出左手,一把住的下颚,冷聲道:“沈芷甯,三年沒見,你變屬狗的了?”
他用的力氣大,下颚骨頭被他得生疼。
沈芷甯知道他也氣得很,他以前生氣就是現在這個神,沉至極,可他現在越是這樣,越是難過,特别是想到剛才的話,滾燙的淚水留在指腹與臉頰隙之間,也順着下去。
“秦北霄……”掙紮哽咽道,“你不我了,現在恨極了我吧。”
他着自己下颚的手頓了頓,漸漸松了。
沈芷甯似乎看見了他眼神中有着愕然、不解……還有那麽一悲痛絕。
隻聽他咬牙切齒道:“恨你?我是恨極了你,恨得無數次想回吳州殺了你與你同歸于盡,與你到地下相互折磨!恨得我看不慣一個顧家的人、見不得一個顧字,特别是那個顧熙載,沈芷甯,你可知道我在京的這幾年,要費多大的勁才能不讓他的存在折磨我?隻要我一想起來,今後他要娶你,要與你同床共枕,當真恨不得,剝他的皮剔他的骨!”
沈芷甯愣在原地。
秦北霄眼睛赤紅:“我多恨啊,恨你什麽都不跟我說,恨你本就從未把我放在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比我重要,你的師父、區區一個徒弟的名義就可以讓你當年就這麽放棄我,我今日說的話狠嗎,沒有你當時的一半,你卻不了了,沈芷甯。”
Advertisement
不是的,并非從未把你放在心上。
你很重要。
沈芷甯直搖頭:“不是的……”
他輕笑出聲,眼眶紅得徹底:“什麽不是的,就連方才我問你,沒有餘氏的阻攔、沒有顧家的親事,你願不願意遵守當時與我的承諾,你也是閃爍其詞,連一句騙我的話都不肯說。沈芷甯啊,我确實恨你,但我也輸了。”
說罷,秦北霄再也不肯多說什麽,也未再看沈芷甯一眼,擡步就往外走。
沈芷甯上自己的面,已滿是淚水,回過神追着他:“秦北霄,不是這樣的,真的不是這樣的……”
他走得好快,也本不想與再說話了。
沈芷甯心口仿佛絞在了一起,快速跑過去,抱住了秦北霄。
他腳步頓時停了。
沈芷甯圈着他瘦的腰,臉頰着他溫熱的後背,到他子僵,又聽他沙啞的聲音:“……你這又是在做什麽?”
“你不要走,秦北霄。”沈芷甯圈他的力氣加大,哽咽道。
秦北霄沒有說話,轉過,沈芷甯害怕他走,将頭又埋在了他膛前,死死抱住他,一刻也不松開。
秦北霄無法形容現在到底是什麽心,口漲漲的,間也有酸之意,他實際上該推開了,可他不想,甚至就這樣被刺穿心髒也無所謂。
口一片潤,許久之後,悶在那裏道:“秦北霄,真的不是那樣的,你比任何人都要重要,可是,一切都是我的錯,我要贖罪……我不能忤逆師父的母親,我得贖罪。”
說完這句話,擡頭,已被咬得鮮淋漓,眼神滿是絕悲哀:“因爲是我害死了師父,你知道嗎,秦北霄,是我害死他的,我是個災星,是罪人,應該死的人是我。”
猜你喜歡
-
完結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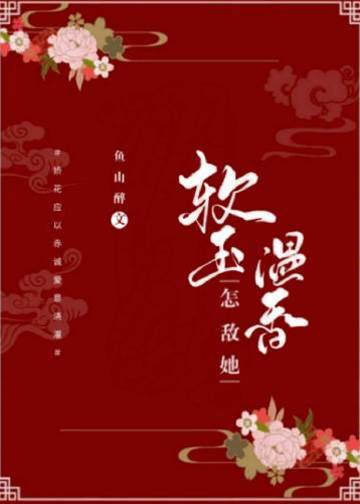
怎敵她軟玉溫香
提起喬沅,上京諸人無不羨慕她的好命。出生鐘鳴鼎食之家,才貌都是拔尖兒,嫁的男人是大霽最有權勢的侯爺,眼見一輩子都要在錦繡窩里打滾。喬沅也是這麼認為的,直到她做了個夢。夢里她被下降頭似的愛上了一個野男人,拋夫棄子,為他洗手作羹湯,結果還被拋棄…
21.9萬字8 10627 -
完結356 章

養丞
童少懸第一次見到家道中落的唐三娘唐見微,是在長公主的賞春雅聚之上。除了見識到她絕世容貌之外,更見識到她巧舌如簧表里不一。童少懸感嘆:“幸好當年唐家退了我的婚,不然的話,現在童家豈不家翻宅亂永無寧日?”沒過多久,天子將唐見微指婚給童少懸。童少懸:“……”唐見微:“知道你對我又煩又怕,咱們不過逢場作戲,各掃門前雪。”童少懸:“正有此意。”三日后,唐見微在童府后門擺攤賣油條。滿腦門問號的童少懸:“我童家
150萬字8 1875 -
完結559 章

一念桃花
八年前,常晚雲在戰亂中被一名白衣少年救下,她望著眼前的少年,俊美,有錢,當場決定我可以; 八年後,常晚雲終於知道了少年的身份。 當朝皇帝的九皇子,裴淵。 重新見面,晚雲作為醫聖唯一的女弟子,來到裴淵身旁為他療傷,阿兄長阿兄短。 裴淵日理萬機,只想將她送走,甚至當起了紅娘。 豈料趕人一時爽,追人火葬場。 晚雲冷笑。 憑本事踹的白月光,為什麼還要吃回去?
95.3萬字8 104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