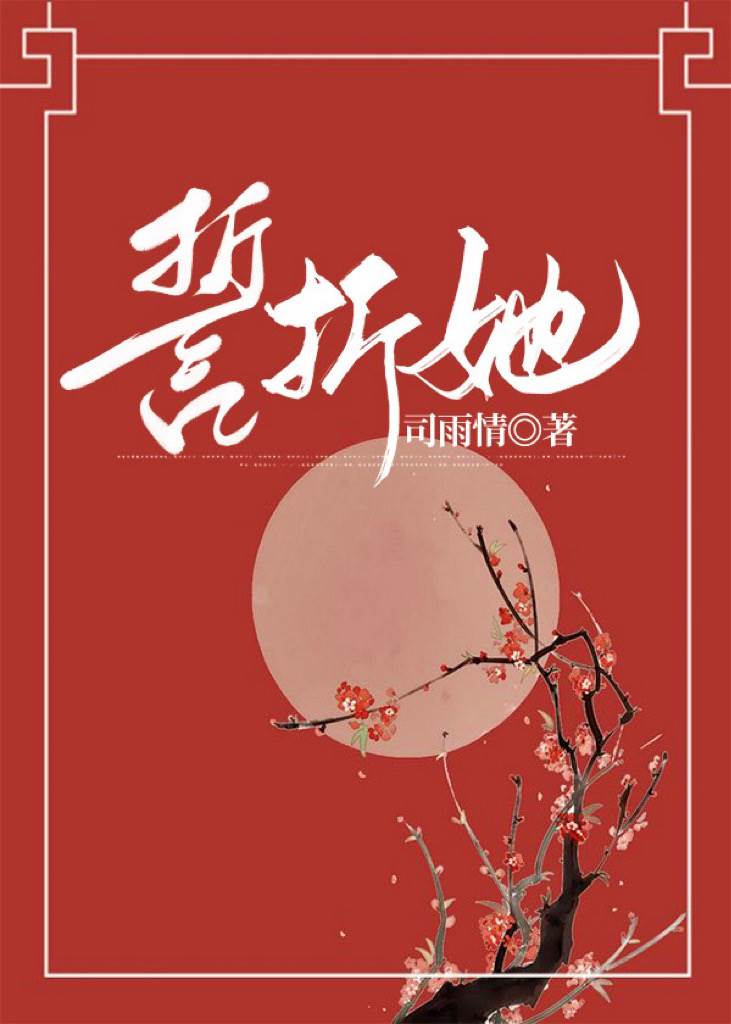《重生明珠》 龍孫
龍孫
當晚鄭明珠也并沒有守歲,待宴席撤下,陳夫人當著太夫人等人的面吩咐丫鬟:“進去與夫人說,無甚要事,早些回去歇著。”
鄭明珠就施施然的走了出來,對陳夫人笑道:“媳婦不恭,先回去歇著了。”
對著在場眾位長輩福了福,便扶著兩個丫頭走了。
太夫人和三叔祖母看起來還很想說點什麼,可今天都沒討著好,大約也無力再戰了。
陳夫人笑道:“這樣冷的天兒,不如太夫人和嬸娘們都挪到里頭炕上去,把桌子也擺到炕上,倒也暖和些。”
太夫人歪著,怒氣沖沖的說:“人也不齊,這守歲還守什麼,難道咱們這種歲數了,誰還是健壯子不,竟也不必撐著了,我也要回去歇著了。”
陳夫人也并不勸:“太夫人說的也是,守歲無非就是那個意思,倒是一家子子要,太夫人也還沒大好,越發早些歇著,也是好的。”
又吩咐丫鬟:“前兒我吩咐給太夫人新做的里外發燒的水貂斗篷可得了?取來給太夫人披上,幾個懂事穩重的小廝跟著轎子,好生服侍太夫人回去。”
又轉頭對陳三嬸娘笑道:“既然太夫人要歇著了,我自然不好留你,你要多費心才是,我給你們家哥兒姐兒都新裁了服在那里,既不得空兒,就另打發人給你送去罷了,那箱子預備給太夫人打賞孩子們的銀錠子也人抬著一起送去。只三弟妹務必好生伺候太夫人。”
旁觀的嬸娘都暗想:這兒媳婦雖說不怎麼奉承婆婆,可手面大方,想的也周到,做婆婆的若是肯只圖用,倒也是不錯的,何必這樣想不開呢。
陳三嬸娘更是笑逐開,忙忙的應著,直說了三五聲‘大嫂想的周到’。
Advertisement
太夫人狠狠的剜了陳三嬸娘一眼,當初給老三挑媳婦,也是挑了又挑的,見家世雖差些兒,也是嫡長,原該見過些世面才是,怎麼竟這麼倒霉,娶了進來才知道,眼皮子這樣淺,老大媳婦一點小恩小惠就把喜的見牙不見眼。
沉著臉直往外走,三叔祖母見狀,也跟著一起走了。
其他幾個叔祖母,本來也沒打算在這侯府守歲的,不過因太夫人是大嫂,把陳家人召集起來除夕團聚,不好不來,本來也就打算吃了宴席,說些閑話就告辭的。
沒想到看了這樣一出好戲。
此時紛紛告辭,這個正月都有話題好聊了。
太夫人進了房,就把端進來的燕窩粥給摔地上了,雖然依然歪著,發起脾氣來也是利落的,罵了一通,把服侍的丫鬟都趕了出去。
三叔祖母朝院子外頭張了一下,見崔媽媽沒進來,才說:“這崔婆子今日回去了?”
提到這個崔媽媽,太夫人越發恨的牙,自上回謝媽媽被發作后,如今邊全是侯府的人,丫頭們還好拿,有事不過他們出去也就是了,可這崔媽媽卻是油鹽不進的,太夫人有事要商議的時候,出去,只走到門邊,就站住了笑道:“屋里一個人沒有,奴婢怎麼敢出去,奴婢在南京的時候,姑就吩咐過要小心謹慎當差,侯夫人吩咐奴婢來伺候太夫人,更是再三說了太夫人子不好,一天十二個時辰,屋里決不能一個人沒有,生怕萬一有個什麼意外,竟沒人知道,眼見得們都出去了,奴婢自然不敢出去,太夫人有話只管與三老太太、姨太太說,不用當有奴婢這個人,或是就當奴婢沒長耳朵就是了。”
Advertisement
竟就立在門口當個門神,太夫人罵也罵過,脾氣也發過,甚至連杯子都朝他擲過去過,只是巍然不,要陳三嬸娘來責罰,陳三嬸娘只賠著笑說,這是侯府的人,媳婦怎麼好罰。
要把打發回侯府,只跪著請罪,并不彈,且一院子的丫鬟婆子都得了吩咐,聽調配,說話竟比太夫人還好使。
如今竟是拿一點辦法都沒有。
以致后來太夫人不管什麼時候商議,都得,趁著崔媽媽去院子外頭辦點什麼事的時候說了。
太夫人提到就恨的咬牙切齒:“這個黑了心肝爛了肺的死婆子,今兒除夕,我早早就放了假回去了。”
三叔祖母拍拍口:“謝天謝地。”
走回到太夫人邊道:“我的老天,原來那個就是花姨娘,虧得大嫂指點的快,不然鬧起來,就越發麻煩了。”
提到今兒的事,太夫人就一肚子氣:“你說你怎麼就那麼準呢?非得去挑的閨的事兒?幸而走的快,若是真鬧起來,是出了名兒的破落戶,要什麼名聲臉面?只是混鬧,只怕倒把咱們的臉面都給丟了,且如今這樣子,咱們還不好招惹的。”
咬著牙道:“前兒那事,原本是老大家的想要整治花姨娘和老三的,沒承想被敏惠郡主倒打了一耙,倒是掙了臉面去,竟就白便宜了老大家的,還挑唆了花姨娘和我鬧,白白吃了個啞虧,沒做了,反倒結了仇怨,如今正是要好生哄著們娘倆的時候呢,你倒惹,如今吃一頓罵,還不是白給!”
三叔祖母屈道:“這委實怪不得我,瞧的舉,誰家里不是嫡才是這樣兒呢,哪家的庶不是要規規矩矩小心翼翼奉承嫡母的呢?我自以為這便是三小姐了,哪里知道竟是!我想著,大嫂今兒本來也是為著立威,雖說和
Advertisement
咱們預計的不一樣,您這侄孫媳婦有些出乎意料,不過只要著罰了三小姐這樣唯一的嫡,也是一樣的打了你那兒媳婦的臉,誰知認錯了!”
太夫人道:“你也想一想,別人家自然是嫡張揚些,庶小心些,可咱們家如何一樣,三丫頭雖是嫡,卻是天生的安靜子,倒是,姨娘有三品誥命,哥哥十六歲就有了爵位,如今就連老大還沒封世子,也要矮他一頭呢,如何與別的庶一樣?自然傲氣些,小姑娘家又不懂進退,你倒去挑的錯,越發鬧起來。”
說的三叔祖母越發后悔起來:“今兒原是一心想著拿你們家老大那一派的人做伐,在眾多親戚跟前先立起來,也人知道,大嫂才是侯府的老祖宗呢,沒承想偏認錯了人。”
說著瞧瞧太夫人的臉,忙扯開話題:“說起來倒也奇了,你們家那侄孫媳婦,原本三子打不出個屁來,但凡有點大小事,只會哭,我原想著大嫂是嫡親的祖婆婆,只要拿出老祖宗份來,拿住真是半點兒不費力,怎麼這一回,就這麼伶俐會說話了?”
提到這個,太夫人越發氣惱道:“你到底是聽了誰跟你下的蛆?說的這樣,什麼最是弱不懂事,話也不會說,連院子里一個嬤嬤都能拿住,的管事貪嫁妝,也半點兒察覺不到,針尖大一點兒事也慌的不得了,只會哭,或是回娘家去……最是好拿的。今兒你看看,這樣伶牙俐齒,真是連我也把臉丟了!”
真是越說越氣,先前見罰的時候,答的又溫又恭敬,還以為果然一下子就拿住了,沒承想……
三叔祖母連忙道:“這話可不止一個人跟我說過,我雖三五年沒去過侯府,到底是一家子分出來的,家里的下人也多有些親戚在里頭,這可是你那好兒媳婦親口抱怨給邊的洪媽媽的,定然沒有錯……如今想一想,莫非是因著有了孕,見一家子都捧著,竟就膽子大起來?”
Advertisement
太夫人想了想:“說的也是。”
三叔祖母笑道:“既如此,那也就好辦了,人的秉哪有這樣容易變的?如今仗著婆婆撐腰,多寶閣外頭又有公公、相公,一時膽子大了,說那些話也是有的。只要今后好生尋了時機,落了單,沒了幫村,大嫂再拿出祖婆婆的份教訓,豈不是就慌起來?自然就好拿了,只要待收服了,那鐵鑄般的侯府也就有了缺口,大嫂自然就能事事順利了。今后再有了老三那邊使力,大嫂何愁不能重掌侯府?”
太夫人也笑了,雖說臉歪著,這笑也很像哭一樣:“你說的也是,想來回回見,都是有婆婆,相公在的,自然膽子大些,這樣一個年輕媳婦,能經過什麼事,孝道上去,別說是,就是再老些的,也不敢犟。”
三叔祖母忙笑著應是,又奉承了無數好話,商議出數十個萬無一失的計謀來,只待日后好下手,越說越是歡喜,就仿佛那些計謀已經了似的。
鄭明珠當然不知道有人在背后議論算計,早早的就歇下了,待陳頤安守歲后回了房里,已是后半夜了,鄭明珠都醒了兩回了,此時抬起一只手遮著瞇著眼睛,迷迷糊糊的問:“才散啊?你累了吧,人服侍你洗澡睡了吧?要不要吃點宵夜,我吩咐人傳去。”
陳頤安把的手臂塞進被子里:“你睡你的,別惦記我。兒子還乖吧?今兒聽說鬧了一場,他可發脾氣沒有?”
鄭明珠好笑:“又沒他的事,發什麼脾氣,你趕著睡吧,這樣冷的天。”
陳頤安想兒子,又怕手冰了鄭明珠,還是先洗漱去了。
待他從凈房出來,鄭明珠已經清醒了很多,披著皮襖兒靠在床頭,旁邊小幾上擺著一碗熱騰騰的湯面,見陳頤安出來,就親手捧過來笑道:“廚房里有新燉的藕燉骨頭湯,看著還清淡,煮一碗湯面,吃一點暖和些。”
陳頤安笑著接過來吃,雖然鄭明珠沒問,他還是吩咐墨煙進來:“先前回我的話,再與夫人說一說。”
墨煙便笑道:“回夫人,今兒那位三老太太,夫人沒見過吧,奴婢原也不大清楚,后來回了大爺,才知道,這位三老太太原是太夫人娘家嫂子的妹子,當初三老太爺的元配沒了,太夫人做主聘了進來做填房的,三老太太娘家差些兒,一直奉承太夫人,如今太夫人娘家的舅老爺升了兒,不管是往太夫人這里,還是姐姐那邊,都越發勤了。”
原來是這樣!
鄭明珠本來也猜想今兒突然發難多半和太夫人那突然抖起來的娘家有關,此時聽了墨煙說的,便笑道:“又是那檔子事兒,怪煩的,回回都拿我來發難,也真是倒霉。”
見陳頤安吃了半碗面放下了,便笑道:“罷了,又不是什麼大事,大爺早些歇了吧,幸而明兒可以晚些起來。”
兩人便一起安歇不提。
只沒承想這話說的太滿,才睡下不到兩個時辰,天還黑著,墨煙就進來了,在門口輕聲值夜的瑪瑙:“請大爺醒醒兒,有十分要的事兒回大爺。”
鄭明珠睡的多,又本來警醒些,便聽到了,輕輕推推邊的陳頤安:“醒醒,有事兒。”
一邊墨煙。
墨煙語氣里都是喜氣:“回大爺,夫人,太子妃娘娘剛剛誕下一位龍孫。”
陳頤安瞬間便清醒了。
鄭明珠笑,真是好消息,正月初一出生的龍孫哎。
猜你喜歡
-
完結300 章
王妃脾氣爆:皇叔,請節製
一朝穿越成傻妞,廚房茅房傻傻分不清。幸有爹孃疼愛,四位兄長百般嗬護成長。笑她目不識丁癡傻愚頑?一朝驚天地,袖手弄風雲。從此商界多了個不世出的奇才!說她軟弱可欺任意拿捏?上有護短狂老爹撐腰,下有妹控兄長為她收拾善後。權傾朝野號稱天下第一美色的輔助親王,更是化身寵妻狂魔,讓她橫著走!某天在金子堆裡數錢數的正歡慕容明珠,被一雙大手覆上「王妃,今晚我們……」「一邊去,別妨礙我數錢」「……」
52萬字8.18 10969 -
完結11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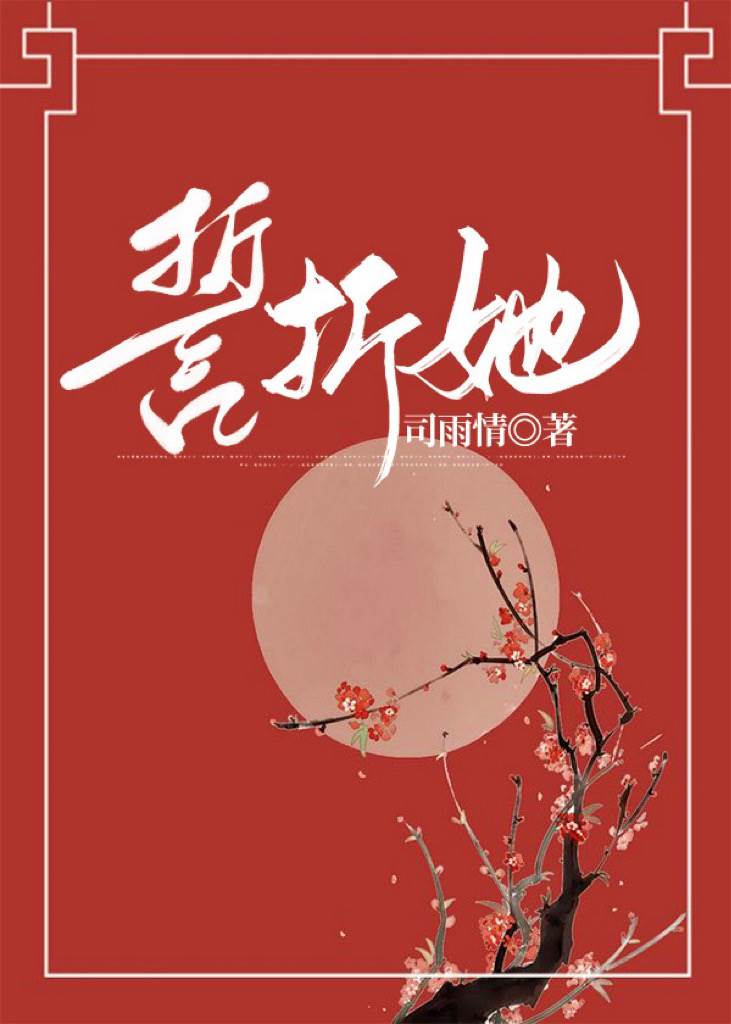
妄折她
昭華郡主商寧秀是名滿汴京城的第一美人,那年深秋郡主南下探望年邁祖母,恰逢叛軍起戰亂,隨行數百人盡數被屠。 那叛軍頭子何曾見過此等金枝玉葉的美人,獸性大發將她拖進小樹林欲施暴行,一支羽箭射穿了叛軍腦袋,喜極而泣的商寧秀以為看見了自己的救命英雄,是一位滿身血污的異族武士。 他騎在馬上,高大如一座不可翻越的山,商寧秀在他驚豔而帶著侵略性的目光中不敢動彈。 後來商寧秀才知道,這哪是什麼救命英雄,這是更加可怕的豺狼虎豹。 “我救了你的命,你這輩子都歸我。" ...
40.2萬字8.18 6703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