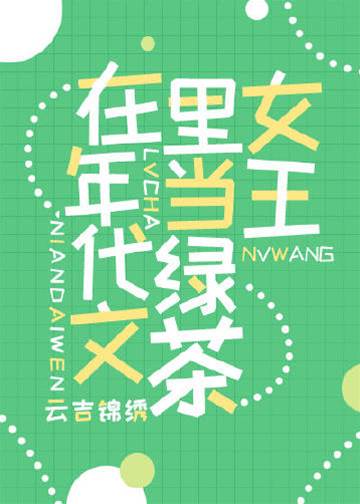《她作死向來很可以的》 第112章 第一百一十二章
楊不棄確實什麼都沒看到。
他順著徐徒然所指, 不管怎麼看,都只能看到被紅籠罩的幽深樹林。徐徒然聽了他的質疑,反皺了皺眉。
“你沒看到嗎?那麼大一個兔子雕像, 兔頭下面還有須須, 怪可的……”徐徒然下意識地描述了兩句,注意到楊不棄越發茫然的表, 話語驀地一頓。
旋想起什麼似的, 拉開自己的袖子看了眼,旋輕輕嘆了口氣:
“不好意思, 應該是我看錯了。”
只見手臂上的符文,確實已經變淡些許。再看楊不棄的臉,徐徒然不出意外地發現對方臉上也出現了古怪的起伏, 甚至能模模糊糊看到抱臉蟲的廓。
這更佐證了的想法——符文的效果果然已減弱不, 那雕像想來應該也只是幻覺之一。
于是也沒再多說什麼, 只默默用筆將手臂上符文補好, 轉頭再看, 果然已經看不到遠那座巨大的黑兔子雕像了。
重新審視楊不棄的臉,也已經變得平整潔俊朗帥氣,遂長長呼出口氣, 將筆往口袋里一揣:
“好了, 沒事了, 走吧。”
語氣輕松,拽著楊不棄往前走去。臨走前沒忘拿出地圖來再看一眼——沒有了大雕像的指引, 只能憑借著地圖, 再結合方才白熊逃跑的路線, 來大致確定行進的方向。
兩人再次于樹林間移起來。被楊不棄強塞進口袋的小花探出頭來, 瘋狂甩了甩被塌的腦袋, 手腳并用地爬出來,順著兩人相牽的手一路跑,徑自跑到徐徒然的肩頭,愉快坐下。
楊不棄原本正擔憂地看著徐徒然的手臂,目被它吸引過去,不太高興地皺了皺眉,跟著視線又落在徐徒然抓著自己的左手,不知想到什麼,眸微微閃。
Advertisement
“那什麼,其實不用牽這麼……”他謹慎地開口,卻沒有任何要將手離的意思。徐徒然回頭瞟他一眼,“誒”了一聲:“可是牽著保險點吧。我聽人說游客在這林子里會走散的。”
這話是從茶室子那兒聽來的。雖然按的意思,哪怕同行的人將彼此綁在一起,也會在不知不覺中失散,但徐徒然覺得,牽著總歸比不牽保險點。
楊不棄聞言,低低“哦”了一聲,不知該不該告訴徐徒然,自己現在和普通人類不一樣,應該不存在類似的問題;而還沒等他開口,徐徒然忽然腳步一頓。
“那什麼,楊不棄啊。”蹙眉打量著眼前的場景,語氣出幾分狐疑,“再跟你確認下。我們現在所在的林子,是正常的嗎?”
這麼問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此刻在的眼里,這片林子非常不正常。
只在行刑場周邊逗留時還沒覺,往前再走個幾十步,就能明顯到周遭的變換——眼下的林子同樣被紅籠罩,然而那層芒卻充滿了一種奇異的流,流之中還會帶出些許偏紫偏橙的變幻,讓人仿佛置于一顆巨大的琉璃球中。
……又仿佛這本就有生命,此刻正如游魚般移。
而被這種幻所籠罩的香樟林,更是出難以言喻的古怪。樹干給人的覺更高,且帶著幾分老人般的佝僂姿態,樹冠上仿佛懸掛著什麼,時時讓人覺得頭頂正有影搖晃,但若定睛看去,又什麼都看不到了。
目及之的樹干上,或多或地還都趴著好些葉子。它們如同禪一般吸附在樹干上,青黃的葉片如同蟬翼般輕輕舒展。徐徒然一開始還不明白它們是怎麼爬上去的,直到又往前走了幾步。
Advertisement
這些葉子是飛上去的——每當從落葉中抬起腳,總會帶起幾片落葉,它們舒展著葉片,宛如小蝙蝠般在低空中翔著,有些會試圖咬到徐徒然的腳上,有的則會就近撲到距離最近的樹干上,出昆蟲般的口開始啃咬。被咬破的樹皮上,蜿蜒流下一般的紅。
如果只是這樣也還罷了,更令徐徒然無法理解的是,隨著的汲取,泛黃的葉片竟又一點點地復原青翠的綠——在流紅的籠罩下,想要準辨別其實不太容易。但有楊不棄和小花在旁邊做對比,想要區分出綠還是很方便的。
而在它們變回充滿生機的青綠后,就會再次往上飛去,重新融樹冠之中,再次為這龐大生命系中的一部分。
徐徒然:“……”
“是我加固沒做好嗎?”難以置信地喃喃自語,再次拉開袖子,“就算是幻覺,這也太離譜了一點。”
“……不,不是你的幻覺。”楊不棄抿了抿,臉凝重,“這邊的樹木確實不對勁。”
他放下抓在手中的石矛,驚飛一堆落葉。他趁機手,抓住其中一片,著它不住張合的:“這里的生命形式也很怪異。”
“說起來,我之前還發現個事。”徐徒然又想起一事,“這林子的落葉下面,似乎沒有泥土。”
“我也發現了。”楊不棄點頭,手指松開,那片葉子逃命般飛了出去,“這些樹的力量,似乎是上往下流的……”
他頓了頓,擰起眉頭,似乎在糾結于該如何表述:“而且這里生命流的方式也非常古怪。給人一種一邊凋零,一邊重生的覺……”
越往深走,這種覺越明顯。
Advertisement
徐徒然詫異:“你連這都覺的出來?”
“升級后的結果……算是有得有失吧。”楊不棄目閃爍兩下,明明徐徒然的語氣是夸獎,他的語氣卻沉重得像是嘆息。
徐徒然不太明白他這種緒從何而來,但明智地沒有多問,而是繼續往前走去。
又往前走了約三四千步,兩人前方的樹木間終于再次出了建筑的廓。那看上去像是個半球形的一角,遠遠就能看到圓潤的弧度。建筑表面不知用的什麼材料,平整明亮,流溢彩。
兩人對視一眼,加快腳步往前趕去。趕慢趕,終于來到那棟建筑之前,徐徒然抬頭窺見那建筑全貌,不由低低哇了一聲。
就如同之前遠遠看到的那樣,這東西果真是個半球形。整像是一個倒扣在地面上的巨碗,表面材料似是某種很薄的金屬,那種有彩流的視覺效果,又讓人想到教堂的彩繪玻璃窗。
建筑的外面,用石頭壘砌了一圈高大的圍墻,一側的圍墻上用紅漆寫著“蟲子博館”幾個大字,字跡之潦草,之間,簡直與鬼片必備的“還我命來”有的一拼。
然而徐徒然在意的并不是墻上的字——嚴格來說,不是這些字。
這圍墻所用的石料與用來鋪路的石子以及石矛都一模一樣,只是這里用的石頭更加大塊,徐徒然也終于得以看清上面的完整花紋——這才發現,那些以為是波浪的紋樣,實際更像是一種古老的文字。
“文字?”楊不棄微微蹙眉,跟著盯著那些形似波浪的紋樣看了片刻,不知為何竟也覺出幾分悉,但再要細看,又會覺得腦袋有些犯暈。
“那你能看懂上面寫的什麼嗎?”他問道。
Advertisement
徐徒然平靜開口:“‘因為近期行刑場發生蟲子出逃的惡|事件,本博館正門關閉。博館部照常運轉,工作人員請從后門進,謝謝配合’。”
楊不棄微微瞪大眼:“你還真看得懂?”
“……我念的是旁邊告示牌上的字。”徐徒然好笑地看他一眼,手往旁邊一指。只見石墻的前方立著一小塊告示牌,上面字跡歪歪扭扭,寫得倒全是簡中文。
楊不棄恍然大悟地點了點頭,想想自己方才的反應,也覺得有些好笑。剛想說些什麼,卻又聽徐徒然道:“不過這種文字,我似乎是能看懂一些的。”
手往石墻上虛虛一指,喃喃開口,語氣帶上了幾分飄忽:“‘當星門歸屬本位,當我們狂蹈而歌……祂循聲而來……毀滅與新生,綻放如彩’……”
念著念著,忽又皺起眉頭,手指圈過中間一大片花紋:“這里我就看不明白了,覺這邊的排列完全是的。”
仿佛一個文盲,將一堆打的漢字拼圖隨意拼接一般。看上去是字的形狀,但完全理解不了。
徐徒然又盯著看了一會兒,覺得有些頭暈,遂搖了搖頭,移開目。楊不棄似是看出的難,默默了與相牽的手指,悄無聲息地遞過去些許生命力。徐徒然有些驚訝地看他一眼,頓了幾秒,笑了一下。
“沒事,問題不大。”牽著人往石墻里面走去,“這里沒有更多線索了,我們進去看看吧。”
圍墻是沒有安裝門的,只中間空出一大塊空隙作為口。進去之后,可以看到石墻與半球形建筑之間還隔著相當一段空間,這部分空間沒有樹木,卻同樣鋪滿落葉。落葉上有很明顯的被碾的痕跡。
“看上去像是車轍?”楊不棄觀察片刻,做出猜測。徐徒然點了點頭,目落在建筑閉的大門上,“正門果然是關著的,繞到后面去看看。”
語畢一拽楊不棄,沿著車轍的印子往建筑后方走去。走了不知多久,一列悉的小火車,忽然撞眼簾。
“好家伙。”徐徒然微微瞪大眼,“原來行刑場里的小火車,是開到這地方來的!”
——只見他們面前,赫然便是之前在行刑場看到的小火車同款。唯一不同的是,面前這輛小火車只剩下了車頭以及車頭后面的兩列車廂。而這兩列天車廂,正裝著滿滿的可憎尸。
“原來如此,‘蟲子博館’,指的就是‘可憎博館’。”楊不棄也反應過來了,“不過在這里開怪展館……有什麼意義嗎?”
沒人回答他的問題。徐徒然只專注打量著車廂里的那些怪尸——楊不棄還在那兒思考這個博館存在的意義,忽然覺手上一涼。定睛一看,徐徒然竟是干脆松開了他的手,自己跑到車廂旁邊去。
楊不棄:“……”
他看看正興致拿著石矛挑來揀去的徐徒然,又看看自己空落落的左手,默了一下,艱難出聲:“你低調點,當心被人看見……”
“我就隨便看看。”徐徒然目不轉睛道,小心翼翼用矛尖挑起一片薄薄的,“哇,你看,這個八爪魚好大!比我之前打的那只還大!”
……你以為你是在趕海嗎還帶比八爪魚大小的?
楊不棄一時失語,剛想說些什麼,徐徒然忽然臉微變,快步小跑回來,拽著他后退好幾步,躲到了建筑投下的影中。楊不棄帶著疑問看過去,徐徒然忙低聲音解釋:“有人過來了,我聽到聲音了。”
話音剛落,果見一只大白熊晃晃悠悠地從小火車的另一邊走了過來。與其他白熊不同,這只白熊前圍了一大片的圍,手上戴著一副很大的紅的手套——看上去厚的,有些類似于烘焙手套。
那只大白熊完全沒發現徐徒然等人的存在,快快樂樂地晃過來,在看到車廂上的可憎尸后,不掩嫌棄地用戴著大手套的熊爪掩了下口鼻,旋即彎腰,不知做了什麼作,輕輕松松地就讓最后一節車廂與前面的車離開。跟著便見它單獨拖著那一節車廂,吭哧吭哧地離開了。
徐徒然豎著耳朵,直到確認聽不到腳步聲了方從影里鉆出來。先是看了看現在僅剩一節車廂與車頭的小火車,旋即又繞到了它的前面——
但見火車頭的前方不遠,便是圍墻的另一個出口。圍墻對面的半球形建筑上,卻依舊平潔,連一道隙都沒有。
猜你喜歡
-
完結162 章

穿成極品受他爸
看了朋友推薦的一本耽美,肖望被裡面的極品渣攻和極品賤.受氣得肺疼,但最讓他咬牙切齒的,是賤.受他爸! 這個賤.受的爸也是個受,更是個頂級極品,自從帶著兩歲兒子與渣攻他爹重組了家庭,就任勞任怨當牛做馬,凡事都以渣攻爹和小渣攻為先,自己兒子卻委屈得連奴才都不如! 小渣攻天天牛奶雞蛋吃到吐,自己兒子連肚子都填不飽,他還在想著晚飯給渣攻爹和小渣攻換什麼口味。 小渣攻新衣服多到落成山,自己兒子衣服破到落補丁,他還教育自己兒子要知足別攀比。 小渣攻零食多得吃不完,自己兒子饞得去拾小渣攻扔的糖紙偷偷舔,被小渣攻發現後當胸一腳踹出老遠,哭得喘不上氣,他第一反應是教訓自家兒子不要饞。 小渣攻故意篡改自己兒子的高考志願,導致自己兒子落榜,他還勸自己兒子別太小氣。
47.7萬字8 6819 -
完結312 章
穿書之福運男妻
魏子航穿書了,成了書里一個十分悲慘的炮灰。 原本是天之驕子的他,結果被人抱到了農村養; 原本考上了最好大學的他,結果被人冒名頂替; 原本應該和親生父母相認,結果被養父母賣到了黑煤窯挖煤; 原本應該過上好日子,結果被設計嫁給一個病癆沖喜; 魏子航怒了,手握異能,完全不按劇情線走! ——等等,說好的體弱多病站都站不起來的病癆呢?這個讓他三天下不了床的人是誰?不行,他要離婚! ——離婚?想得美!在他霍成毅這里,沒有離婚,只有喪偶!!!
91.7萬字8 26311 -
完結110 章

虐文女主只想煉丹
小頂本是九天上一只金燦燦、圓滾滾的煉丹爐,一朝穿進一本名叫《我是師尊的極品藥鼎》的小文文里 她一心以為自己能繼續老本行,誰知卻成了個膚白貌美、腰細腿長的少女 小頂:??? 回頭拜讀原文,她才知道此鼎非彼鼎。原書女主癡戀清冷師尊,師尊卻只把她當修煉工具 不可描述了百八十章,女主被榨干最后一絲靈氣,然后被無情拋棄,凄涼地死在師尊迎娶真愛的當晚 小頂:…… 她決定遠離渣男,發揮特長,煉丹自救 后來,師尊斷了筋脈,原文用女主療傷 小頂“呸”地吐出一顆極品仙丹:逆天回春丹,原價十萬靈石,親情價一百萬 師尊:? 再后來,師尊傷了元神,原文用女主續命 小頂:十全大補丸,原價五十萬靈石,親情價一千萬 師尊:?? 再再后來,師尊中了情毒,原文用女主解毒 小頂:葵花斷根丹,這個可以白送你 師尊:??? 忍無可忍的師尊堵上了她的嘴:“閉嘴……張嘴。” ————————————— 男主和原書男主無關 團寵瑪麗蘇女主,肚子里真有煉丹爐,外掛逆天 ———————————————————————————— 預收復仇虐渣文《那個替身回來了》(點專欄收藏~) 十六歲以前,師尊就是冷胭的神 她猶記得五歲那年初見,尸山血海中一人佇立,白袍勝雪,豐神如玉。天神般的人向她伸出手:“師父帶你回家”。 十六歲生辰,她的神親手剖開她的靈府,抽出她的元神,一刀刀剮碎,她才知道從頭到尾,她只是另一個人的替身和容器 冷胭本該魂飛魄散,卻陰差陽錯留下一縷殘魂,禁錮在原地,看著身體被另一人占據,看著他們恩愛百年,直到恨意熔鑄成新的靈魂 …… 都說當世第一大能玄淵道君與師妹青梅竹馬、宿世姻緣,是羨煞整個修真界的神仙眷侶。 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心頭有一點胭脂色的淚痣。 他以為她已魂飛魄散,惟余空山舊夢,夜夜煎熬。 直至三百年后,修真界忽有一人橫空出世,一招驚鴻睥睨四海,三尺青鋒橫掃六合 那個曾經只會默默忍痛、無聲垂淚的小姑娘,終于踏著鮮血與白骨來到他面前,劍指咽喉:“我回來了。” ——————— 注意:上述男人僅為復仇對象,非女主cp
38.1萬字8 7252 -
完結256 章
穿書後,鹹魚娘娘不小心成了團寵
本是古医世家天才继承人,一睁眼却穿成炮灰女配? 谁人都知,永安侯府嫡长女夏落是个草包。 嫁了病秧子太子,全上京城都在可怜她,太子却神奇病愈。 昔日战神重返巅峰,视她如珠如宝。 面对一屋子莺莺燕燕,众人都在看她笑话,她却直接躺平。 宫斗争宠?不存在的。 她只想当一条混吃等死的咸鱼。 ...... 太子狼光一闪,慢慢靠近:咸鱼孤也可以。 夏落:??? 【甜宠,双洁,无虐,放心食用】
52.7萬字8 10952 -
完結16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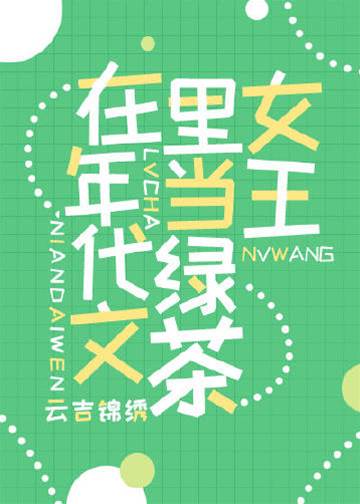
滿級綠茶在年代文躺贏
佟雪綠外號綠茶女王。她外貌明艷身材窈窕,仰慕者無數,過萬花叢而不沾身。等到玩夠了,準備做“賢妻良母”時,報應來了!她穿書了,穿到物質匱乏的七零年代,還是個身份尷尬的假千金!根據劇情,她將被重生回來的真千金按在地上摩擦臉,再被陷害嫁給二婚老男…
88.9萬字8.17 3335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