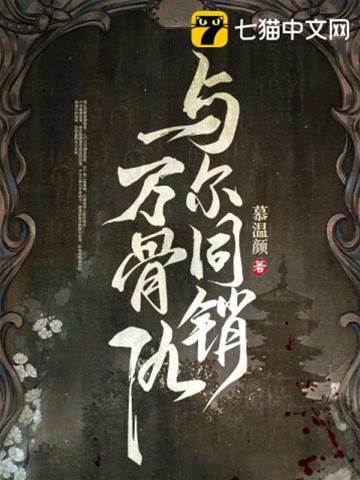《嫁給偏執戰神后(重生)》 第72章 心肝兒
驅馳在道上的馬車音轆轆,夜如墨般濃稠。
回到侯府后,魏元很快將宮中的消息通稟給了只在書房看堪輿圖的霍平梟。
甫一進室,魏元就約覺出,男人的緒有些不甚對勁。
霍平梟的神晦暗不明,眼角眉梢浸著薄戾和沉郁,有一搭沒一搭地用修長的手,將泛著寒的流鏢轉玩,男人強勁的掌背上有許多條分明的青筋在向外微賁。
“說。”
他沉聲命著,指尖似在捻琴弦,流鏢隨其往烏木高架上的花瓶倏飛而去。
“嗙——”
瓶極厚的華貴花瓶應聲碎了好幾瓣,一片片地落在地面,甚至有的地方已經變了齏。
魏元的面微微一變,即刻恭聲回道:“侯爺,宮里的探子來報,說蕭嫣公主傷的那條…是保不住了,陛下已下令徹查此事,說是一定要還蕭嫣公主一個公道。”
霍平梟開眼皮看向他,淡聲問道:“保不住了?”
魏元將探子的話同他轉述一遍:“公主的…好像是爛掉了。”
聽到“爛掉”這個字眼,霍平梟突然森然地笑了笑。
男人的面部廓朗,五深邃俊,可邊的笑意卻有些測測的,讓人莫名聯想到從地獄而來的修羅。
修羅雖是神明,卻總被誤認為是魔,有關他的雕塑莫名著森可怕的鬼氣,無人膽敢將他供奉,是旁人避之不及的惡神。
魏元略微調整了下呼吸,暗覺蕭嫣屬實不該在有那麼多飛龍兵的地方手,北衙和南衙的那些軍,表面上都歸皇帝直接調配,可實際掌管著他們的人卻是任著大司馬的霍平梟。
曲江兩岸和那偌大的跑馬場,都是霍平梟的眼線,蕭嫣剛一派人買通馬,他們這就得到了消息,就沒有能傷害到阮安的機會。
Advertisement
只霍平梟比的心思還要更狠毒。
干脆在馬鞍藏著的鐵釘淬了劇毒,那些毒一旦融進了人的里,就會使那的皮迅速潰爛。
蕭嫣如果想要活命,惟有讓擅長刀法的太醫將整條鋸掉。
蕭嫣的雖然沒了,可縱是在心里,魏元也不敢說霍平梟殘忍。
畢竟蕭嫣對夫人下的也是死手,阮安畢竟騎不,若是在急速奔跑的馬背上摔下來,不死也要落得個半殘。
皇家的人定然知道阮安不會騎,卻還要往侯府遞帖子,分明是想尋機會讓霍平梟難堪。
且不說摻手這件事的都是死士,在曲江做邊球手的也多是南北衙軍的衛士,皇帝是無法將蕭嫣墜馬這事徹查清楚的。
況且,就算皇帝查出了幕后兇手是霍平梟,他也奈何不了如今的他,只能將這事全部當是霍平梟對他的某種威懾,最終還是要打掉牙齒活吞。
霍平梟有這個資本,讓皇帝都對他低下頭顱。
只魏元不清楚,這種屈居人下,要在蕭家人面前俯首稱臣的日子,霍平梟能忍多久。
等魏元離開,霍平梟將語氣略微放低了些,對著博古架外那道瘦小的影說道:“別聽了,進來吧。”
阮安將小手覆在心口那,聽到男人低沉的聲音后,突然一僵,難以置信地將杏眼瞪大。
覺得自己分明藏得好好的,霍平梟是怎麼發現在聽的?
阮安穩了穩不甚均勻的呼吸,決意裝死,先不吭聲。
未料在緘默不語后,卻聽見了冷且沉的“篤篤”兩聲。
霍平梟微微瞥眼,曲指敲了敲烏木書案,催促道:“要我把你扛進來嗎?”
阮安無奈地眨了眨眼皮,終是在男人的脅迫下,躡手躡腳地走進了書記房。
Advertisement
見小妻子的神態帶著懼怕和錯愕,霍平梟冷峻的眉宇輕蹙,朝著招了招手,低聲命道:“過來。”
阮安依言走到他旁,姑娘上的那子乖巧勁兒逐漸平了男人心間的躁郁。
霍平梟將姑娘溫的小手攥掌中,盯著溫弱的杏眼,問:“生老子氣了?”
阮安搖了搖首,小聲回道:“沒有……”
“沒生我氣的話,總躲著我做什麼?”
霍平梟說著,用大手了若無骨的小手,怕將人疼,他不敢使太重的力氣。
阮安已經能從魏元和他適才的對話判斷出,蕭嫣墜馬的事,就是霍平梟派人做的,這麼多年過去,男人的依舊睚眥必報,一點都沒變。
亦終于弄清了,他上那種莫名讓產生畏懼的氣質到底是什麼。
那是一種,獨屬于上位者的強勢。
或許會讓人覺得殘忍恣睢,但又帶著天生的凌厲和迫。
男人上的這種氣質越來越濃重。
阮安知道,或許那個日子,已經不遙遠了。
他早晚是要篡位稱帝的。
但凡是為君大業者,斷不能有婦人之仁,手段也大多凌厲狠辣,雖不習慣他這樣的一面,卻也深知,只有像他這樣的人,才能在那個位置上坐穩。
夜漸濃后,窗外忽地淅淅瀝瀝地下起了雨。
四柱床堆疊的衾被略顯凌,霍平梟將墊在阮安腰后的枕拿走后,便將虛弱的姑娘抱進了懷里,強壯有力的雙臂在將往前收攏時,呈著保護的姿態。
阮安在他溫暖的懷里闔上了眼眸。
其實一直都很喜歡霍平梟上的這一點,就算焰火強盛,卻也從不會將這種事認是的義務。
只要稍稍做出些抗拒之態,他就從不會強迫,也不會表現得太沮喪讓心中不舒服。
Advertisement
所以自霍平梟說他喜歡后,阮安在這種事上,幾乎都由著他的子來。
只的到底溫吞了些,一直尋不到合適的機會將同樣的話,坦坦地同他說出口。
不過照這樣下去,阮安很怕自己又會懷孕。
眼下時局不穩,孩子一兩歲時最是弱多病,不能隨著他們一起奔波,在南境游醫時見到了太多的死嬰,自然害怕孩子會在半路夭折。
未料此時此刻,霍平梟的想法倒是同合了拍。
男人用大手輕輕地拍了拍的肚子,呼吸又重,似只克制的野,嗓音猶帶著云銷雨霽后的沙啞,說道:“我們再有個兒就好了,然后就再也不讓你生孩子了。”
隨著均勻的呼吸,阮安心口間的那枚狼符帶著的溫,著悸的心跳。
地嗯了一聲。
霍平梟接著又說:“如果你不想再生孩子,有霍羲那個小鬼也夠了。”
雖這麼說,霍平梟還是因為沒能陪著阮安度過孕期的那一年,而到憾。
“那你以后,會只疼我一個人嗎?”
想到他在未來會稱帝,阮安突然垂下眼睫,問了他這樣一句話。
霍平梟的神微微一怔。
很快,他領會到了阮安的話意。
因為他很在乎,所以對緒的變化并不遲鈍。
他知道阮安的心中也是有他的,卻不想迫說出那些令難以啟齒的話。
怕會哭,他哄不好。
向他要什麼,他都給。
“當然只會疼你一個人。”
他用大手扣著的小腦袋,俯吻了下的額頭。
霍平梟記用啞帶糲的嗓音同說出最溫的話,每一個字都在刻意哄,仿佛半點委屈,他都要找補回來。
Advertisement
他好像真的很喜歡。
這是阮安以前從來都不敢奢想的事。
霍平梟這樣的男人,看似危險且難以接近,可一旦得到了他的心,他會毫不掩飾地表達他的意。
通過各種方式,給足了安全。
阮安的心,因著他的幾句話,逐漸安沉下來。
這時,擁著的男人用大手拍了拍的腰窩,嗓音溫淡地說:
“寶貝兒,睡一會兒。”
阮安豁然睜開雙眼,有些赧然地小聲道:“你怎麼總這麼…喚我啊。”
雖是同他單獨相,沒有外人在,阮安還是覺得有些難為。
霍平梟低低地笑了聲,無奈問:“那喚你什麼?”
阮安抿著,沒吭聲。
他親了一下,嗓音沙啞地又喚:
“心肝兒。”
猜你喜歡
-
完結309 章
寵妃為大:戰神王爺是妻奴
重生一世,蘇喬隻想要一紙休書。卻是死活擺脫不了家裏這個像換了個人似的戰神王爺為了休書,她在作死的道路上漸行漸遠:“王爺,側妃把西苑的兩個主子罰了”“無妨,把後院給我全遣散了”“王爺,側妃把隔壁侯爺的弟弟給揍了”“等著,我去善後”於是隔壁家的侯爺也挨揍了。(侯爺心裏苦)“王爺,側妃...她....出家了......”“什麼?還不快點給我備馬!” …
53.8萬字8 21858 -
完結361 章
魔妃一笑很傾城
有沒有搞錯?剛穿過去就帶球,還被王子悔婚,還被家裡丟荒山野嶺喂狼——還得在狼堆裡養兒子。21世紀的智商,這些,全部小Case!六年後,她帶著天賦異斌的萌寶寶強勢迴歸,鳳臨天下,鯤鵬扶搖,她要報仇!**毒舌女VS大魔王VS萌寶寶“軒轅隕,我來自未來,不是你的沈墨離,離我遠點!”“娘子,修煉成幻神,的確可以跨越時光,逆光而生
104萬字7.92 26002 -
完結522 章

農家小妻她A爆了
穿越還附帶一家子包子家庭,這樣的人生,過起來可真的是夠夠的了。她趙如瀾,天天懟天懟地,這還是第一次記,碰上這麼奇葩的事情,奇葩的家庭。她吊打炸爹,給自己的寶貝女兒,重新找了個喜歡孩子,有錢多金帥氣的後爹。除此之外,當然是改造自己這些包子家人,讓他們早點改變自己的形象,看著讓人覺得無能的家庭,其實也會有一線轉機。
89.3萬字8 10342 -
完結413 章
我被皇叔寵上天
一朝穿越,成了有名無實的工具人太子妃,蘇沫表示虐渣男,撕綠茶沒壓力,養活三崽子沒壓力,她最大的壓力是那個,整日追著她喊阿沫的英俊皇叔。 三奶包揚言:我娘親有錢有權有顏,就缺個會做飯的男人。 某男:阿沫,江山為聘本王為你煮一生茶飯可好。 蘇沫扶額,不好這妖孽太會撩,本姑娘要把持不住了。 “皇叔,我不舒服要輸液。” 某男一臉緊張,蘇沫一下撲倒妖孽,狠狠地吻著他。 高冷的皇叔噙著淺笑,任她擺弄溫柔的喚著她“阿沫! ”
85萬字8 11054 -
完結36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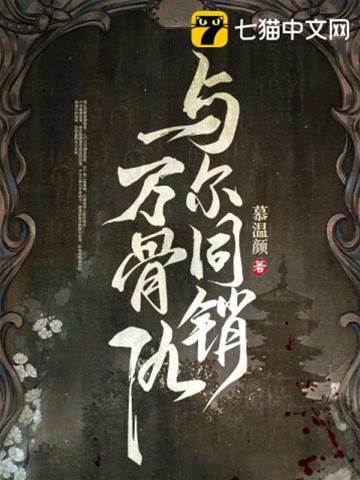
與爾同銷萬骨仇
深山荒野狐狸娶親,人屍之內竟是魚骨,女屍愛上盜墓賊,吊滿詭異人影的地宮...... 六宗詭譎命案,背後隱藏著更邪惡的陰謀。 少女天師與年輕尚書,循著陰陽異路解決命案,卻每每殊途同歸。 暗夜中的枯骨,你的悲鳴有人在聽。
32.6萬字8 7481 -
完結250 章

愛卿,龍榻爬不得
魏無晏是皇城裏最默默無聞的九皇子,懷揣祕密如履薄冰活了十七載,一心盼着早日出宮開府,不料一朝敵寇來襲,大魏皇帝命喪敵寇馬下,而她稀裏糊塗被百官推上皇位。 魏無晏:就...挺突然的。 後來,鎮北王陶臨淵勤王救駕,順理成章成爲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攝政王。 朝中百官紛紛感嘆:奸臣把持朝政,傀儡小皇帝命不久矣! 魏無晏:好巧,朕也是這麼想的。 慶宮宴上,蜀中王獻上的舞姬欲要行刺小皇帝,攝政王眸色冰冷,拔劍出鞘,斬絕色美人於劍下。 百官:朝中局勢不穩,攝政王還要留小皇帝一命穩定朝局。 狩獵場上,野獸突襲,眼見小皇帝即將命喪獸口,攝政王展臂拉弓,一箭擊殺野獸。 百官:前線戰事不明,攝政王還要留小皇帝一命穩定軍心。 瓊林宴上,小皇帝失足落水,攝政王毫不遲疑躍入宮湖,撈起奄奄一息的小皇帝,在衆人的注視下俯身以口渡氣。 百官:誰來解釋一下? 是夜,攝政王擁着軟弱無骨的小皇帝,修長手指滑過女子白皙玉頸,伶仃鎖骨,聲音暗啞:“陛下今日一直盯着新科狀元不眨眼,可是微臣近日服侍不周?” 魏無晏:“.....” 女主小皇帝:本以爲攝政王覬覦她的龍位,沒想到佞臣無恥,居然要爬上她的龍榻! 男主攝政王:起初,不過是憐憫小皇帝身世可憐,將“他”當作一隻金絲雀養着逗趣兒,可從未踏出方寸之籠的鳥兒竟然一聲不吭飛走了。 那便親手將“他”抓回來。 嗯...只是他養的金絲雀怎麼變成了...雌的?
40.5萬字8.18 1120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